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先谈谈“是”是什么的问题。
《说文解字》里,“是”指的是夏至时分太阳走到空间的基准点上。由此,“是”引申出“正确”、“善”等含义。《淮南子》中有“立是废非”的说法。“是”还意味着“遵从、以之为法则”,《荀子》中有“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之语。
我们已经很少谈及“是”的上述含义了。尽管,“是”也许是我们使用最多的汉字。我是教授,我是政协委员,我是商人,我是官员……当人们习惯用这样的句子向别人介绍自己,却往往忘记了“是”字之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我”,而“是”字之后,是这些称谓应该正确遵从和恪守的职业法则。
这也就是南方周末为何以“我是”为纲,来编辑这一期报纸。我们让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来阐释“我”,更阐释他们的人生规则。他们或是“兢兢业业”,向内寻找本职工作的意义;或是“不务正业”,向外拓展人生价值的外延。无论向内还是向外,他们都在遵照内心的信仰和规则,确立自己的“是”,写下大写的“我”。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红二代的观点,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在法律和宪法上达成共识就好。谁都有说话的权利。
我退休后的生活,是由一堆聚会组成的。
聚会分两种:一种是红色后人的聚会。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有很多活动;还有许多战役的纪念日,许多父亲战友的诞辰或者忌辰。推不掉,我就参加。推得掉的,我就让给我的大哥陈昊苏参加。他更能代表老陈家。
另一种聚会,我把它称作“尽社会责任”。比如《财经》杂志的年会,讨论政治形势;比如一些反思“文革”的讨论会,我不是专家,可以谈谈自己亲历的事。
又比如2013年11月,我参加了由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的“江湖”沙龙。中国证券的创始者高西庆、王波明等,回顾当年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经过。现场,王波明甚至提到了与我的一段交集:
1980年代末,王波明找到了我,我当时正担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改室)社会改革局的局长。他对我鼓吹,中国要建立股票交易所。我那时不明白,只能对他说:你说半天股票交易所,可是我现在研究的是,社会发生动荡以后,到底如何处理——社会改革局嘛。
那是1988年,物价飞涨,社会不安,我们政改室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不过可惜,还没调查完,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销了。
现在想起来,即使很多东西不明白,这段交集对我影响也很大。在政改室的那段日子,让我了解了中央运作的过程,也让我体悟了改革之难。随后,我选择离开了体制。转业,经商,一直走到现在。
所以,我算是“红二代”当中的少数了。
为“文革”道歉也一样。我曾用“头羊效应”来解释群众运动——羊群中,头羊起着导向作用。头羊一走,大家就跟着走。“文革”中,极左的人就是头羊,它诉诸武斗,打砸抢烧,其他的人都会恐惧,于是没有人敢说真话,大家都随波逐流。
为“文革”道歉,则不存在“头羊效应”了。“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
因为红二代的多数人,都是吃“皇粮”的——军人,或是在体制内。我不吃“皇粮”,比较自由。我还是纳税人,所以讲话可以多一些,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红二代的聚会上,我则说话不多。大家默契地不谈政治,不谈敏感的问题。都是说谁又整理父亲的文章出书了,谁又到哪里参加纪念活动了。
在我看来,红二代无足轻重了,应该和普通的农民工一样的。都是一帮老人,带着记忆活着而已。如果还能说说民情,让领导听一听,就是好事。
红二代的观点,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在法律和宪法上达成共识就好。
谁都有说话的权利。我们正计划做一个“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记”网上平台,使用“百度百科”的编辑方式,谁都能在上面写文章、补充细节,主要是想把历史记下来,别重蹈覆辙。
2013年12月29日,我还到国际金融博物馆,参加了另一场“江湖”沙龙。主持人是任志强,另一个属于少数的红二代。
他们让我谈谈我的人生。我老老实实讲:我这个人,也无足轻重,就是潇洒一点,追求自由的人格,仅此而已。
(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采访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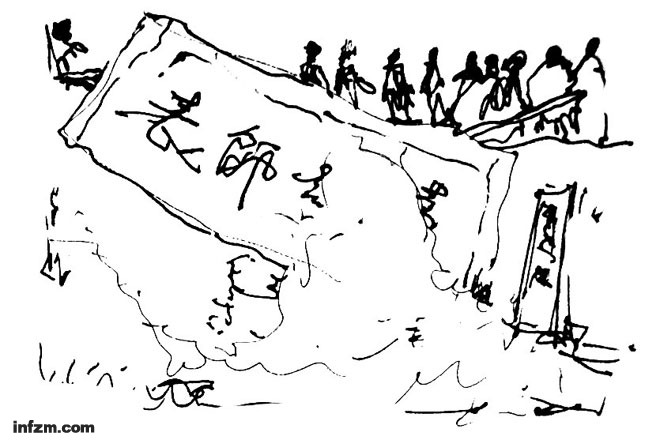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