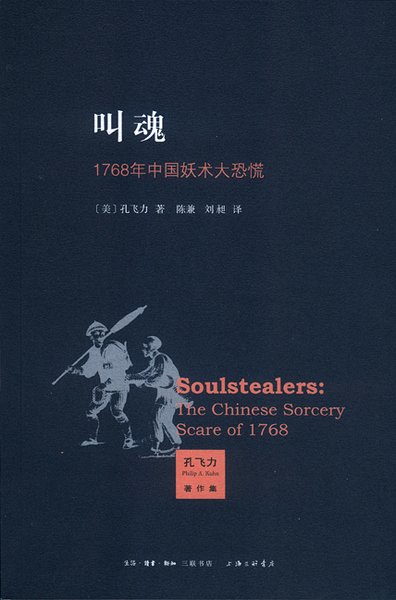
1768年,乾隆盛世。安定和谐的社会表象之下暗流汹涌,千疮百孔的中国近代史即将拉开帷幕。在这个特殊拐点上,一种对“叫魂”妖术的恐惧短时间内近乎疯狂地席卷全国,十二个省份受到波及。农夫、官僚及皇帝均被卷入其中,在狂热的闹剧中兢兢业业地出演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或许是一个预兆,或许是一种警告;然而事件很快风平浪静,我们生活在18世纪的祖先并未意识到波折隐喻的社会状态。直到两百多年之后,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挖掘出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并以历史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梳理和解读,写成了这本严谨而不失趣味、翔实而不致沉闷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在盛世繁荣的表象下,庞大的人口已开始对社会生活形成压力,山区与平原沿海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诱发了民众心底的惶恐不安。经济地图上的倾斜带来了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对底层流浪者的疑惧一点一滴累积起来,最终在“叫魂”事件中爆发。浙江省一个县城修桥请来的石匠被诬将写有人姓名的纸条打入桩中借以害人;云游到萧山的和尚因询问小孩姓名而被恐慌的家长扭送官府屈打成招;恐惧的民众将身上带着几张护符的铁匠活活打死;在安溪县,甚至有人仅仅因为口音生僻而被村民捆绑并殴打至死;在苏州,几个乞丐被怀疑剪人发辫而遭拘捕,其中一人死在条件恶劣的狱中。
对妖术的恐惧很快扩散到长江以北;在汉阳,一个“妖人”被群众私刑处死并遭焚尸。事态愈演愈烈,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将可疑的乞丐、和尚、匠人、异乡客等扭送官府或群殴至死,各级官员疲于应对、屡屡动用大刑逼供,最终连乾隆皇帝也被惊动,接连下达谕旨清剿妖人。各省官员遂闻风而动,一个庞大而有组织的妖党团伙竟被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
事实上,到1768年底,几乎所有“叫魂”案都因没有足够证据不了了之,只见被诬陷冤死的无辜百姓,不见认罪伏法的作乱妖人;屈打成招与遭罗织陷害者纷纷翻供,承认并无其事。最后,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停止搜查,释放被羁押的疑犯,惩治办案不力的官员。这一风波终于偃旗息鼓。
孔飞力认为,“叫魂”事件在民众、官员与皇帝眼中是截然不同的三个故事:
对普通民众而言,下层阶级越来越多地渗入社区生活,激发了人们对陌生人早已有之的恐惧。他们对赤贫者的道德责任感随着乞讨现象的泛滥而不断削弱和模糊。当妖术谣言传播开来,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向离得最近的乞丐与和尚猛扑过去。同时,对于绝无可能接触权力的底层民众而言,“叫魂”一事忽然慷慨地赋予了他们一种权力的假象,似乎假借这一名义,便可满足心中报复与贪婪的欲望:“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这一罪名成为一股从天而降的力量,被不同境遇的底层民众视作量身定做的工具,借以获取自己无法通过其他路径实现的利益:“对担心受迫害的人,它提供了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在普通民众无法真正享有权力的社会中,清剿异己的狂热带来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快感;一旦这种行径被国家默许,便愈发难以抑制地蔓延开来。
对乾隆皇帝而言,他最关心的与其说是妖术,不如说是“割辫”这一行为:在清朝,头发样式是一个政治问题,剪人发辫即可视为谋反。他在关于妖术的第一份谕旨中称“叫魂”之说“其言甚为荒诞……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庭,理应留心查禁……”可见他本人对于妖术并不相信,却深深忌惮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隐患。在他看来,百姓轻信、而且易被煽动蛊惑;妖术的威胁不在于百姓性命,而在于社会秩序和统治稳固。他同时认为,江南地区汉化程度较高的官员腐败顽固,朋党为奸,欺上瞒下,对妖术一事知情不报,因而不值得信任。而山东巡抚为抢占先机,在得知皇帝即将发出上谕的前一天递交奏折,声称叫魂并非简单流言,而真是妖党有规模、有计划地引发恐慌。巡抚提供的佐证是两个乞丐的供词;无论其中提及的剪人发辫、摄人魂魄乃至作乱谋逆之事是罗织编造抑或确有根据,这份供词都成为皇帝大规模镇压妖术的基础和理据。
其实,对大部分官员们而言,他们普遍是因职责所在而谨慎行事,本身对妖术的说法不以为然,却又不得不在皇帝的催促与暴民的狂怒下给出个说法。在官员心目中,无论流浪者是否与妖术有关,都是不稳定因素: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者无法被纳入政府的控制体系,因而令官僚机构头痛。因此,当上层与下层的压力共同作用于他们身上,一部分为求自保的官僚们选择顺应圣意、大力清剿搜查。难得的是,仍有一部分官员采用各种抵制手段消极处理,直到风波平息。然而孔飞力指出,这些官员们设置障碍并不意味着封建官僚制度对皇权存在某种制衡。因为若要限制与平衡君主的专制权力,官员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视为皇帝的奴仆,而要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然而,在帝制早已是强弩之末的时期,具有此等胆识与自信的中国官员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之后,当帝制终于垮台,滋养这种自信的社会与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
尽管各怀鬼胎,乾隆年间效率低下的旧中国官僚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阻挡皇帝与民众的狂热,“叫魂”一事也因此未能造成太大影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平息。然而,当旧制度终于垮台而新制度尚未完善之时,新统治者就可能利用和操纵民众的恐怖力量打击异己,而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种疯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叫魂”可算闹剧一场;而真正的悲剧,在近两个世纪之后才在中国上演。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