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结束,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一直存在着。
无真相,无反思
胡发云2016年4月关于文革的一次讲座
最近正在为我的一本台湾版的书做一些最后的文字工作,这本书是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是我的文革三部曲的第一部《迷冬》,副题是“青春的狂欢与炼狱”。5月16日左右,也就是我们大陆的文革50周年,将由台湾一家出版社出全本繁体字版。这期间,一些朋友、老师都很关注,都在讨论和这本书的有关问题,有些话题刚好和今天晚上这个讲座比较接近,其中朱学勤老师看了这本书后,首先提起这个话题,他看了这本书后,觉得也可以当史来读的,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说这个史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朱学勤老师接着说,任何反思如果没有真相,这个反思就没有前提。我今天晚上就讲这个话题。
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文革十年,多年以前,我对文革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文革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如果稍微说得明确一点,它应该是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甚至更早一点的延安整风开始的,第二,文革到现在没有完全结束。第三,当年那种特殊形态的社会运动的文革,应该是12年,即从1966年到1978年。我为什么把后两年也加到文革当中去呢?因为这两年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文革的一部分,是文革的尾声。1976年,我们用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也就是文革的方式——几个人碰了一下头,商量了一下,用了军队,把一帮人逮起来了。这个手法,文革当中一直在用,从1966年一直到1976年,动用国家军队和非法治方式对付自己的政敌,一直是惯用的手段。1976年后,并没有跳出文革党内斗争的套路。甚至还可以说它发展到了一种极致。那些胜利者们,在完成这一次的宫廷政变以后,他们打的所有旗号,实践的所有理论,都跟文革一脉相承,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时所有的语言、方针、政策、路线、口号都是差不多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只是文革的一个部分。在十多年前的一篇小说——《葛麻的1976——1978》中,我就谈到了,这两年实际上也是文革。我在书里面通过一个老工人的遭遇,和他的几个疑问,提出了这个问题。官方关于建国后的历史划分也显示出这种尴尬:文革以前叫17年,文革叫十年浩劫,而新时期呢,又是从1978年底开始,共和国史是分成这么三截的。这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问题,17年到1966年截止,文革到1976年截止,而新时期又从1978年开始,那中间的1976——1978这两年到哪去了?我说这两年是个尾巴,还长在文革的身躯上。当然从后来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看来,文革那一套实际上都还在,文革的那些人也还在。文革是十年也好十二年也好,它的基本统治力量,还是共产党,是它所控制的军队。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还是到基层,文革前的人,文革中期的人,文革后期的人,基本上都在那儿活动。只是走马灯一样上上下下轮换而已。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的,指导思想也没有变,崇拜的偶像也没有变,思想理论来源也没有变,就谈不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变革。我这样的思想从很早——应该是从1976年就开始隐隐地在我心里作怪,不时在思考和观察这一类的问题。现在能找到原始资料的,是1997年我们湖北省由女作家方方主持的一个刊物,叫《今日名流》,召开过一次关于文革的座谈会,当时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大概有7、8个湖北的学者、专家和作家,为了今晚这个讲座,我上午在网上还居然把它搜出来了。现在我把我当年的发言,按发表的座谈纪要读一下。那是1997年,离现在将近二十年,看看当时我是怎么想的,怎么表达的:
1978年当局宣布文革结束,三年后,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去清点,反正我们已经作了结论了。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或是其他参与者、关心者,对文革研究的自由度还是非常小的,这有种种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至今为止,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种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进行,有很多规定好了的表述不能突破。
首先有必要对文革的过程和事件进行一种清理。文革像一头极其巨大的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国各地、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各种阶级地位、各种不同结局的人都能够参与。重要的一点,文革是亿万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它有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如果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又不利用这种资源,那就比付出代价本身还要可悲了。
现有的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纪实作品或理论研究著作,都时时可感觉到一种隐匿现象。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涉及他参加“新北大公社”的一段,就写得极其含糊不清。实际上,当时一些教授、作家、右派及“胡风分子”等,在文革的某一阶段,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一种蠢蠢欲动的、使出浑身解数的姿态。而刚刚粉碎“四人帮”,将文革作一种脸谱化的定位时,他们非常快地抓住文革初期受迫害的形象,以致固定下来,一直演绎到文革结束。而把曾经积极参与的另一段经历非常深地隐匿下来了。
还有一批隐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员,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依然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文革最终的结果,是一大批的隐匿者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重新寻找这些文革的隐匿者,让他们重新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些责任,让他们发出自己对历史该发出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有一些官方性质的文革史,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去补充,它们以后就会成为正史。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进行甄别的话,这些人死后,这些文革史更是白纸黑字,不可改变了。
说文革的发动、推进是权力之争,我以为不准确。还要加上意识形态之争,利益之争。当时中央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稳定的。而老百姓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政治地位出发,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极其复杂。右派、胡风分子、大学教授等一些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不在体制中心的人,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1957年相近,有疏离体制和反体制的情绪在里面;社会底层也是这样。这些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各阶层自己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群在新体制下的心态和利益及其在文革中的要求和反映,都很有研究价值。
上面想法,我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下或讲座中都作过更多更深入的阐述,包括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有前几年在美国和欧洲都谈到了这些问题。我说当时文革各派群众组织,都在毛的话语中,在毛的旗帜下,利用当时文革的理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时有很多这种社会现象,都被我们的文革史和政治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革初期的很多群众组织,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生活经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比如说,当时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组织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这一个带有经济色彩的口号。比如说,文革以前,就有因为出身问题,个人思想问题,剥夺了他们升学的权利发配到农村去的那一部分老知识青年,他们的口号是:“回城闹革命”。他们在这样的口号下组织起来,以打倒刘少奇的这样的一个革命的口号,来证实他们的革命的合法性。甚至还有一个组织,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们接过了反走资派这样的一个口号以后,就认为今天的走资派就是1957年镇压他们的那些旧官僚,他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找回自己真正的社会评价,他们认为他们当时就是在完成今天文革需要完成的任务。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织——“1957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设在当时的武昌红楼,现在的辛亥革命纪念馆里面。后来我在网上查询,发现湖南也有同类的组织。当然,这种组织后来的下场是非常惨的,它已经超越了最高当局对文革的规定性,有的人被判了死刑,有的被抓进监狱,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在当年那个座谈会上,我提到了这一点,我说,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社会运动当中,文革无疑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前面有德国的纳粹运动,中间有苏联的苏维埃运动,中国最典型的一段,就是文革运动。但是呢,文革又不能和纳粹作一个简单的类比,纳粹运动的施虐者和受害者界限分明,二战结束后,纳粹的整个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被完全摧毁,文革就要复杂得多。
这是当年一些非常粗浅的想法,后来接触到更多的资讯,深化并丰富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十年文革,它是由同一个领袖,同一个军队,同一个党组织一直控制着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舞台上演出的角色,却经常在轮换,戏份内容也在变化。所以,文革12年,有的人此时是白脸,彼时是红脸,此时是英雄,彼时是罪犯。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看到它的真相。很多人谈起往事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跟我讲讲,你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我才能判断你这个表述是否准确。”去年跟某个文革史专家发生过一次非常激烈的辩论,她有一篇文章,讲一个叫张放的女教师,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在文革当中的悲惨遭遇,最后不堪折磨自杀身亡。我看了以后就跟他说,你这个故事本身,我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这个人死了,有名有姓的,而且她还有家属,但是,她被谁整死的,你里面的表述,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起码是你没有给出一些准确的要素,来说明这个人是死于怎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致她于死地的是怎么样一些人。
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语言的迷宫和陷阱中。刚好今天上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当年马思聪叛逃的文章,我转到朋友圈,有很大的反响。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不管他是文革的亲历者,还是后来的年轻媒体人,他显然也落入了这种的语言陷阱。
关于马思聪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马思聪出逃记》,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就不复述文章的内容。但是,我要说明这篇文章是如何落入了文革捣糨糊的陷阱之中,以至于到今天,我们没有弄清楚是谁让马思聪受的罪,逼迫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像一个偷渡的深圳渔民那样跑到香港去的。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马思聪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章很抽象地说了: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个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每天被迫学习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写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进了学院,接受了红卫兵小将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他们还来不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了马思聪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戴在了他头上,他脖子前后挂上了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边走一边敲。这个地方涉及到了两个迫害马思聪的对象,一个是没有在文章没有出场的角色——是谁把他们送到那个牛棚去的?1966年的6月,群众组织还没有兴起,各个单位还是党委当家,那么这样的一批在各单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是谁送的?第二个,就是到了8月的时候,一辆贴有“黑帮专用”的车,把他们送过去,红卫兵小将是怎么折磨马思聪的,文革中有各种各样的红卫兵,这个红卫兵小将又是谁?这两处都说得非常含糊。好,我们再往下看,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与一群黑帮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里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吐唾沫。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变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承认自己有罪的歌,只要那些小将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而这里又出现了第三个对象,叫“造反派”。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没有点名的一个角色,把他们送到牛棚,然后又在8月份——即2个月以后,红卫兵又把他们带回学校,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体罚和折磨了。第三个对象,就说得很清楚了,叫“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他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
文革史中的“造反派”这个词,应该出现于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号召之后,涌现出来一个群众组织派别,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恰恰是6——8月这个期间被打击被批斗的对象,也是和前面两个角色对立的一批人。他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但是为了区别于前面那种红卫兵,他们会加上各种前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前面说的只有三个字的红卫兵,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为基础,以地富反坏右等传统的阶级敌人,以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迫害对象。随着运动矛头转移到他们父辈头上之后,他们成为当时保护父辈,保护旧有体制的“保守派”。这两个派别,成为贯穿文革史的两大派别。
为什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将折磨马思聪的对象,用了这么几种不同的称呼?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语言陷阱。我们搞文史研究,需要非常严谨的学术规范,应该对每一种人有一种准确的表述。但是恰恰是在做文革史上,混淆了很多概念,并就发明了很多种篓子,把一些不便表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很简单地扔在一些篓子里面,比如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比如说抽象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有那个“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分子”“四人帮追随者”,这样的一些表述,表面含混,实有所指,根本的目的就把他们觉得很难堪的话题回避过去。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和我自身的经历,和整个运动过程的了解,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第一个把马思聪关进牛棚的,是他们音乐学院的党委,或者是更高的部门。第二个折磨马思聪,让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拔草或者是一边干活的,这个是当时的一批由北京的建国元勋们的后代、现在叫红二代组成的老红卫兵,也就是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红卫兵干的,第三个让马思聪吃草的“造反派(瓦工)”,应该是当年当年音乐学院根正苗红的左派工人,在文革史中,他们应该归于“保守派”,是和后来起来造他们父辈反的那批人相对立的。文章后边就不断地用“造反派”这个词了,这个造反派在文革当中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的符号。古人说,造反是犯上作乱,那么,显然前两者是谈不上造反的,尽管他们也喊造反的口号,他们当时只是镇压,他们当时是处于社会的权力阶层,他们对马思聪这样的人,以及别的在他们眼里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好,地富反坏右也好,他们只是是一种戏弄式的屠戮和镇压。文革史上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毛泽东最后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号召下,那些年轻学生们,特别是那些在运动初期受过打击压迫甚至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小爬虫和有问题的学生们,他们感到毛泽东把他们解放出来了,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向上造反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一批人,他们后来的矛头,不再是对着马思聪了,而是对着院校的书记或者是北京市的领导甚至中央的领导。那么这一批人,才叫真正的造反派。那么为什么他们后来笼统地把所有的坏事都算在造反派头上呢?因为他们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弟们干的坏事遮掩起来。那么,关于马思聪的这篇文章里面,后来发生了一些诡异的变化,你们看到前面一直让他们拔草啊,一个“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一个红卫兵还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这样的表述,都已经开始用造反派来替代其他的角色。这个当中,就有一种变脸术,就想把运动初期他们和他们子女干的事,慢慢地用一个“造反派”的篓子把它装进去。一个运动的十年,所有的坏事,后来都基本上放到了这个篓子里,都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造反派”,这样,就把他们自己躲过去了。马思聪的这篇文章又说到,到了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这一点,我可以说一下,这个时候的造反派,可能是真的造反派了,就是后来用“造反派”这个词给予定义的那批人,这一批人到了1966年11月份,他们开始渐渐得势,他们的革命对象,已经主要不是马思聪,甚至完全不是马思聪了,他们当时正在把中共所有的高级干部梳理一道,看看哪些是不同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批人,正在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个时候,马思聪被这些人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就合情合理了。马思聪回家后,发现自家的四合院已经搬进了4、5户人家,那就是说,在马思聪他们6、7、8月出去受难的时候,已经有人住进他们家来了。他最后能够往广州逃跑,实际上是当时造反派没有关注他,也没有兴趣管他的那段时间,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出逃的条件。当时在武汉,在其它地区,都是那样。我在《迷冬》里面写到,那些运动初期被各级政府抛出来的人,到了1966年底,突然没人管他们了,或者是管束比较松了,他们从牛棚出来一看,天地大变,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群众已经在斗夏天镇压他们的人、迫害他们的人。所以这批人当时,很快会感激造反派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喘口气的机会。这批人很多后来也成为同情、支持造反派的人。我很随机的从这篇《马思聪出逃记》这篇文章,看出了我们的文革叙述是如何地混乱如何地荒唐,即便这篇帮马思聪说话的文章,也落入了这样一种语言陷阱中,使得一批也该承担责任的人们,把自己的罪错洗白了。另一个同样的话题,我2008年在武大的一次讲座中也说到过,我当时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在座的这些研究生大学生们,有多少人知道你们的老校长李达?当时举手的人不少。我又问,那么李达是谁迫害致死的?大家都不做声了。我说,最顺口的一句话就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个是文革结束之后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我说,李达死的时候,林彪的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也管不着湖北省这样的事情。第二,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影子,那时的王洪文还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小保卫干事,其他人也没有“帮”起来。李达的死,和当年在任的几个高官不无关系,比如说,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当时的湖北省省长,还有武大的党政干部、包括李达的秘书,他们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这些人从来没有提及自己是迫害李达的责任人。这就和我刚才说过的马思聪的遭遇一样,在文革当中,一些真正的迫害者,在文革以后,说得最多的,是在第二个阶段自己受到的迫害,他们在第一个阶段以及其后几个阶段当中迫害别人的事情,他们从来不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达了以后,就不许再追究文革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个人的每一段历史。这就是是我说的,文革远比纳粹运动和苏联的苏维埃运动要复杂得多,就是因为文革加入了很多中国自身的社会矛盾,而毛泽东在文革当中不同时期大幅度的摇摆和突变,也给解读文革造成很大障碍。比如1968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有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叫“清查5.16运动”,这个阶段,又将第二阶段中最高当局支持的造反派当做主要镇压对象了。这个运动也是当局多少年以来不敢直面的。最近一期的《领导者》有一篇文章——也可以在他们的共识网上查到,作者是杜钧福,标题是《清查5.16运动始末》。这篇文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最高当局是如何随心所欲地运动群众、迫害群众,他们像演木偶戏那样,操纵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一场运动,而这个运动,除了北京数十个大学生,其余几乎都是莫须有的。在长达数年的“清查5.16运动”当中,迫害致死的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直到现在,只有个别省份披露了一些信息,依然得不到具体的数字,但受到直接迫害的应该是数以百万计。
我刚才谈到了,近40年以来,从1978年到现在的2016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许多人的前史都和文革有关,你们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履历,如果他们的年龄在60到80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他们很多人都有在文革当中不同地方任职的经历。能够在文革当中任职,能够在“九大”前后入党,能够在文革时期提升为某一级干部的,应该说都是文革机器的一部分。所以,这样一部分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它几乎是整体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整体地接管了这个新的时代,并且继续享受它的一切好处。在这点上,我觉得今天不能够直面文革,不敢否定文革,更不能清算文革,是有它的原因的。前不久我看到了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一篇文章,杨继绳比我年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我们有非常多的同感。杨继绳的这篇文章叫做《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这篇文章我推荐大家读一下,他在文章里面说的,也跟我在1997年的发言里说到的一样的,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其中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杨继绳说: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为当时面临的政治问题,以折中妥协的态度来写总结评价文革的,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这篇文章非常简明扼要地把我们最高当局和执政党对文革的这种态度点了出来。决议里面说,关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错误的领导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论断把林彪、四人帮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我刚才说过,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文革当中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在党内兴起、在党内消亡,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另外我补充一下,杨继绳先生有一个没有提到的话题——文革当中最重要的一批力量,甚至在各个时期都可以看得见他们的手的那支队伍。他们在文革当中,从1967年初“三支两军”开始——就是支工、支农、支持革命左派,军训、军管,就几乎掌握了中国上上下下的最大的权力,他们已经成为皇上派出的“御林军”,小太上皇,他们在文革干的坏事也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但是,这一块也是最缺乏清理、缺乏反思的。你们只要看一看,文革当中,那些重大的冤假错案,那些重大的杀人案,广西、青海那些事件当中,在军管时期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中,就可以看得见那只强有力的专政之手了。当这一切都不能面对的时候,所有反思都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对象,也没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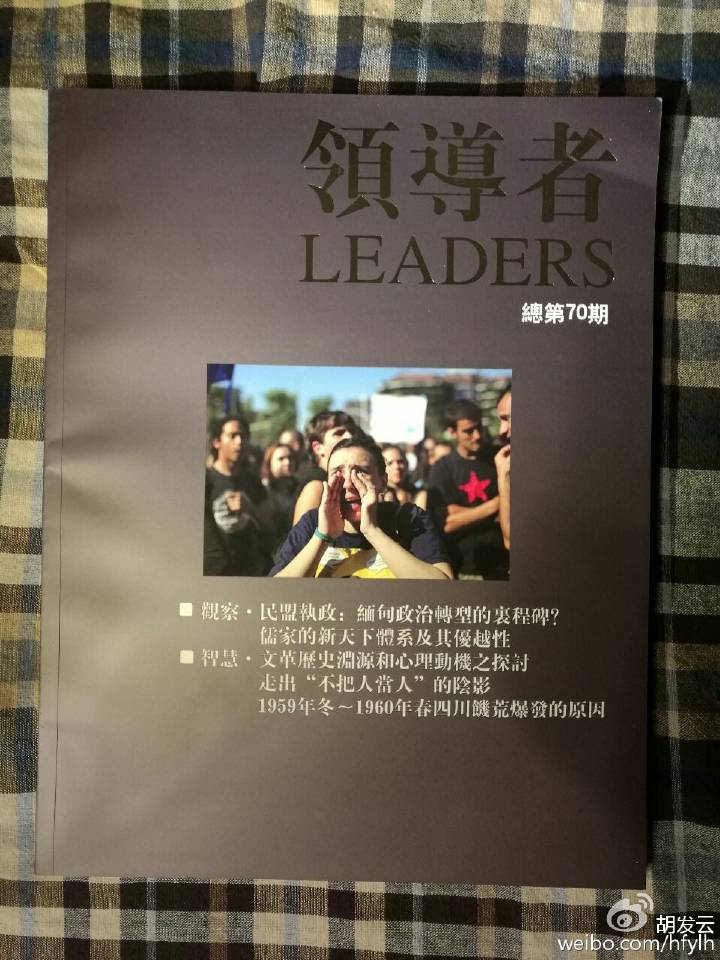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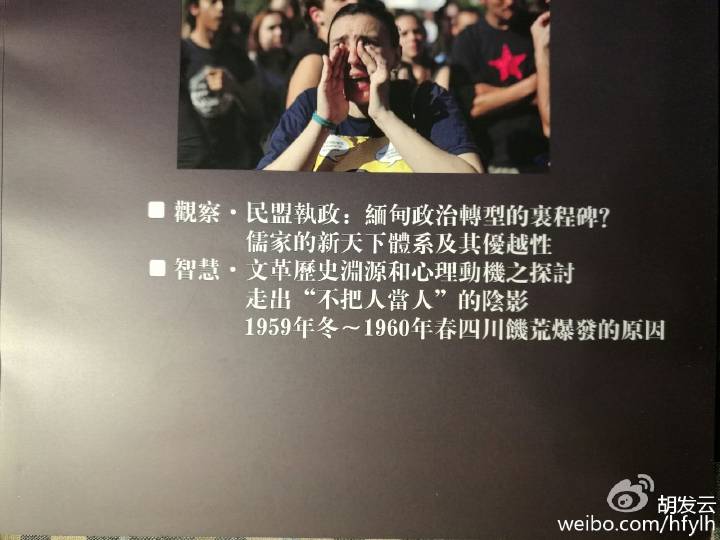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