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到达丹麦?当然,在这里,“丹麦”不是特指丹麦这个国家,而是指一种美好如童话的状态。具体到政治上,就是一个国家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沿袭《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看法,福山的基本出发点是: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这看似一句“正确的废话”,其实不然。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这个维度的意义。所以,他的“政治三维论”表面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核心却是要为“国家建构”这个政治维度“正名”。
在书中,“国家建构”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用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家失败”;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希腊、意大利今日的债务危机;还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美国当代的政治僵局。当然,国家建构的问题,不仅仅可能“太少”,也有可能“过多”: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国家建构”剂量过大走火入魔了;而中国,在福山看来,也是国家建构有余,而另外两个维度不足。
什么是“国家建构”?概括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能力、一个是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autonomy)。前者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后者涉及政府能够超越各种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光是拳头硬还不行,还得有“一览众山小”的超脱地势。
与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的,在这本书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依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私利”的逻辑取代“公益”的逻辑。其表现,是权力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绑架——在美国,可能是那些组织性非常强的游说集团,在非洲可能是某个强大的部落甚至家族,在希腊、意大利,则可能是积重难返的公有部门。总之,当政治家和官僚机构不能从局部的、特殊的利益当中挣脱,而是被其俘获,依附主义就产生了。依附主义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标志。
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走向了“国家建构”,而有些则陷入了“依附主义”?成功的国家建构,从福山的论述中,可以梳理出三个由来:
第一是战争。军事压力迫使一个国家在征税、人口管理和军事建设方面加快步伐:中国国家建构方面的“早熟”与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相关;欧洲各国近代以来的频繁战争也是它们走出封建主义、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动力。相比之下,拉美国家之间缺乏持续性、高强度战争,所以拉美国家的问题一直是国家能力不足;同样,非洲长期以来的地广人稀与地形地貌,也使得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没有形成国家建构的压力。
第二是政治改革。为什么同样是早发宪政国家,希腊至今深陷依附主义,而美国的国家建构相当成功?原因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政治改革,以考试制的公务员体系取代了“政党分赃”式的职位分配制,而希腊却始终没有发生这个关键的“龙门一跃”。这种分岔又何以出现?美国十九世纪后期高速的经济发展重组了社会阶层,新兴的经济集团不满旧式的分赃制,推动了政治改革,而希腊所经历的是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即所谓“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精英阶层没有根本的“换血”,始终寄生于政府和公有部门,并且这个寄生阶层越来越大,引发今天的债务危机。
第三是民族认同。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如何说服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万里之外的黑龙江人认同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如何让一个佐治亚人和一个马萨诸塞人被同一面国旗感动?同样,如何让一个Kikuyu人和一个Luo人将其历史上的身份感置于“肯尼亚”三个字之下?共同的民族认同往往极大压缩国家建构的成本,而民族认同本身也往往被建构:政府强行推行的共同书面语、宗教、经典文本、各种“主义”、宪法,都是形塑民族认同的方式。在这个方面,福山对尼日利亚和印尼进行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国家,认同感“揉捏”的成败很大程度影响了国家建构的成败。
对“依附主义”的起源,福山则强调一点:早熟的民主制度——即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发展——是依附主义的温床。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他以美国早期的历史为例,展示当时公职如何被执政党当做“战利品”瓜分,而这种瓜分的动力恰恰是民主机制——从1830年代的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了赢得选票,候选人承诺选战胜利后分配公职给支持者。在福山看来,今天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悲剧逻辑类似,都是选票逻辑推动了公共职位与资源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攫取”(captured),而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又始终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发生。
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最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而不是之后,没有强大自主的官僚机构与借民主通道前往“分食”的各路人马对抗,选票逻辑只会将公共资源变成被哄抢一空的政治自助餐。更何况“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财力、组织资源丰富的人群往往抢得最大的一块饼,而他们却往往不是最饥饿的人群。
但这可能也是此书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福山试图梳理出一个“民主-依附主义”的逻辑时,他显然忽视了专制之下的依附主义问题。甚至,某种意义上,民主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或然性的(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能够通过改革摆脱“政党分赃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丹麦”),而专制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是必然的。专制,根据定义,几乎就是为“片面的”利益服务的——这种片面性可以体现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部族、一个教派、一个党或者一个阶级。当政府权力与一个片面的利益结合时,就构成了“庇护-依附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试图把秦汉时期(以及后来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时代)的中华帝国描述成一个中立的、非人格化的、自主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时缺乏说服力——的确,从暴力垄断的角度而言,大一统王朝中国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大,但是从政府的不偏不倚性角度而言,一个“家产官僚制”如何可能真正做到中立、自主、非人格化?当袁崇焕和崇祯帝发生冲突、岳飞和宋高宗发生冲突时,官僚机构如何保持“中立”?
事实上,美国的历史不但说明一个国家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再进行“国家建构”,而且民主制度框架的存在促进了国家建构。众所周知,美国十八世纪末就有了代议民主的基本框架,而它真正的国家建构——碍于其强大的州权传统与政党分赃制——迟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渐进发生。正如福山自己所说,政治改革是美国国家建构的动力之一,而美国十九世纪末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票给议员带来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改革呼声如此之强大,政治家不可能再装聋作哑。
民主问责可能促进国家建构——至少是提高官僚机构质量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格外有意义。在福山列举的国家建构主要动力中,有战争、政治改革与民族认同。今天,刻意发动大规模战争来促进国家建设既不现实,也很可能得不偿失——总不能现在一斧头把阿富汗劈成七份,然后说,“你们先打两百年吧,没准能打出一个秦始皇,两千年后阿富汗的崛起将势不可挡”;同样,认同的形塑——在族群世仇的基础上建构共同的民族认同,又岂是朝夕之功?反倒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改革,可能成为官僚机构摆脱依附主义而成本相对低、见效相对快的动力。
固然,民主可能滋生新的依附主义形式。福山书中所说的利益集团、游说集团爬满美国政治躯体的现象,的确存在。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却值得思考。正如一个美国政治分析家指出,“我们,你,我,他,都是各种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一个清华大学女教授,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教师协会”、“北京居民菜价补贴协会”、“公立医疗保障项目组织”、“职业女性平权协会”等各种游说集团所代表。某种程度上,游说集团是代表性的一种形式——相比专制体制下隐秘的、黑箱里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公共资源游说,民主和法治体系下,游说至少可以更规范、更透明——比如在美国,所有的游说人士和集团必须公开登记,而所有的政治家不得收受游说人员超过二十美元的礼物。更根本而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否则民主可能带来的“游说集团”现象就不可能完全禁绝。当然,一定的改革可能缓解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比如缩小政府职能),继续改革也仍有必要,但是将民主所滋生的广泛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现象当做一个道德上黑白分明、因而解决办法一目了然的问题,显然忽视了任何改革可能带来的价值互换性。
那么,到底如何“到达丹麦”?总结福山的看法,一是国情论,二是顺序论。
“国情论”不难理解。既然“丹麦”意味着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之间的相互平衡,那么,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应当“缺啥补啥”。对那些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主与法治但欠缺国家建构的国家,就应该努力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在当代,此类国家似乎是福山笔下的多数,从非洲到拉美,从印度到希腊,似乎都应该着力于此;而对那些国家能力有余但是民主与法治发展不足的国家,药方则是另外两个维度的加强。
“顺序论”则是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答案,在书中若隐若现。就政治发展三个维度的顺序而言,英国似乎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情形:法治 (大宪章时期就有萌芽)、国家建设(都铎王朝下的王权兴起)、民主(十九世纪普选权的扩散)。法治的基础使王权的壮大不至于绝对,而国家能力的基础又使得民主不至于造成社会失序。政治发展的顺序不对——根据福山——平衡就很难实现。比如,那些民主先于国家建构的国家,往往陷入依附主义。“法治先于民主”,更是清晰明了的“英国经验”。当然, “顺序论”并非福山先生的独创,中外学界已经有一批学者(比如Jack Snyder, Michael Mann)这样论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先法治,后民主”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答案看似清晰,换到操作层面上,依然引发“然并卵”的困惑。首先,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政治发展三维度哪个强那个弱、哪个前哪个后,自有其历史路径和路径依赖,而历史不能改变。即使“顺序论”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也不可能让——比如希腊——为了进入一个英式的、正确的政治发展顺序而取消选举、取消中央政府的权力,而集中精力在希腊先发展“贵族对国王的契约式限权”;我们也不大可能劝说集权者穆加贝取消津巴布韦的选举,同时自己也宣布放弃权力,然后找一块空地与该国的纳税大户先打一架,再签订一个“大宪章”。
更重要的,是政治发展三维度内在的紧张关系。“顺序论”基于一个假定:当“好东西”依次进场的时候,先到的那个“好东西”不会阻挠后面的那个“好东西”到来,而后到的“好东西”又不会破坏前面的“好东西”。这种假定过于乐观。国家能力十分强大时,统治者似乎没有理由坐在头盖巾中温柔等待民主的到来;而民主到来时,也未必会温顺地投入国家能力的怀抱——卡扎菲政权下的利比亚,“国家能力”不能算不强大,然后当民主至少从形式上到来时,民主与国家能力不是相互叠加,而是相互摧毁。
事实上,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从顺序论的角度有六种可能的组合,这使得任何过于简洁的“模式”都显得可疑。比如“先法治后民主”这个说法——不错,英国的确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这似乎是对顺序论最有利的支持。问题在于,英国同时也是先有法治,后有国家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建构是发生于法治这个框架之内——忽视“先法治后国家建构”这个前提试图复制英国的“先法治后民主”,极可能导致认识上的刻舟求剑。在那些国家建构已经极端发达的地方,那些“国家能力”本身已经成为法治最大障碍的地方,还是否有可能“先法治,后民主”?站在1939年的德国,或者1937年的苏联,是否可能“先法治,后民主”?还是,这种情形下,只有通过民主进程弱化极端的国家能力,法治才可能从重压之下拓展出呼吸的空间?在此类国家,法治与民主与其说应该遵循“顺序论”,不如说只能遵循“同步论”。
当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药方”有没有用以及多么有用,政治问题不等于智识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药方”并非不知,只是难为:利益的、观念的、资源的束缚使得“通往丹麦之路”异常艰难。但是对福山这样的研究者而言,或许知识中的游戏乐趣已经足够精彩,政治上的回音只是锦上添花?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政治家采取行动,政治能够造成巨大的改变——更好或者更坏。书中关于哥斯达黎加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身处中美洲地带,周边国家的当代史上充满血腥战乱、政变、高度贫富悬殊,而这个国家能够在过去六十年保持和平、民主与环保基础上的发展,原因——根据福山——就在于不同派系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接受了宪政限权。历史上哥斯达黎加不是没有过内战与政变,但是1940年代保守派与左派“各让一步”的妥协使得政治发展得以可能。看来,无论什么政治配方、以什么发展顺序出现,政治家们的妥协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到达“丹麦”之前,还是要先到“哥斯达黎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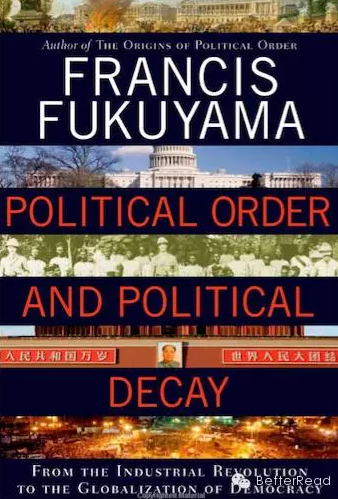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