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卡洛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
翻译:周雨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中,基础设施曾一度没能跟上意识形态的发展。于是在满足意识形态功能的建筑被设计出来之前,人们开始自己动手建设社区。当时的情形看上去像一种吊诡的倒置:革命领袖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奢华酒店里建立起他们“空想的共产村庄”(phalansteries),而工人阶级却在资产阶级那些大公寓里建立社区。那时,新的“无产阶级之家”还不存在任何建筑上的范例,甚至没有任何房屋大小或内饰方面的准则。于是建筑师们不久就开始创造一些未来主义实验风格的模型:立体主义的、环形的、塔状的、不对称的或是曲折的结构。不过与此同时,各部门与市镇很快也开始开展住房分配竞争,这个过程中终于渐渐地树立起一些设计规格上的严格惯例。
米诺维奇(Meerovich)的研究告诉我们,为苏维埃公民提供的住房分配政策虽然表面上宣称进步与平等,事实上它不仅仅是试图将工人们整合进一个个“劳动-生活社区”,更是一种阴暗的政治操控。为了把某些更好(或更坏)的住宿条件匹配给工人们,住房的“紧缺”变成一个必要的工具。被分配到额外面积的“居住空间”被看做是对国家效忠的最佳证明。住房竞争不仅明确规定了房间的数量和大小、房内提供哪些公共设施(如厨房、饭厅、托儿所、阅览室、洗衣间等等),它更是试图计算和规划生活本身的最低标准。例如,它测算人体在一晚睡眠之后需要多少必要的空气量就能“正常”运转,以此制定房内“生活空间”的体积标准。
这些准则被运用到不止是新建筑,更是那些老房子里。压缩(uplotnenie)政策把公寓的老住户塞到一个房间里,然后把其他房间填满新来的人。正如米诺维奇指出的那样,建筑师们本想要推广的那些“进步标准”实际上被破坏了:那些为单个家庭设计的小套间被塞进了好几个家庭,一个房间住一整家人;而为个体设计的单人间也是挤了好几个人。许多工人的营房里更是毫无隐私。人们于是争先恐后想要逃离这样的住宿条件,去抢那些更宽敞但也数量更少的房子。1930年代早期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居住制度从而变成了一种很系统的统治技术。当然,一个父亲形象的国家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建筑师们也对此毫不知情,他们继续设计着舒适的住房,并对过度拥挤表示抗议。而居民们,一方面忍受着对于“被统治”的恐惧和疑虑,一方面又试图去相信他们所住的片区是最优质的。
一旦这种居住体系被建立起来了,那些未来主义的社区实验就变得近乎多余。随着1930年代早期斯大林同化政策以及新传统主义的来临,这些激进的、大型共同居住的住房-社区实验就被完全地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规格化的、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的独立公寓。同时,那些从前被设计为社区的建筑,开始被改造为工人和学生的宿舍(obshchezhitie,意即“公共生活空间”),附属于工厂、建筑工地以及大学;而新宿舍也被建成多层、带过道的样子。因而,在所有类型的城市住房中,如果按照舒适度排列,集体宿舍可以被排在那些不供暖的木质窝棚与工人营房之前,排在老式合住套间与公寓楼独立套间之后。
于是,这种宿舍成为了那些没有自家公寓的人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在大规模劳动力迁徙、普遍房屋紧缺以及持续不断的城乡流动压力等情况下,这种宿舍在所有城市被大量建造。对于许多有理想抱负的流动居民而言,住在集体宿舍里变成了他们一个共同的人生阶段。如果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有一份稳定富足的收入,且分到一套自己的公寓,甚至是一套乡间邸宅的话,住在集体宿舍里可以视为是一个道德成熟过程中的过渡阶段。
乌杰辛(Utekhin)的以下这段评论传达出了在苏联时代中期,集体宿舍具有怎样基础性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是如何制造集体情感和消灭自私冷漠的:
集体宿舍—不论在它最宽或最窄的意义上—都被那些和善的人视为一段宝贵的经历,它培养了一种苏维埃人的性格。正如它的官方说明上写的那样:“……这种以艰苦著称的居住体验其自身就包含一种益处:它是一个学校,教导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自己做斗争、如何培养同志友情。”
据克拉克(Clark)发现,在1950和1960年代一种名为“英雄的回归”的小说类型中,集体宿舍是很常见的场景。这种小说的关键主题是:主人公如何才能融入到成人社会中去?首先,他或她必须离家远行,走上一条标志着道德或是政治进步的旅程。通常,那个将要去到的“远方”会跟赫鲁晓夫时代的某个新的建设项目联系起来——西伯利亚的一个建筑工地、处女地开垦计划等等。或者,主人公来到城市寻求教育。在小说的开头,他或她往往很不正经地只是想跟其他学生一块儿找点乐子。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情节:一个道德认同上的转变阶段。工作的最初几天常常是对毅力和耐力的考验。在库茨涅佐夫(Kuznetsov)的小说《传奇的延续》(1957)中,主人公托尔亚(Tolya)被安排去铲混凝土。“我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呢?”他问自己。一天结束的时候,托尔亚手滴着血,只剩下最后一点力气把自己的身体拖回宿舍,并爬上那“高而又高”的楼梯,回到他的寝室。他最终战胜了自己。
在这里,宿舍的楼梯可以被视为一个完美的意识形态象征,象征主人公道德上的进步和上升。在这个故事中,体力劳动的价值与在底层的卑微生活将被理想主义与冒险所升华。然而在《传奇的延续》中同样明显的是,官方意识形态自身也投射了想象。在新世界中,托尔亚感到“童话成真了”,那是当一个工人讲起了关于伟大的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是如何汇合的古老传说,而这正是托尔亚所参与的建筑项目的目标。托尔亚有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童年异象,是“在蓝色的海洋中航行着许多红色的船只”;而当他在建筑工地上辛苦地劳作时,在一片飘扬的标语横幅之中这个异象又突然浮现出来。这部小说清楚地表明,苏维埃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剂无聊而受限的处方,更是一套高度复杂的话语,其本身就包含了浪漫的元素以及潜藏的威胁。
在我开始分析这一主题之前,请让我再多探讨一下集体宿舍的社会空间与建筑结构。从功能上来说,集体宿舍是那些外来者在本地的寄居之地。宿舍的形式各异,根据它们所依附的机构特点而有所不同(军队的、工业的、院校的等等)。任何在俄罗斯住过的人都知道,甚至每一个学生宿舍都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有给乡下人住的农业院校宿舍、聚集着哈萨克人和西伯利亚人的宿舍、给工程师们住的闹哄哄的宿舍,在市中心还有给艺术学生住的漂亮宿舍等等。邻近宿舍的居民们时常与彼此展开竞争,比如足球赛,或是一种象征性的敌对(像是从窗口挂出侮辱性的标语来激怒邻近宿舍的人)。非本楼居民禁止进入宿舍,除非持有许可证。因此,当有派对或舞会举行时,年轻人在门外排起长队,等着兴许能随机交上一个“朋友”以便借他的门卡用一晚上。然而,从我所能考察到的各方面来看,在整座宿舍建筑中,最能使人对其社会属性产生丰富想象的部分,并不是它最明显的外部特征,而是它的内部建造结构是如何被设计的。
在1950到70年代的大规模修建时期,曾有过对房屋结构的标准化修建规定,虽然那些更老、更多元化的宿舍依然在使用中。通常,入口通道处坐着一个看门人,负责检查谁进门了、谁出去了,负责锁大门、关灯等等事宜。一层是宿舍主管办公室。沿着宿舍楼的中心是一条宽敞阴暗的过道,两边依次是各个合住的寝室。在一些高端宿舍里每间寝室只住两个人,但在一般的宿舍里通常是住四到六人,有时甚至多达十五人。铁床、衣柜、小橱柜整齐排列,通常由围帘隔开,从而每一间寝室都是一个拥挤而复杂的空间,组合出更多的私人与公共区域。房间中间通常放着一张公用桌。墙上装着一只收音机,不能关掉、只能调小音量(我的记忆中是这样,至少是在1960年代)。楼外的竿上或树上也挂着广播扩音器,转播着同样的节目。在宿舍过道的一头是一个大大的公用厨房;另一头是盥洗室和洗衣机。装修较好的宿舍会有一个叫“红色角”的房间,用于进行政治教育,但后来往往更多被用于自习。最后,大型的宿舍在底楼或地下室会有个食堂。食堂里往往排着长队、桌椅拥挤,人们吃得飞快而非悠闲进餐,因为食堂只在有限时段内开放且分批次供应。
这种从波罗的海地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都随处可见的宿舍结构,被设计出来贯彻关于平等、节俭、公正公开以及集体责任的理念。到1966年时,许多这样的宿舍都已经过于拥挤,比如经常没有足够的洗衣、盥洗设施,一个厨房要给六十到一百人共用,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学习与休闲区域等等。考虑到这些状况,一套新的规定出台实施。然而,到1970、80年代时,新一代的宿舍却被设计容纳更多的人—最多达到1300人—人均居住空间从4.5平米缩减到4平方米。只在极少的新宿舍中,原本沿走廊分布的房间被改善为围绕公共设施来分布。不用说的是,老宿舍还是继续运营。
考虑到苏联各国的宿舍都没什么大的不同,我们继而可以开始论证:这种建筑结构是如何危及而非贯彻了苏联意识形态。这是由于许多设计细节必须照顾到普遍的建筑施工问题,例如材料的节约成本、光线的充足情况、排水系统等。从而,即便宿舍的整体结构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认为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携带了明确的意识形态意图。或许正是由于缺乏精确性,宿舍中的生活其实是根据实地经验由个别苏维埃机构来具体管理的。管理的执行者包括管理员,即一些被指派来维持秩序的工人/学生积极分子。每一层楼都有一个管理员,他们组织住户进行各项工作(打扫过道、清理厨房、倒垃圾等等),并对醉酒、打架等违规行为进行训斥。在某些宿舍,每间寝室里都有一个管理员。除了管理员还有告密者,他们专门向宿舍主任等权威悄悄通报住户所犯的政治错误。这些监管行为都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象征着社会主义的责任心、对他人的尊重、有教养的行为以及政治忠诚度。然而这些监管被实际实施的方式在每层楼却是风格各异——例如,二楼厕所可能打扫得比较干净;在八楼可能有传闻说某某是告密者;而四楼的乌兹别克人则永远占据着厨房在煮羊肉。
住在寝室里,你不仅可以听到室友们的各种活动,还能听到从两边隔壁房间传过来的噪声。乌杰辛曾写到,人们不仅适应了这些隔壁来的声音,而且还潜意识里欢迎它们。他引用了一首1960年代的诗:“我喜欢墙那边传来—音乐/当墙那边传来—噪音/我无法忍受那来自安静的/冷漠,如此浓稠又浑浊”。对一个共产主义信徒而言,搬出拥挤的公共宿舍去住公寓将是一个痛苦的创伤,因为那将意味着对他人的冷漠,他们对这种冷漠中包含的罪恶深感恐惧。乌杰辛认为这种情感在1960年代意识形态浪漫化的时期最为强烈,但这种对于告别集体生活的焦虑并不仅限于激进分子,而且在之后的年代中也持续出现。一位来自布里亚特的朋友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谈到在1970年代晚期当她必须离开集体宿舍去住独立公寓时她忍受了多少无聊和孤独。这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宿舍中的生活通常比宿舍的规划者所设想规划的还远要集体主义得多—事实上,它创造了一种 “过度的集体性”。
这种集体性一体两面,一方面它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它也残暴压抑。寝室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处于这种集体性的核心。还是那个来自布里亚特的朋友,她告诉我她同屋的四个人加上附近寝室的两个姑娘组成了一个小组织,有自己的组织名称、歌曲甚至“行话”。钱被放到一个公用罐子里,食物被共享,不论做饭还是吃饭都结伴进行,到晚上也是组队出去玩。她们一起去洗澡、洗衣服;甚至内裤和内衣都被传来传去。曾有一个外来的姑娘通过分享自己新得到的大床而被允许加入,其他想加入的人都在开会表决后被拒绝。她们会走到公共走廊里大声唱自己组织的歌。不出所料的是有一个学生曾多次伸出头来就她们发出的噪音表示抗议。然而她们每次都大发一番脾气然后把他推搡回自己的房间去,直到“每个人都承认了我们在这层楼的权威。从那以后,无人敢挑战我们。”我的朋友回忆道,“那真是一段愉快时光,我们没有管理员,我们有的是集体精神。” 然而,这种精神无法遵循苏联集体宿舍所意图推广的那种自律、公正理念。不过我的受访者都常常提起这种温暖而愉悦的“精神”,并且有证据显示这种“寝室-过道”的组织结构也在许多其他年代和地区产生过类似的社群关系。一个1930年代的例子显示,有一个小组织曾写过同一本日记,而且跟那位布里亚特女士一样,组织的核心成员(kostyak,意即“主心骨”)直到他们离开宿舍很多年后都依然维持了朋友关系。
这种强烈的集体性所带有的黑暗面,则是它加诸人们身上向它臣服的压力。在一个学生的一封家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讽刺段落:
亲爱的爸爸妈妈,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正坐在我寝室的门口给你写信,因为他们不让我进去,说今天没轮到我睡……其实,其他都还挺好的。同楼层的朋友接受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但这意味着所有我的东西从今往后就都是集体的了,甚至是戈沙叔叔从蒙古随果酱一起寄来的克林普伦裤子。他们把它当做入会费给没收了。现在每个人都想穿着它结婚。其中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意大利黑玻璃但是是坏的。所以,爸爸,请不要给我寄马裤了,马裤实在太公共了,整个组织都会想穿它们。给我寄钱吧……
一个宿舍住户回忆道,保存贵重物品的唯一可靠办法是锁进手提箱里,最好绑在床架上。另一些俄罗斯朋友提供的记述中提到,某些没能遵守房间规矩的人被迫替人受过或是被放逐。最近一部关于俄罗斯军队的民族志也讲述了军中严厉残暴的服从和层级关系,例如在浴室、食堂、医务室,被排斥的士兵是如何被严酷地处以私刑和监禁。
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应该期望宿舍中的排斥和霸凌只是个别现象。另一方面,宿舍住户有时也需要空间来进行私密对话。寝室里总是永远被占据着,几乎不可能是空着的;厨房里太容易被旁听;浴室不仅太冷而且小隔间里太容易躲着偷听者。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是,过道这个最最公共的空间,反而最能够提供“隐私”。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过道视为一个拉图尔(Bruno Latour)意义上的行动体(actant)。住户们离开自己的房间“走到过道上”去谈话。正是那过道的宽敞和黑暗,利于四周观望、半隐半现的微笑以及秘密的交换。人们每次都悄悄走到过道里,有时是手挽手。一旦你听到他们缓慢的脚步声,就明白他们要开始私密的谈话了。同样的,楼梯也是一个开放的隔离带,用于违规的吸烟、喝酒、交易和午夜亲吻。然而,这种隐私依然是一种公开的隐私。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集体宿舍中的社群关系与想象?集体宿舍绝不仅仅是隐喻而已,虽然苏联作家们确实创造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隐喻,例如将集体公寓比作“寡妇之船”;它们也不是寓言,像是在卡扎科夫(Kazakov)写的《小车站》(1962)中,一个乡村火车站被用于象征苏联式野心所导致的所有那些伤痛离别。而我在本文里讨论的集体宿舍,它的物质结构本身就切切实实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运转。虽然这种影响并不完全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从这一点看来,建筑能够像一个棱镜一样运作:它将意义聚集起来又发散开去,然而并不是以随机的方式。正如一个棱镜的表面数量有限,它所折射的光线也是带有固定方向的。
本文节选自《建筑与苏联想象》,选自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学刊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05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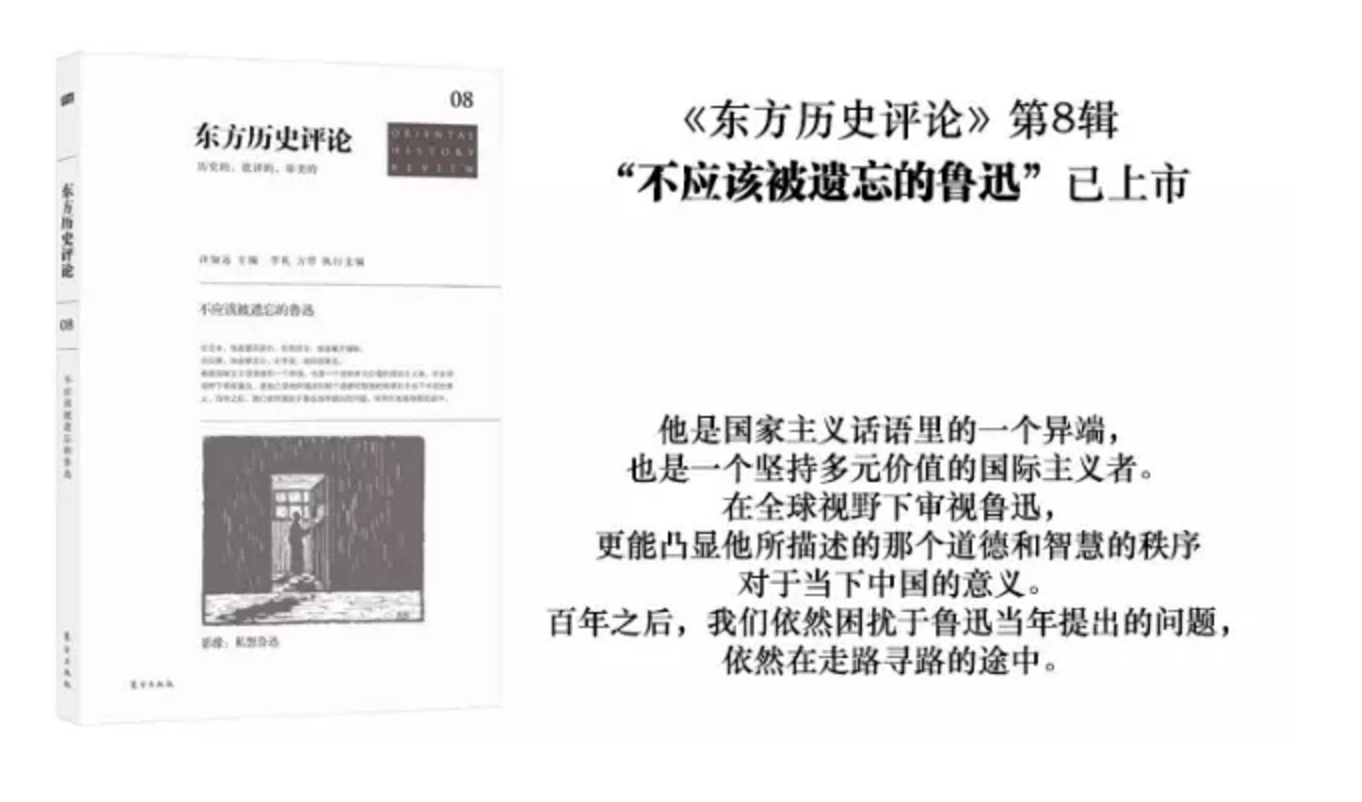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