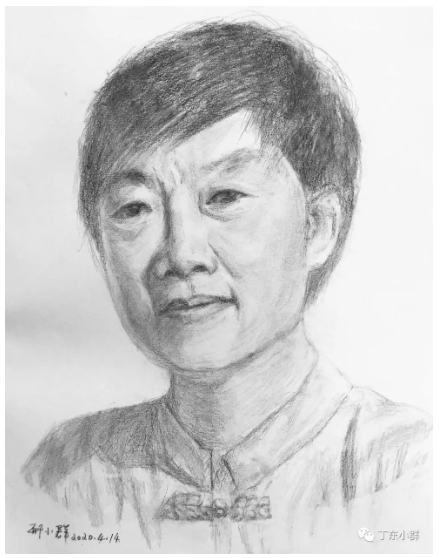
和崔卫平相识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小群曾在《诗刊》当过一年编辑,崔卫平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没有房子,她只好和先生暂住《诗刊》编辑部。我们在这样的场合见了面,但谈不上更多交往。
1990年代中期来往渐多。当时,我们住在新街口一带,她住在小西天,距离比较近,走动比较方便。崔卫平喜欢写文章,我先后为几家报刊做兼职编辑、策划,免不了向崔卫平约稿。
王一方在青岛出版社策划了一套《野菊丛书》,第一辑六种,其中有我的一本《尊严无价》。丛书投放市场后,反应良好,于是王一方约我策划第二辑,再出六本。小群的右派系列采访文章编为《凝望夕阳》,成为其中之一。崔卫平反思知识女性的随笔,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我也约她自编一本,取名《带伤的黎明》。她后来出了很多文集,这本是最早的。加上蓝英年、林贤治、马斗全、程映虹四人的文集,合称“野菊二集”,于1999年初问世,读者也很欢迎。
崔卫平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文艺理论。不少社会热捧的明星,都是她授过课的学生。但因为她不看电视剧,对于学生的走红,往往全然不知。她更关切的是另一类影视。世纪之交,独立电影在中国悄然兴起。崔卫平、郝建等教授,成为热心的扶植者。当时,不少独立电影人拿着没有机会公演的作品,寻求崔卫平的帮助。崔卫平就在自己家中,邀请朋友,小规模观看、研讨。我们有几次应邀参加。印象最深的是胡杰放映了《寻找林昭的灵魂》。那是最初的版本,一些电影界朋友,从纪录片的专业角度,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改进意见。我则从思想上引起了深度共鸣,由此和胡杰成为好友。还有一次是王超放映他自编自导的第一部故事片《安阳婴儿》,我们也很受感动。由此让我们感慨,中国编导不是拍不出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故事影片,而是这种影片很难通过审查,和广大观众见面。
崔卫平和唐达成夫人马中行是电影学院的同事。马中行比崔卫平年长20多岁,但她们关系处得很好。唐达成去世,马中行精神上受到重创,崔卫平常去宽慰她。陈为人撰写《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这本书定稿前,我和崔卫平都参与过意见。整体上都给予好评。但尾声《病中吟》写得十分悲怆,马中行因痛苦而不能接受,要求删去。她请崔卫平把关,得到了崔卫平的支持。我主张保留尾声,和崔卫平当面争辩。后来张凤珠和赵赵也表达了和我同样的意见,这才保留下来。
我还和崔卫平参加过有关大学人文教育的活动。几度聚会的余兴,她翩翩独舞,令人难忘。环境再严峻,她都力求积极生活,乐观应对。
崔卫平是《李锐口述往事》的最早提议者。那是2002年,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建议和李锐老做口述历史。李老早就有此想法。我和他联系后,一拍即合。崔卫平和我一起去木樨地李老家中谈了几次,她先生王绥琛摄像。后来,她有别的事,没有再参加。王绥琛将录音文件转交于我。我又继续录音采访。文稿曾搁置数年,最后李南央参与,终于推动李老在96岁时定稿完成。
崔卫平还参与了很多有影响的公共事务,这里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说,那就是她把一些东欧思想家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思想资源。她译的书包括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哈维尔文集》由李慎之作序,《通往公民社会》由何家栋作序,但都没有出版机会。李慎之在序言中说:“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李慎之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崔卫平。李慎之去世后,她不但写了悼念文章,还把《哈维尔文集》自印出来流传,影响了老中青几代热心读者。包括哈维尔本人,生前得到了这样印刷的中文译本,后来又见到崔卫平本人,也格外感慨。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