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文学技法和文学伦理并非「无法批判」的禁忌之物。在 2015 年凭借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火遍全网时,余秀华就曾被人批评「她诗歌中艺术性还没有达到今天诗歌的写作高度」,并详细列举了理由与分析 —— 这都是合理范围内的理性讨论。那时候,余秀华还以为,在外界的热捧和猎奇褪去之后,一切喧嚣都会过去。
五年之后,她又一次以 #余秀华键盘侠克星# 这一微博热搜成为焦点 —— 因为一首对歌手李健的表白诗,以及事后她在评论区和私信中对批评她的网友毫不留情的回击。但这一次,被余秀华回击的部分网友显然不具备文学批评的自觉,而是为了让她禁言、闭嘴。最客气的,是用「别人未必想听」阻止她表达公开对李健的情感;更多的,则是把谩骂的矛头指向她残障的身体,或是将她称为「荡妇」。

时至如今,为什么关于文学和诗歌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偏激?网友对余秀华批评和骂声大多都集中在荡妇羞辱上,这种谩骂内容的单调是否与她的女性角色有关?在舆论场上,为什么拥有性觉醒意识的女性特别容易遭到围剿?
其实,多数网友对于余秀华的愤怒,恰恰反映了他们将女性视为「第二性」附属物的潜意识 —— 她们的情欲、情绪和言谈,都被要求束缚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些批判并不是指向余秀华的脏话,而是指向她对于情欲和自己愤怒的表达。事实上,脏话是近乎人人都会听到和曾经使用过的。对此,鲁迅曾经写过一篇《论「他妈的!」》,将这句脏话列为「国骂」: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在微博上,余秀华的反击被截图后,引发了大量转发。有人将她称之为「加强终极版史航」,后者作为一名在微博拥有三百多万粉丝量的编剧,也经常用脏话「挂人」,并因此在社交网络上惹起争议。不仅如此,普通网民的谩骂在目前暴戾的网络环境中也随处可见 —— 他们都没有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余秀华此次成为众矢之的,就是在男权文化对女性畅然表达情绪的禁令下,遵循男权文化规则的人对公开违背者的愤怒声讨 —— 特别是,她还是在公开场合「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情欲。

在男权文化里,女性应该是噤声的,她们自然地被视为「聆听者」,应该默默地聆听男性关于爱情、时事、政治以及其它一切事情的态度和见解,并表现出认可和崇拜的模样。这种情景出现在男权文化的几乎所有权力关系中,在酒桌上尤为明显。
美国女作家 Rebecca Solnit 在她的著作《爱说教的男人》(Men Explain Things To Me)中,将这一现象解释为「mansplaining」。她在该书中描述了一次聚会上的场景:一位男士滔滔不绝地就某一专业问题向她介绍一本相关的书,而她只能微笑着保持沉默,而她本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对于余秀华来说,无论那些网友在评论区和私信中使用的话术是什么,是所谓的「理客中」还是直接进行暴力辱骂,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让她不再书写。作为诗人的她,被网友们要求在她自己的专业领域 —— 诗歌上保持沉默、不再书写关于她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欲望。
有一种说法是,相对于过去,在综艺节目上,「真性情」的女明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喜爱,女性的表达似乎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保障。但我们绝不能仅满足于此,当她们的表达和认知一旦进入深水区,或者对准某些被视为「男性特有」的领域时,就会遭到抵制与嘲讽。

在蔡玉萍的《男性妥协》一书中,作者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收入主要由女性提供的家庭中,男性发展出了一种既保障了自己尊严,又在名义上给予了女性自主权的自洽话术,即「家里的小事,女的做主;大事,男的做主。因为男的比较擅长谈论这些事。」而在男权文化中,「情欲」就是被视为独属于男性可以谈论和享有的特权。不过余秀华并不以为意,她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来,封我为荡妇吧,不然对不起这春天浩荡里的遇见……走吧,我们去后山大干一场,把一个春天的花朵都羞掉
在传统的异性恋模式下,男性被视为性与爱中更主动的一方(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社会文化上),被视为亲密关系中的权上位者,因此他们更有资格谈论性与爱。而主动讨论性与爱、表达自身情欲的女人,不仅会被质疑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上发言,更要承受来自整个男权文化的荡妇羞辱。

但事实上,这种关系模式只是男权文化熏陶的产物。日本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一直以来在家庭中付出了大量包括家务、照料后代、发展抉择等事务,但这些「再生产」的劳动并不被社会计算在内。相反,人们只看直接劳动带来的生产成果:金钱、产品、业绩 …… 家庭只以带回家的钱作为权力分配的标准,却忽略了创造这些劳动背后所需要付出的再生产成本。因此,这种原本只存在于劳动领域的分野,被男权文化加以利用,扩展到了权力关系之中,被视为应然的上下位关系。
19 岁那年,余秀华和大她 12 岁的尹世平结婚。在余秀华口中,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丈夫性格暴躁,斤斤计较,把「女人是个猪」挂在嘴边。尹世平从湖北荆门打工回到家,两人就经常吵架。直到她成名之后的 39 岁,他们才顺利离婚。

导演范俭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感受到了人们对余秀华的「男性凝视」:在一场关于余秀华的诗歌研讨会上,一群男性聚在一起分析诗歌中的表达是否恰当。
她曾对媒体说,爱情像信仰,信则有,不信则无。下辈子,她希望有个人在她 19 或 20 岁时走进她心里,因为那个年纪像花一样。2018 年,余秀华在微博写道,「给李健写 10 首诗歌,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今年,这一条微博又被翻了出来,作为网友证明她是「荡妇」的证据。
之所以采取荡妇羞辱,或许正说明了在他们心里,「女性失去矜持和贞洁」是一条在他们眼中对女性有效且伤人的指控。这种狭隘让他们默认陷在「女性没有性主体性」的前提和「荡妇羞辱是有效的」的错觉之中,来回反复。但在余秀华的眼里,这样的指控可能软弱而无力。她曾说,现在的婚姻和男女亲密关系都是自由的,「真的无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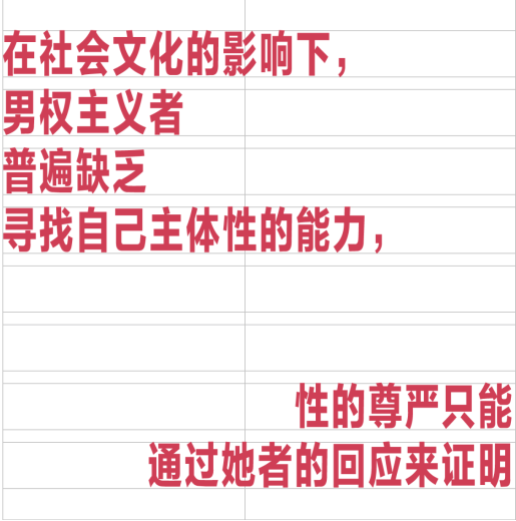
然而网友却认为,男性作家(以及所有男人)对于情爱的表达和评价都是正常的,最多只是「尺度不当」而已;但若女性这样「放荡」,可就真跳了脚。这种看起来「过激」的反应,正反映了他们对于男人的主体化不得不依赖女人这一悖论的敏感。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男权主义者普遍缺乏寻找自己主体性的能力,性的尊严只能通过她者的回应来证明。因此,他们不愿意面对女性的情欲觉醒,这将进一步挤压他们原本的性主体空间。
1976 年,余秀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由于乡卫生员的失误,当余秀华刚刚睁开眼睛还未来得及啼哭,她的脐带就被剪短,造成了脑部缺氧。直到出生后的第四天,在她的躯干四个角落被打了四针之后,余秀华才终于哭了出来。但缺氧还是导致了她的脑瘫,行动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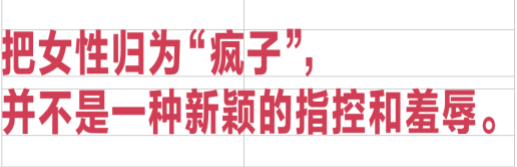
在微博上,「女疯子」「女脑瘫」成为了网友对她的谩骂之一。事实上,把女性归为「疯子」,并不是一种新颖的指控和羞辱。从中世纪的女巫,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再到现当代港媒对女明星的丑化,「女疯子」的意象从来没有从人们的围观中缺席。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eraison)中提到,疯子只是被主流排挤的异类,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在父权制的挤压下,这些所谓的「女疯子」只是不遵守男性特权规则的女性,男权用这种指控来加强对女性的控制。对于出逃的女巫,中世纪的人们选择绑在十字柱上将她烧死;对于情欲觉醒的余秀华们,男权文化的信奉者们则选择用语言的暴力和羞辱来「处置」她,并幻想这是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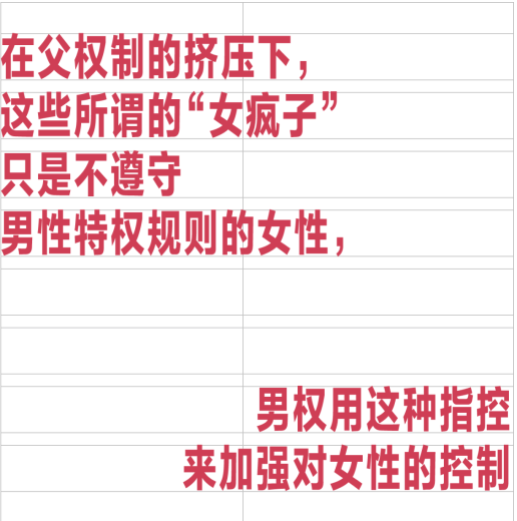
2015 年,在余秋华的诗歌分享会暨读者见面会上,李健发来了一段视频,他说,「这种诗歌是我最心仪的,因为它特别纯粹。」而在屡次经过和网友的论战之后,余秀华仍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诗歌,时不时会提到关于李健的种种,她在微博说:「在这个肮脏龌龊的世界,几句脏话算个屁!」
表达的权利,不应只在文稿中,也不应只是在言语论战中被引用的工具,它体现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时,究竟能被远离指责和干预地实现多少。诗歌的能量,也许就在于那植根于诗人自身的固执与坚定,通过一行行文字,得以传递给所有读到它的人。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