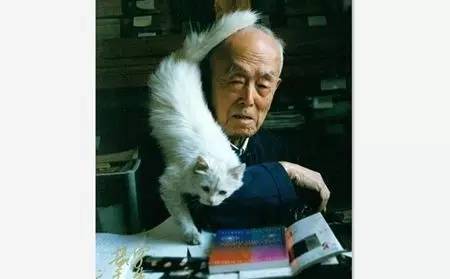对话的意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一文的缘起,其实可以远溯到对早期的中文社交媒体的观察——我是这类媒体最早的用户之一。在2007-2009年前后,这个圈子还不是很大,几乎是个熟人群体。该群体不乏同心同德或者同仇敌忾的时候,但在更多的场合,就如你所能预料到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有几位我所尊敬的知名网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饭否和Twitter上,互相骂阵,真的而且忘记了他们是在一个公共场合这样做———这就好像有人天天在你们家客厅吵架,你想谈点正经事都不行。这事让我心生很大的困扰。
我不关心私人领域的是非曲直,我关心的是中国互联网上的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尤其关心在网上可否推行有效的对话。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无法对话。网络上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块对话试验田,数位也号称网上意见领袖的精英,其意气用事如此,试验如何进行得下去?
对话的意义是怎么夸大也不过分的,因为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我在文中引用查尔斯·泰勒和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话来论证,人类的生存是对话式的。由此,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即每一个人是否会对话的问题,并列举了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答案,包括哈维尔等人的答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维尔的8条《对话守则》,大概我是最早在大陆予以扩散的。
这些守则简单而实用。遵守这样的规则,对话才有效。可惜的是,在网上,就连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都常常不能用它们来要求自己,更何况一般的网民?我为“网络精英”们轻率的人格攻击、粗俗的自我陶醉和炫耀以及一言不合便拿出的狂妄而空洞的威胁恐吓而感到难过。我尤其在意一位有影响力的网人所说的这句话:“除了我认识的人之外,我一直都是谁关注我我就关注谁。希望那些主动关注我,在我关注你们之后又取消关注的人告诉我一声,以便我取消对你们的关注。”回声室里的声音,是不能当作大自然中五音杂陈的天籁的。
说话的权利
发表意见就是说话。关于“说话”的“话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说”。在中国,尤其难说。
为什么难说呢?看看中国一些大知识分子的纠结就知道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正在调养中的季羡林,祝贺季老96岁寿辰。当时温总理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的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出身贫寒,一生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季老回答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并解释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季老是“国学大师”(尽管他本人不认可这项桂冠),从这段纠结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心结。无独有偶,另一位大知识分子,文学泰斗巴金,“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然其代表作《随想录》,用陈思和的评价来说,“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出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而且,就算巴老晚年直率地说了真话,你也不免心生悲哀:在中国生活,只有到了晚年这“一头”才能“真”么?年轻时在做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巴金先生有两句描写:“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显然,“豪言壮语”有淹没真话、吓倒真话之效。
2011年4月温家宝在中南海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承认“我们鼓励讲真话”,然而“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讲不了真话,不想说假话,那沉默总可以吧?也不可以。
1953年,胡适在台湾接受曾虚白访问,指出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由此认为“沉默的自由”是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人权。这段话随着新中国历史的进展,被证明为惊人的远见。1957年,知识分子被破天荒地动员“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结果却是一场“阳谋”,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钓鱼”。吃了苦头的知识分子懂得了“祸从口出”,暗自想不说话总可以了吧。他们没有想到,更厉害的还在后头。那就是剥夺你的“沉默权”,强迫表态。
史家雷颐先生有文曰《表态的“艺术”与“胆魄”》:“凡‘运动’一来,人人都要表态,没有沉默权;而且必须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态度来‘表态’。”这种当众表态、人人过关的方式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如此一来,华夏大地陷入一片“万马齐喑”的失声状态,就成为必然。那个年代宣扬的是“万众一心”,而万众一心的表现,必然是“万口一辞、万言一腔”。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有个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话份”,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而这种习用,到了众人连自己都不知的地步。有最大话份的人,当然是当权者,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
这种话份的最好象征物,就是大喇叭。凡是对文革岁月有记忆的人都知道,曾几何时,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间学校,每个广场,都矗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
70年代出生的贾樟柯,他的“县城”体验,即一种中国内地小城镇的文化和社会经验,在电影《站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又是通过运用背景影音媒体所传达的声音和图像来暗示人物所处的历史时间,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媒介物就是大喇叭。
无论是调看早先的影音还是翻阅国人的个人记忆,“大喇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意象,形形色色的“喊话”也早已成为记忆中的“背景音”。上海的评论家吴亮接受杂志采访,问听什么歌长大的,他答“听高音喇叭里的歌长大的”。那不是音乐,而是声音。80年代,有人开始练琴,弹钢琴和拉小提琴。到一个朋友家,把窗帘拉起来,留声机插好,那种感觉,后来人无法想象。所以,吴亮说,“我记忆中不是音乐,而是听音乐这回事情给我印象深刻”。
大家都说一种话,都听一种声音,这件状况终究不能持久。正如一众“蓝蚂蚁”终将让位给争奇斗艳的帅哥美妞,你无法把一切个人化的东西都归零。
我们知道,在暗夜里最先睁开眼睛的总是诗人。中国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十年,我们对北岛的“我不相信”、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都耳熟能详。顾城的这首诗的名字不是别的,正是叫做《一代人》。这代人首先要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那是多少年来被压制的声音,北岛称之为“被判决了的声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回答》)。
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降的中国互联网,在精神上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存在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1986年,在深圳曾经有过一场现代诗大展。发起者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敬亚。1986年7月5日,徐敬亚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50多封邀请信。在这封手写的信中,徐敬亚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地道尽了互联网精神?诗人杨黎曾经感慨,当时的中国有太多限制了,诗展的推出,让大家“在这一瞬间都自由了”,有了“说话的权力”。接下来,诗歌在商品化大潮中衰微了,王朔说,在“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文学强迫自己冒充一股社会势力的现象被终结了”。
诗歌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让我们真正有了“说话的权力”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互联网。
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
互联网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12年3月6日的记者会上,阐述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
把这段话用来形容有了互联网以后的中国,也不无贴切: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地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拥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当然,弱势群体也伴随着技术和表达能力的障碍。大多数穷困者和为数不少的少数族裔人群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很多人甚至难以接触到数字媒体。)“话份”获得了民主化。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传播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正如我的一本书的书名所说,就是“众声喧哗”。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这种进步的意义和价值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
钱钢说:“多灾多难的中国百姓,有隐忍沉默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还利于民,人民权利意识苏醒,鸦雀无声,变为众声喧哗。百姓有种种诉求,诉求有时也会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
首先要承认,这是个重大突破:隐忍沉默的传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被打破,而且,一旦打破,再重归沉默就成为不可能。其次,多年鸦雀无声之后,大家不太会说话,常常情感战胜理智;或者,只会说“话份”垄断年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混账话”;或者,只顾自己说,而不听别人如何说,凡此种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形,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只有“人”,才会说真话
互联网为中国人历史性地提供了表达空间,但却未能造成理想的言说环境。戾气十足的公共对话遍及朝野:名人对骂,公知约架,只有站队,不见是非;高官骂不爱国的人是“败类、人渣”,主流媒体称揪出的“大老虎”为“叛徒、国妖”,整体而言网络语言的粗鄙化,对互联网形成公共领域的能力构成严重挑战,也使寻找社会共识的努力格外艰难。
当下网络的整体粗鄙化,是全社会弥漫的戾气在互联网空间的真实折射,其又同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和挑战息息相关。属于互联网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法律的手段予以解决,但属于社会的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建设和治理,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社会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工作,容不得急躁,但或许当务之急是先从改变当下的网络话语习惯和体系做起。一场又一场的骂战喧嚣终会平息,但它们对于互联网生态带来的损害却是长期性的。在“革命”和“战斗”文化的浸淫之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话语惯性导致人们在网络上很难展开公共说理,议论和批评动辄变成人身攻击和意气之争,凸显了公民理性的缺失和民主对话的低能。互联网对话,追求的应该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压制异见,更不是语言暴力的宣泄。
专研博弈论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约翰·奥曼证明,如果人们能够充分交流,而且都是理性的,那么人们之间不可能在给定事件的判断上存在不一致。换言之,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由此可以得出的推论是,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或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使得他们漠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或与已形成的观念不相符的信息。
互联网中的对话,只能是在理性和真诚的态度下,才可以成为自由而可持续的。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表达很多,对此忧心忡忡的智者不少,比较悲观者如茅于轼,甚至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
其实,学会说话的唯一方式,是在一个可以说话的空间里不断练习。而更为核心的前提,则是要成“人”。只有“人”,才会说真话,“非人”不会说真话。有“人”的独立,才会有社会的独立;有“人”的主体性,才会有国家的正当性。最终,对“说真话”的呼唤,指向的是如何建构起自我认知,具备自己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