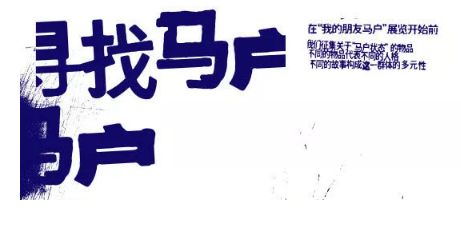2013年我从北京徒步到广州的路上,
有个网名叫“驴”的人来陪走。
她真的很像驴,沉默、脾气倔、吃苦耐劳、有双非常大的眼睛。
后来我说:“不能老管你叫“驴”吧,太不顺口了,
把驴字拆开叫“马户”好了”之后她便一直用马户这个名字。
马户想当快递员,只因为她是女生,被中国邮政拒绝了。
她和中国邮政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开始全职做就业性别歧视的议题。
2015年马户查出得了躁郁症
2017年躁郁再次发作住院,今年的5月马户告别我们回了老家。
她走之前,我们进行了大概有10个小时的采访,这是一场久违的长谈,我们一起梳理了马户至今为止的经历。
相关阅读:
2017年,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女权行动者不断地被迫搬家。国保(国内安全保卫)四两拨千斤,凭着警察的身份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一边吓唬房东,一边装好人。我们陷入了不断与房东交涉和搬家的循环,一年内被骚扰5次,搬了3次家。
原因说起来好笑,居然是为了2017年底要在广州召开的财富论坛。国保来找我们之前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论坛是什么,原来是一个美国杂志办的活动,届时会来很多高官富人。我们惯常被抹黑为境外势力,现在他们为了和境外势力开会,用了这么多心思就是为了让我们这几个女孩子搬出广州。
失去了居住的安全感,时常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余下的力气都用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再看着它们被一个一个404。我想这也不是女权行动者的独特经历,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环境的收紧。
这段时间马户还是充满了激情和希望,因为她参加了一个艺术策展工作坊
无边无际的讨论
“终于可以接触到所谓的艺术家啦,而且议题也是自己感兴趣的”马户说。工作坊参与者一半是做公益的,另一半是青年艺术家。这个活动想探讨策展还能做什么;策展不光是艺术家和策展人在搞,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听大家天马行空的聊天,马户像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如同当年去参加徒步接触到做女权运动的人一样。
“那个讨论是共识制的。哎哟,讨论个问题特别困难”马户说。这个讨论不控制时间,不控制发言,谁都可以插话,讨论起来无边无际的。马户和另一个有过协作经验的人都受不了了,找主持人说:“这样太没有效率了”主持人还是坚持这样的方式。
“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充分讨论和表达之后才知道大家想做什么”。的确,在探讨了1000种排列组合的人际关系,打破了1000种身份之后,大家马上就有了一个很有成效的结果:要从个人的点出发探讨抑郁情绪,这个点就是马户,展览的名字定为“我的朋友马户”。讨论期间大家也渐渐的互相了解成为了朋友。
零界点
马户特别兴奋,连轴转了20天。展览的第一次推广是收集和抑郁相关状态的物品,叫做“寻找马户”。征集文案里写道:
“马户是谁?ta是一位虚拟又确凿的朋友,也是所有与马户相似的人。通过对马户这一形象的集体塑造,我们希望回应在抑郁状态中生存的个体面对的复杂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与自身的博弈。在这种多面向的追问中,马户的处境又时常引起我们的共鸣。如果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可以更了解朋友“马户”,是不是同时也更了解自己呢?”
收集进行得很顺利,不管是做艺术的、做公益的或者对抑郁感兴趣的人都很关注。马户还把消息发给了自己家人,一直盼望女儿可以当艺术家的爸爸看到之后非常开心。
没想到正式的展览预告发布的第二天就被删了,参与者们觉得莫名其妙。更夸张的事情继续发生,当晚发布消息的公众号被删·号了;隔天知乎、豆瓣等平台的消息全被删除了,“我们被全网封·杀了”马户说。
炸开了锅
维稳办、街道办、宣传委员会三个部门一起去找主办方谈话,来得气势汹汹。来人说:“马户这个人是市里要调查的,这是市里的命令。这个马户非常卑鄙,各种炒作自己,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她背后还有女权行动派,之前被拘留过的,背景危险……” 还问过马户和主办机构是什么关系,甚至问出了“是不是马户建立的这个机构”这种明显胡人的问题。
对维稳的人来说这只是驾轻就熟的工作而已,对主办方和参与者来说却是巨大的危机。参与者们聚在一起想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大家基本上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办法判断形势,又怕又激动。马户之前也从来没有直接被找过,并没有什么经验。
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人只是凭着同样的兴趣聚集在一起,才认识不久。维稳的人利用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对政权的恐惧,再加上他们的惯用手法——以权威身份抹黑一部分人。当一滴水滴到油锅里,人们才知道油有多烫,这时候早已躲闪不及。最后参与者、主办方还有马户之前出现了一些摩擦,大家都觉得很受伤。
靶子
从那些夹杂着恐吓和暗示的话里,大家分析出了关停展览的三个大概的理由:
1. 他们认为抑郁症不正能量:“还收集东西?想要大家都抑郁吗?”
2. 马户是一个卑鄙而危险的女权行动派
3. 广州马上要开财富论坛了,这个期间什么活动都不准办。
我听到第3点的时候笑了:“可能这才是主要原因吧。”马户说:“是啊,感觉自己当了靶子。”
有人建议马户离开广州避一避,马户回家收拾好东西出门打了车。在出租车上她给朋友打电话说自己要走,朋友听了说:“没必要吧,哪有这么严重?”聊了一会儿马户又让司机掉头回了家。
朋友的分析是:这是针对活动的打击,不是针对马户个人的,马户只是一个参与者而已。有朋友建议要不要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公布出来。对这些回应马户不太满意:“女权伙伴们太理性了,大家没有体会我的处境,让我觉得自己不重要似的。”
“我的处境要求我考虑所有人,所以我不能做任何回应。但是他们说了这么多我们的坏话,还不能发声,叫我怎么忍啊……”马户很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马户的家人想给她一个惊喜,他们已经买好了机票,准备来广州看马户的展览,。这下子马户的压力更大了,不能让家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多情绪堆积在马户心里,没有爆发的出口,躁郁症本来也是一个很情绪化的疾病,加上她停药几个月了,马户说:“当时简直要了我的命啊……”
候补遗书
一个月之后这件事渐渐过去了,被影响的人也慢慢散了,马户还站在原地,她觉得整个事件的后劲上来了。
送走了家人,和小伙伴们渐渐疏远。马户住在城中村的小房子里,又开始不出门。她记不得洗脸、刷牙,记不得吃东西。马户觉得非常孤独,没有人理解她的处境,她的状况比三七事件的时候还糟糕。大脑总是放空的,时间过得非常慢,靠刷一些无聊的电视剧来打发时间,如果不看这些电视剧她无法不去自责:为什么和其它领域合作这么难?为什么自己所有关系都处理不好?本来好好的,怎么会搞成这样?
她当时刚好看到了几个关于自杀的新闻,死好像是一条出路。
马户一边觉得自己脑子很糊涂,另一边又觉得自己很清醒。她试了家里的水果刀和菜刀,都很钝,怎么割都割不破。她浑身脏兮兮的的去超市买回刀片,马户想:“这肯定可以了”。轻轻划了一下:“哦,好快啊。”
她担心自己死在这个房间里也没人知道,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让她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后的事情。马户开了一个公号,用来记录自己每天的挣扎:死,还是不死。如果哪天死了,这些就是她唯一留下的记录,所以叫做:“候补遗书”。
看到这些信息,朋友们紧张极了,给马户打电话。马户感受很强烈,但是没法思考朋友在说什么。她知道大家关心她,但又觉得这都不是安慰,反而像是要求。马户觉得自己没法满足大家让自己看起来好一些的愿望。她已经不能像头两年那样假装还行,因为自己真的很不好。
一个夜里马户有几个小时比较清醒,她受不了自己那么脏就去洗澡。沐浴液沾到之前用刀片划开的伤口非常疼。疼痛刺激了马户,她想:“我不能死,如果这样死了的话,那就是真的死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马户发现医院还可以线上咨询,医生说:“你必须来医院。”她脏脏的去了医院,医生看到她这个样子说:“好在你还能来。”
住院

照片由马户提供
医生强烈建议住院,住院就必须有家人陪床。马户不想通知家人,医生说:“那就只能吃药,但是你的身体受不了的。可能半年都缓不过来,我不确定你半年会发生什么。”马户只好告诉家人这个消息。
“怎么之前不说,一说就是这么大一件事”,家人受了很大刺激。妈妈阿娟很快就来了广州,她是个很坚强的人,但一看到马户胳膊上的口子整个人都垮了。阿娟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马户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照片由马户提供
住院之后马户感觉很好:吃饭也规律了,吃药也规律了,会有护士来盯着把药吃完;时不时还能和阿娟出去吃顿好的。马户觉得轻松多了,自己的生病的状态终于可以告诉大家了。
阿娟后来还是表现得很坚强,她把马户照顾得很好。住院条件特别差,家属没有地方睡觉,阿娟只能和马户挤在一米二的窄床上。
阿娟特别爱干净,觉得医院很脏,还没法洗澡。病房里有个病人晚上老是叫唤,阿娟正在更年期本来就失眠,几天下来人快不行了。马户说:“感觉应该住院的人是她”,她劝阿娟晚上回家休息。
阿娟不放心留马户一个人在医院过夜,有一天她特别不舍地说:“那我今天晚上自己回家吧,我洗个澡休息一下啊。”又叮嘱了很久晚上怎么吃,要注意些什么,一直到医院快关门了才走。
病友1

照片由马户提供
让马户感触最深的就是那几个同病房的病友了。有一个是不想高考的高中生,假装自己抑郁症要住院,没住两天就被医生赶了出去。
还有一个是高考之后就不正常的女孩,已经住了很久了,一直没法从备考状态里走出来。她每天晚上都要大声的背公式,背政治到深夜。如果不让她背书她就受不了,非常焦虑地说:“我不背书怎么办阿,我就不能考好成绩。”女孩的妈妈也是个大嗓门,夜里整个病房都是她们母女的声音。
女孩永远都在找东西,“我的书呢?我的木梳呢?我的手机呢?我的电脑呢?”有次她爸爸来陪了几天,他把女孩的电脑和手机藏了起来,以为把东西藏起来她就会安静了。女孩到处找,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焦急:“我的电脑!我的资料都在电脑里,辅导员发给我的期末考试的题都在里面!”她发疯似的不停的找。只能把她要的东西给她,她才会停下来,但是给了她,她就会开始特别大声的学习。

照片由马户提供
她老想往医院外面跑,跑了好几次,每次发病都会被绑在床上。有次她又要往外跑,说要出去买学习用品。女孩很强壮,她妈妈是个小个子,根本追不上她。她跑过马户身边时,马户下意识的拉住了女孩,女孩说:“我要出去买笔记本,我没有笔记本了。”马户说:“姐姐这里有,回去给你用。”
马户扯着她的手回了病房,她又被绑在了病床上。马户很内疚,因为骗了她。被绑的时候女孩说:“我要自由啊……你们这样绑着我我没有自由啊……”一直重着复关于自由的话。
隔壁床的女生小雨永远都没有力气说话,没法自理,她来月经就会流得床上哪里都是。一起住了很多天马户听到小雨最有力气的一句话就是半夜里无奈的说:“阿姨你们能不小点声啊,我睡不着……”
小雨的妈妈和阿娟平时聊天:“你闺女是做什么的?”阿娟说:“做公益的”小雨妈妈说:“我闺女也是做公益的”。但是估计她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是干嘛的。
小雨总是不吃东西,有一次她妈妈指着马户说:“你看看人家,吃得可香啦,顿顿都不落。你要像人家学习,人家也是做公益的。”
那个时候马户和小雨才知道两个人都是做公益的。小雨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等两人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小声的问马户:“你是做什么的呀?”马户说:”做女权行动的。你呢?”对方回答:“做同志运动的。”两个人小声的聊了许久,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彼此。小雨有了力气,从床上挪下来,爬到马户的耳边小声说:“你不要告诉我妈,我还没有跟她出柜。”马户也小声的说:“我也没有……”
妈妈的坚持 爸爸的委屈
住院结束后马户和阿娟一起回东北过年,这期间爸妈又要离婚。阿娟想离婚想了一辈子,夫妻俩吵架也吵了一辈子。
阿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小学都没有读完。婚后阿娟一个人要拉扯两个女儿,还要做家务。马户的爸爸老邓是个木匠,最早开小作坊给暖气片做木格子。阿娟负责在档口搞销售,她每天从镇里坐火车去上班,往返要两个多小时。车站离家也很远,冬天没法骑自行车只能走路过去,要走半个小时。她不舍得叫电动三轮车,只有带着两个女儿的时候才会坐,怕把孩子冻着。
因为生的都是女儿,生完孩子没人照顾。刚结婚那几年家里特别穷,婆家亲戚也不帮忙。老邓把农村的地和房全送给了自己的兄弟姊妹都没告诉阿娟一声,他觉得这是自己家的东西不用和阿娟商量。
后来生活好了一些,阿娟很舍得给婆家人花钱,她给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买这么好的东西。婆家一有什么事就想起让阿娟帮忙,但是她怎么做都不够,还是会被埋怨,被当作外人。马户的婶婶家因为生了儿子就不用给婆家花钱,说是要存钱给儿子买房。
老邓很委屈,他对马户说:“我和你一样啊,我也有好多想法。但是你妈不让,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阿娟管钱,她维持家里的生存线,只想家里人四口人一起好好过。
老邓几乎每年都被人骗钱,前年被传销了,买了一堆没用的药。虽然嘴硬不承认自己被骗了,但他后来也不吃那些药了。这一年又是想花一万元去学算命。“我爸觉得钱是自己赚的,有权决定怎么花,所以每年都要作一下,他想掌握家里的主导权”,马户说:“他性格特别固执,谁都没法说服他什么”。
阿娟和老邓去民政局办手续,到了拍照的时候,老邓都坐在那里了,阿娟又有点舍不得,最后也没有去。
阿娟老了,没文化,找工作也没有人要,要不然就是非常累的体力活,她的身体受不了。
出柜
和阿娟吵架的那天,老邓晚上出门沿着湖快速的走路,走了一圈又一圈。“他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发泄方式”马户说。
差不多十一点老邓才回来,马户想和爸爸单独聊聊,安慰一下他。聊着聊着他们谈起了马户为什么会生病,除了工作以外是不是还有感情问题。马户说:“有一部分吧。”老邓冷不丁的问:“你该不会是同性恋吧?”马户答:“那你接受吗?”老邓说:“不能……”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我也有点心理准备,你住院之前我找你姑姑算了一下,想知道是不是有砍儿过不去,你姑姑算出来说你是同性恋,我让她别告诉别人。”
第二天早上马户还没有起床,隐约听见客厅里老邓和阿娟还有姐姐在聊马户是同性恋这事。姐姐三年前就知道的。马户听见阿娟说了一句: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啊……之后就不停的哭,老邓和姐姐一直劝阿娟。听到马户起床了,老邓把阿娟带到房间里去哭,怕马户见了影响情绪。马户退了火车票,打算留在家里久一点。
阿娟那天决定去夜总会当保洁员,那是24小时一班要熬夜的工作,实在太幸苦了,之前阿娟不愿意去的。过了差不多30个小时,阿娟回家了,她对马户说:“你爸和你姐跟我说了你的事儿,我呢比较保守,也不了解这个东西……不过你开心就好。”紧接着又说:“你也要考虑一下这个事儿,这样不行……”之后的10天阿娟再也没有当着马户的面哭过。
马户的爸妈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往往说两句话就会吵起来,姐妹俩开始教父母怎么沟通。比如外出的时候,老邓说:“你穿这么少不冷啊?”马户会告诉老邓可以改成:“外面冷,多穿点,我担心你。”
回家
家人希望马户回家,他们觉得马户的工作太让人紧张了。马户还在策划着和异地恋女友阿芒未来在广州的生活。一次次的商量安排各种细节,最后阿芒还是和前女友复合了,不来广州了。
马户得知这个消息时在朋友家,她躲到厨房里默默流眼泪。从小阿娟都不准她哭,所以她即使哭也很少发出声音,这次马户逼自己哭出声来。朋友来安慰她,她还是不愿被看到,捂着脸哭了很久手都泡白了。哭完之后马户觉得轻松多了,她没有了牵挂终于可以回家了,马户彻底辞职了。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马户觉得非常轻松,有一天晚上她和同事还有一些朋友聚会,她问:“我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你们了解我吗?”辞职以后马户觉得自己能量多了起来,开始和伙伴们多交流。朋友问她是不是真心想回家,马户说:“是的”。
马户开始憧憬回家,没有了以前那种想要离家的叛逆,也不是逃避,是真的需要回家。“家人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家人,我要回家面对他们”马户说。
回家以后至少每天可以按时吃饭,而且东北很饥渴,非常缺乏和性别相关的活动,马户开始构思要做些什么事情,期待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在广州染头发的马户
结尾
三七事件过去很久之后,我听吕频说起做社会运动的年轻人有很强的脆弱性。我们本来就是一些有边缘特质的人,所以才更希望找到可以解答疑惑的思想,更渴望改善社会。又因为没有很多既得利益的包袱,更有行动力。这些特点同时也导致我们格外脆弱,缺乏社会资源。参与社会运动加剧了我们和原生家庭以及原有社会关系的分裂。如果运动受到重创,我们承受打击的弹性是很小的。
我时常自责,怪自己天真、无能,怀着一种善意想要帮别人、也想帮自己,但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怎样一头巨兽。
每个人都能看见很多文章被删掉,很多事实被隐藏,像割韭菜一样。女权之声被删号,接着多个营销号给我们扣上跨国卖淫和分裂祖国的帽子。还比如一些搞笑账号、八卦账号都被删了,理由很多,但不知道背后真实的原因。可能这个没有统一人格的庞大机器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越来越可以为所欲为了,巨兽已经长成。
有人留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骚扰别人,光是来骚扰你?你有什么问题?”我也明白:当人生活在一个无力反抗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很容易产生相信强者的渴望,不然怎么面对自己的处境呢?接受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事实,需要勇气。
时不时的有人劝我:“你们不要那么激进,不要刺激它,我们才可以好好做事。”但如果不是站在前面的人的守护,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激进者了。不过你也看到了,我们很没用的(笑)。过不了多久这就将是更多人要共同面临的挑战了。
在更多的痛苦来临之前,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在黑夜里行走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从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穿破黑暗成长的力量。
我问吕频:“在越来越糟的环境里该怎么办呢?”吕频说:“活下去。活得比它更久,才能等到希望。”是的,我们要精神和肉体都健康的活下去,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我们可以成长。我想用文字写出我们的血肉,希望这样做还可以在这个充满戾气的网络世界里,留出一个拥抱那么大的空间,建立不那么容易被挑拨的信任。
这也是我写下这些故事的原因。
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