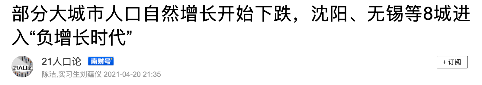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一再推迟公布时间,导致国内外各方多番猜测。英国金融时报在4月28日报道中预测,中国将迎来5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第二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则通告表示: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尽管国家统计局努力以这么一则通告安慰早已焦虑不堪的舆论,但多个城市发布的2020年统计公报似乎都在印证人口自然增长率下跌的预判。
2015年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前,就已经有学者使用“大国空巢”的意象来表达对未来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严重和劳动力不足危机的忧虑。每年我们都能听到来自专家学者、两会代表和委员为了解决低出生率而提出的奇葩方案:把男女的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开放三胎政策;父母生三孩,孩子高考加50分……这些方案几乎都被骂上热搜。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大国空巢”。我的着眼点更多放在生育率下降的今天,国家与妇女权利之间的张力。
关于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一般可见主流的观点是:女性受教育权和就业权越有保障,女性就越不愿意生育——经过推骨牌一样的滑坡论证,妇女权利越进步,中国人口越来越少,国力越下降,亡国都有可能。
那么,要提升生育率,是不是意味着女人不能受教育、不要找工作?女权进步和提升生育率真是完全矛盾的吗?
01
不婚不育:妇女的无奈和反抗
先有压迫才有反抗
“女权越进步,生育率越低”这种说法是一种过于头脑简单的判断。尽管妇女权利进步的确有利于女性从经济上、思想上摆脱对父权家庭的人身依附,但这并非女性不生孩子的最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时,掌握了一定政治决策权的女权主义领导者致力从法律、政策保护层面固定妇女的离婚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等。建国后,妇女权利总体上比建国前那段动荡时期更有保障。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中国人口净增1.05亿,被称为建国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根据对北欧四国近年生育率稳步恢复的研究,国家调控提高生育率的奥秘,就是在倡导妇女受教育、就业、公共参与权利的同时,提供公共托儿、育儿福利、妊娠补助等配套措施,减少大家生养孩子的压力。而2012年台湾学者对“外配”生育情况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家庭内的权利不平等和社会歧视都导致“外配”的生育意愿较低,总生育率低于台湾本地妇女。这种情况在日本、韩国也有实证研究印证。
以上例子都足以证明,“女权进步导致生育率低下”,只是先生们放弃思考、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为怪罪女人变得自由和独立,比倡议国家做好服务工作要容易得多。
实际上,人类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理性的、社会化的分析。在确定环境适宜的情况下,考虑经济条件、政策福利、精神健康和投入产出比等相关的因素后再生育,是比较正常的人类续存状态。但在厌女文化中长大的“未来丈夫”们,不能接受女性解放后将会夺走他们既得利益的可能性。他们只能把女性具有选择权这件事无限妖魔化,把对于高生育率的想象极端化成“女人像猪一样不停生”,才能减缓他们对于香火不继的焦虑。
在所谓性别对立的视角下,女性要么驯服要么夺权。两性之间有商有量、偶有妥协的光谱被简化成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时,提出不结婚、不生育的女性,俨然成为了向男权结构发出挑衅的反叛者。
这一时代的年轻女性大多出生于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严厉执行的时代,很多是独生女,得以较为充分地享有家庭资源,以投入在她们的教育和就业上。2011年后,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从学校图书馆涌出到大众媒体上,“醒来的女性们”渴望在各个领域实现自我,却同时意识到她们在生活各方面都未能达到与男子一般平等的事实。她们对自身身为女性的生存境况感到担忧,寄望于社会能有所进步。
但是,国家一方面在满头大汗地忙着用春晚小品、国产电视剧电影来渲染“生个孩子你全家老人都会很幸福”的概念,另一方面却难以在教育平权、离婚自由、反性侵/性骚扰等年轻女性最关注的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反而明里暗里通过对封杀女权主义活动和发声平台的方式来试图对女人进行思想控制。在无能力改变国家政策的情况下,不婚不育是自觉处于不公的女性最明显又最终极的防卫武器——既然婚姻和生育意味着权利进一步受损,那倒不如冒天下之大不韪保持单身。
尽管不婚不育尚未成为或者很难成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但它反映出年轻女性对国家性别盲视和歧视政策的愤怒。大家不停追问:女性还要承受怎样的对待?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敢生吗?
02
回避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公
生再多也枉然
有学者在研究韩国生育率低下问题时指出,“工作至上主义”打败了韩国鼓励生育的税收激励和儿童保育政策,让劳动者自觉更不适合养育子女,致使生育率下降。
“工作至上主义”由Derek Thompson在2019年提出,指的是“只有在职场中努力工作才是唯一实现人生意义的方法”成为了一种像宗教一样被狂热信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无论在欧美还是东亚国家都一样很有市场。
爱岗敬业、最美劳动者等美称都在号召人们热情努力地工作;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则仅仅是维持工作至上主义的必要资源;公共辩论和公共参与在很多国家更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那会成为国家维稳的障碍。在这种信条下,打工人们在996以外已经没有欲望为自己的生活找其他盼头。
可以想像,在当下,家务劳动共担、拒绝丧偶式育儿等性别平等观念越来越多被女性劳动者接受,但女性劳动者和她的丈夫却同时像韭菜一样被割而看不到什么出路,更不要说要花精力去构建平等的婚内关系了。理想中的温馨小生活被打碎成挤地铁、吃盒饭、加班、挤地铁、熬夜,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节奏,如何让这些年轻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生育后让生活变得更好?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生育率提高国力才能提高”“生个孩子未来才有保障”的说法,也许都有很多疑惑。
这些疑惑可能是“用工荒”和“找工难”两种互相矛盾的新闻居然长期地出现在新闻推送中,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生够了足量的劳动力,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富裕;也可能是多省社会保险基金出现缺口,就2018年数据看,广东的养老保险可持续52.2个月,而黑龙江却已经亏空476亿元;可能是“养儿防老”已经被看穿仅仅是老人,特别是女性老人在退休后依然需要付出无酬劳动照顾孙辈,否则就会变成儿女互相推搪赡养责任的烫手山芋;也可能是我们看到高级小区里有钱人一掷千金做能够筛选胎儿性别的人工受孕,但身边的打工人总是抱怨太贵不敢生。
分配方式的不公让人对未来生活有一种危机感,普通人总觉得赚得不够,无法承担养育孩子带来的经济风险。而再分配的不足则让人只能着眼于年轻的时候要赚得更多,防止老来无所依的焦虑死循环。
“生出来干什么,只会让ta像我们一样痛苦而已。”
03
女权主义视角的治理
让想生的人敢生
女权主义关注妇女权利,并且关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平等与公正。她是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清醒而有能量的关键。我将会用三个假设证明,只有女权主义视角的治理,才能解决上述低生育率带来的困境、对两性对立的焦虑和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危机感问题。
第一个假设是,更多女性女权主义者能够进入政治决策层,与男性在公共事务中平等地分享决策权,将会使生育率得到提高。
如果没有人提出生育中的疼痛问题、生育后的精神和身体康复问题,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人知道女性生育将会面临那么多风险和不便:漏尿、侧切的痛楚、无尊严的生产体验、抑郁、产后回归职场困难……如果我们有足量的女性领导者,她们不会像男性一样无视这些切身的问题,将会考虑更多保障母亲权利的政策。从北欧四国女性参政比例高企和近年来生育率回升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可能性。
第二个假设是,更多女权主义者能够不受审查地在各种领域开展性别平等倡导工作,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更多科学的、关于生育的结论。
例如“最佳育龄”的说法过度渲染了高龄生育的风险,徒增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的焦虑,还加深了对女性的年龄歧视。在英国的一些地区,首次生育的产妇平均年龄是30.3岁。女权主义的视角可以让生育医学和科技从业者把注意力从拼了命要求女性刚毕业就生孩子,转移到更好地改进本来就应该花力气改进的、对产妇的医疗服务上。
第三个假设是,多元的性别平等理念能够打开我们关于生育的想象力。
在法国,同性婚姻合法,同居关系有政策保障,非婚生育率(包括单身女性非婚生育)占总出生率仅60%,其总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替代水平。反观我们社会,在同性恋者依然被歧视、单身女性难以冻卵和给孩子上户口、未婚先孕依然是一个贬义词的当下,如果把生育率的提升仅仅寄望在传统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上,那么这个愿望恐怕无法实现。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剧《使女的故事》第四季回归了。它讲述的故事是在环境污染极度严重的世界里,基列国有生育能力的女人被枪杆子逼着为特权阶层“自然代孕”。它曾一度引起国内外女性的恐慌,大家都担心那可能就是自己未来的生存图景。
我曾经对这个故事的基本逻辑感到特别困惑:既然生育率低,那就应该大力发展生育科技帮助国民生育,而不是变态地杀掉同性恋、女医生,让生育率提升的可能性变得更低啊。
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这个故事中特权阶层们哪里是真的想要提升生育率拯救人类,他们仅仅是想在世界末日之前仅存的那几十年里狠狠捞一把好处,享受自己处于权势地位的美好人生罢了。
每一个为生育率下降而焦虑的国家,都应该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你不是基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