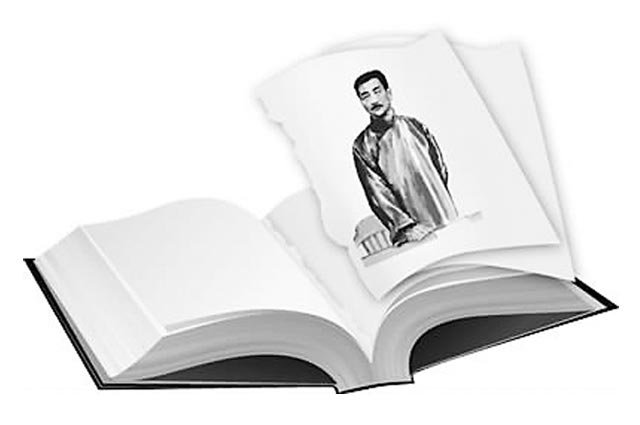近几年的秋天,随着新学年的开始,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进进出出,就像旧伤口发炎肒脓一样,总是引起传媒和网友们的吵闹。其实这些争论,总体来说价值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总是争论鲁迅的作品该不该删除和该不该保留这样的伪命题,而不去思考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主宰并导致了这样的原因?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就会在每年秋天,鲁迅的作品“一有风吹草动”,就重复言说,毫无新意,还显得没有一点含金量的振振有辞。
(资料图:鲁迅作品是否从教科书中撤下,一直是舆论争议不休的话题。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争论的前提,就是教材编写不能搞大一统,不能搞垄断。如果百舸争流,教材编写完全由民间自行编写与出版,学校和教师自行选择,乃至他们自行编写,那么鲁迅作品的增加和减少,都会变成一个伪命题。
长期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热衷于选林觉民的《与妻书》——两党曾经极不相能,你死我活,却在许多时刻都选这篇文章,那是为什么呢?请参看拙文《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这里面蕴藏着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但在1998年台湾教材编写民营化后,以我所见,台湾民营教材和台湾“教育部”部编教材也没再选《与妻书》,这里面可以阐释的信息非常之多。但为什么没见台湾教育界、新闻界于此闹哄哄地争来争去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教育哲学的改变和教材编写的自由竞争。
教育哲学的改变,我们选按下不表。教材编写一旦自由竞争,谁的作品真能带来美的享受、知识的增益、思想的深度、心理上的帮助与成长,便不只能由教材编写者说了算。一九四九年后大陆的教材编写者,只不过是庞大利益分肥者的一员,像我这样对教材比较有研究的人,都不知这些编写者有何等事功——是否教育有能,写作有得,心理有感的人在编写——更何况万千与教育有关却对教材不甚了解的学生与家长呢?
如果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讲解,由一线教师做决定,加上家长委员会这样自助性组织的权衡,我想在教材编写、出版、发行、使用上的制衡上一定是会起点作用的。
但或许有人会讲,如果教材百花齐放,深度竞争,那是不是对高考不利呢?那当然相应地要改变全国统一高考的模式——改为各高校自行招考,使得高校竞争成为可能,民营资本真正有可进入之期。
有人会说这样太腐败,难道现在的高度垄断没有腐败?请参见我两篇几年前乃至十年前论《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的文章——我并不主张取消高考,而是主张取消全国统一的高考,使高考的资源配置达到一定的优化。同时舒解学生一考定终身的巨大焦虑,一年可多考几次,单是使学生自杀率有所降低便是功德无量的事,何况还有教育上的其它增益?再者,客观题僵死一般的具有统一答案的题,所占的比例应该大幅削减,使得教材的充分竞争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由民国时期的教育成就得以证明。
鲁迅的名声被传播得很广远,如果我们做点像样子的实证研究的话,其实他名声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他真正值得重视的小说《呐喊》《徬徨》,散文集《野草》,更不来自其学术作品《中国小说史略》,而是来自他后期的杂文。
名声如何得来,这是作者自己控制不住的,因为作品的传播,有社会之需,更有手握“议程设置”——传播学名家拉斯韦尔、施拉姆等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对了解信息控制与传播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重权的掌控者如毛泽东的深度参与有关。这正如钱钟书的调侃:“所谓名声不过就是误会的总和。”
鲁迅的杂文都是随感性质的东西,并没有太深的讲究。尤其是他并没有较好的政治学常识,在公共议论中缺少清明理性,特别是争胜好斗的习性,使得他骂功大放异彩。其间的仇恨教育和怨毒之辞,很容易把把情感与智商正处于发育期的学生,培养成了一个大多丧失理智,不能正常讨论公共问题的谩骂者。
这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许多人没有见识,大陆曾引进台湾学者陈奎憙、张建成审订,谭光鼐、王丽云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版),将世界级的教育社会学家几乎说了个遍,但几乎很少涉及教材在教育社会学里应有的份量。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所处之时代,教材对学校对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引致足够的重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工业化引起的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还远没有到今天这般疯狂。
越到后来,教育越追求规模化效应,讲究一种投入与产出的速成,成为国家至上教育观,以及商业与人力资本全球化对人才需求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民主国家教材编写充分竞争,有时根本就没有教材,但他们的老师能做到在价值观与情感、知识上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干扰。但对于封闭社会的教育,教材所造成的诸多社会影响之大,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但问题是,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作为影响学校和社会最重要的媒介,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学家的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引致传播学者的深透观察。一篇课文被重复选用,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信息,选它的目的何在?学生能有兴趣地接受否?讲解者有何种能发挥的余地?如果按规定死了的“教学参考”来做,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如果我们能对从民国以降,鲁迅的作品入选教材的情形,做个数字统计的梳理,对其诗、小说、散文、杂文等进行一个入选的分类,那么就不难得出我们的教育在注重鲁迅的什么,从而分析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和时代风尚,甚至教育哲学目的。如果说民主国家的教材问题,还不是个巨大的教育社会学应该研究的问题的话,那么像我们国家的教材编写、出版、发行、讲授,应该成为教育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
研究迅翁的人可谓夥矣,既有“伟大领袖”号召在前,更有众多只能算是“就业大军”的研究者岂甘落人之后?迅翁值不值得研究呢?当然值得深加研究。但如何研究,却是那些只靠他吃饭的所谓研究者,不曾想过或者万万想不清楚的。他们只有辗转稗贩,连鲁迅的知识谱系怎么来的,他们都不甚了然。只有像金纲兄这样的人来下苦功夫,编著一本厚厚的《鲁迅读过的书》,做这样吃力不讨彩的基础研究。
同理,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对国人的社会认知、知识的构筑、历史的体会、现实的应对、情绪的形成有何等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尽量做定性定量之研究。而不是流于泛泛谈论,产生一堆无用之口水,每年秋天来发炎肒脓,而毫无精进。如果有人写一本《教材的传播威力:以鲁迅为例》,从教育传播学和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讲,那一定是件功德无量的美事,做得好甚至是本传世之作。可惜的是,只知重复蹈袭的迅翁研究者,哪里能产生这样新的研究视角和功力?
有人说最近几年在教材里连续取消鲁迅的作品,是有关部门想淡化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怕许多人读了鲁迅的东西,对当下有极其丰富而敏锐的联想,使得他们不安,我不认为有关部门完全没有这样的企图。但是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鲁迅不少作品,不适合在初高中来读,也不必为此讳饰遮掩。不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就不会成为一种流布甚广的校园段子了。
当初我读书的时候,选的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可以说除了《从百草原到三味书屋外》,没有一篇我喜欢的。这说明教材编写者,根本就不从教育心理学上去思考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灌输,不管你是否喜欢。他们在选入鲁迅作品的同时把鲁迅也给异化了。
事实上,在公共话语中有着清明理性,具有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的人,鲁迅远不是最好的批评者。我不是说鲁迅的完全不选,至少应该给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徐志摩、王小波、林达、刘瑜等人,以较多的机会,让学生们知道批判社会现实还有这样的维度,文字不必剑拔弩张,但却深具穿透力,甚至有趣而优雅。
鲁迅的一些作品如《纪念刘和珍君》于当下依然有现实针对性,但你要是不能讲透“三·一八”惨案的背景,你不能诚实地告知其间有多种势力形成的此局,以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那么你如何讲《纪念刘和珍君》?
不客气地说,如今的中学老师里,很大一部分人单一而混乱的历史知识,不配来讲这样的课。我认为要讲这样的课程,不仅要有诚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还要有相当的政治学常识,而不是仅是停留于“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的空洞抒情。愤怒和仇恨都是人之情绪的一种,但对心智和情感都尚未成熟的学生,恐怕在这方面,我们成人要有相当多的考量,不可偏执而不顾他们的良性成长。我们应该对鲁迅文章入选做比较精确的数据统计,看哪些重复入选的概率较高,而为何忽略鲁迅另外的文章,来做重复率研究,以明了官方为何选此鲁迅而不选彼鲁迅的原因。
很多人说不理解鲁迅作品何以被剔除教材,好像他能洞悉鲁迅作品入选教材的教育目的似的。如果我说斗争哲学、阶级意识、仇恨教育、丑化民国才是有关部门在几十年里频繁选鲁迅的目的,希望你不要感到吃惊。但有人或许会说,他们害怕嘛,我们就一定要选噻,这样的教育的目的恐怕害人终害己。因为不要忘记仇恨的反噬作用,往往是民众间的互相仇恨,更符合古老的牧民术和统治运营成本及风险的降低。斗争及仇恨导致互信降低,使得人的原子化加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会让我们深思,但他并没有谈及中国的现实何以如此。
鲁迅的作品依然是现在教材里,所占比例最多的,这说明人们的认知有相当多的惯性,同时也表明现实的丑陋,不能达成鲁迅希望其一些文章速朽的愿望。如果我们不清楚为何如此,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港台两地所选鲁迅篇什,就能大致明了大陆教育何以如此了。选文中保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这样的篇什是必要的,我甚至认为高中可选《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章节来让人们认识一个别样的鲁迅,使其更加丰富而立体。
教材对一个写作者的名声既有传播乃至神化功能,但也有极大的异化作用,因为很多人所受的教育,也就到高中为止。教材对人之“三观”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有人只知杜甫的“三吏三别”《茅于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便形成对杜甫、白居易如此扁平而单一的终身认知,要想改变其认知绝非易事。那么对鲁迅的神化和利用,何尝没有异化他的成份呢?
2013年9月5日至6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