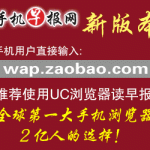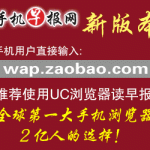郑永年:当代中国社会暴力的制度基础
(2011-08-02)
| 早报导读 |
● 郑永年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案件快速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凸现。在种种暴力行为中,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当然,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不过,即使是后者,很大的责任也应当归咎于政府。很简单,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缺失,只能说明政府的失责。
当然,暴力也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减少社会暴力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暴力的根源非常多。中国社会的暴力行为也体现为中国特色。任何社会都不期望暴力行为的兴起。暴力产生了,就要分析暴力行为的根源,才能采取有效的举措来减少和控制。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公共秩序,控制暴力行为,但中国的公权力往往成为社会暴力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公权力的暴力化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暴力行为的崛起。(在中国,暴力也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这需要专文论述。)
中国社会暴力的大制度背景,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在发达社会,往往是社会决定国家,人民决定政府;而在中国则相反,社会和人民的存在空间基本上取决于国家和政府。换句话说,在发达社会,尤其是先发展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在中国,国家和政府决定了社会和人民是否能够得到权力,能够得到多大的权力。
在后发展中社会,典型的是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等,政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发展过程中,较之发达社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也决定了社会的生存空间。不过,随着社会本身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均衡,呈现出一个良性的互动方式。在学术界,人们经常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也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试图改变改革前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的严重失衡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得到迅速的成长和发展。在1980年代,国家公权力首先从农村逐渐减少,在农村实践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为城市市民社会造就了巨大的空间。1990年代中期之后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更是为社会空间的成长打下了制度基础。
公权力扩大激化民间政治意识
应当指出的是,在政治领域,尤其在基层,尽管社会也具有了一些空间,但并没有得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空间。社会的成长和发展发生在除了政治以外的其它领域。邓小平南巡之后,正是因为社会在其它多个领域获得了很大的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得到缓解,因为人们把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方面。
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和从前一样,在政治领域,社会照样没有实质性的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在非政治领域,社会空间也在迅速缩小。例如,在经济领域,国有部门的快速扩张,迅速挤占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在政治领域,随着维稳机制的推行,社会其它方面的空间也缩小。这就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结果。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空间分布的严重失衡,公权力迅速扩展,而社会空间缩小。其次,社会空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社会不能正常发育,不能产生自我管理机制,自我约束能力弱。社会自治能力的弱化,表明社会无法自我解决很多问题,必须依靠公权力,从而为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机会。再次,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它领域,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其代理人,都是以政治的方式来挤占社会空间的,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性反弹。社会群体和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挤压,它们也必然诉诸于政治的手段来面对其所面临的困难处境。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只是其中一种政治表达方式。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暴力行为的大背景。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年的政治和政策大环境的变化——对“法制”和“法治”的忽视和漠视。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最为基础的制度,是其它所有基本国家制度的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国家暴力和暴力使用必须法制化。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不仅没有多大的进步,而且在很多层面发生倒退现象。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