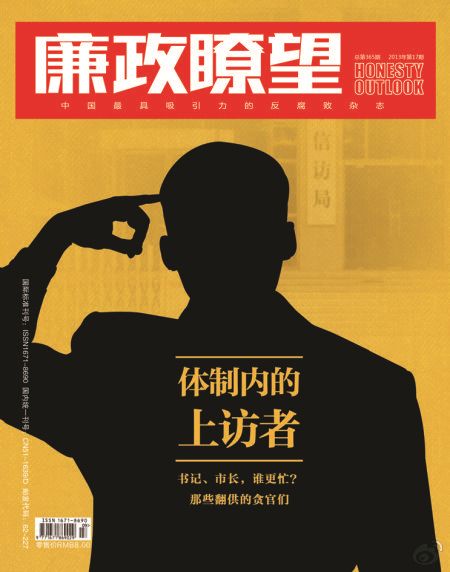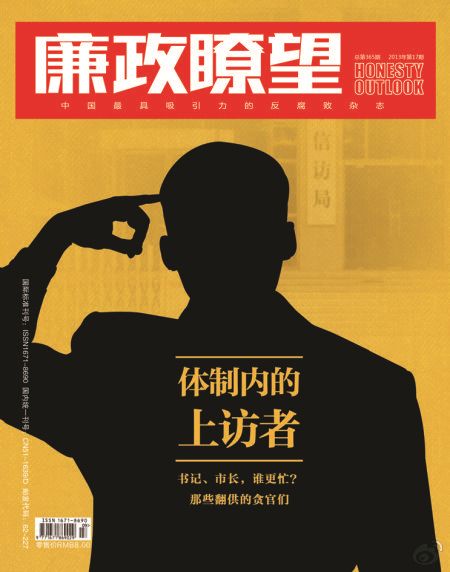是悲剧?是尴尬?是影响政府形象?是体制内的“叛徒”?还是供人嘲讽甚至快意的“笑话”?
都不是!体制内的上访者只是一个简单的上访者,不应该被贴上这个或者那个标签。每个人都有上访的权利。重要的是,如何在公正的法治环境中解决问题、平息纷争,这无论对政府,还是上访者而言,都十分重要。
“我的事情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戴新华并不想通过舆论来施压,他希望得到的是社会认可,尽管部分“朋友”视之为软弱。
监察局长的上访路
一个小时内,戴新华遇到了两拨以前的同事。
第一拨他主动招呼后,双方寒暄了4句话,握在一起的手还没有感受到彼此温度,旋即分开;第二拨更简单,双方点头示意,口中都咕隆了几句话,声音低不可闻。
戴新华介绍称,其中一人是宁夏平罗某县直部门副局长,“和他们见面,我有很大的压力。”此前,他曾先后担任平罗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长。体制内外,落差巨大。
2012年2月2日,因为一次出庭作证,宁夏石嘴山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戴新华犯伪证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一年。随即他被“双开”。
对判决结果不服但又申述无果后,他走上信访之路。
“只有上访,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戴新华称。
“我是出于实事求是出庭的”
一切缘起于一次闲聊。
2007年8月底的一天,时任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戴新华正准备下班,平罗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张怀兵找上门来。
聊天过程中,张怀兵说,曾于2007年春节期间收受村干部礼金约4万元,并拿出了一张纸,上面记录着相关礼金的花销情况。
据戴新华称,“他让我不要说,称会退钱,我就没有按照程序上报组织。”张怀兵将纸条留下就走了。
事情就此开始。
几个月后,张怀兵因受贿被判缓刑,而行贿者被判实刑。
行贿者家属就此不断上访。迫于压力,2009年9月,石嘴山中院再审张怀兵受贿案。
开庭前,张怀兵找到戴新华,希望他能出庭作证。
戴新华同意并出庭证实张怀兵曾在2007年8月向他反映,曾收受他人4万元的事情。
“他确实找过我,我是出于实事求是出庭的。”戴新华否认了张怀兵给他钱的说法。但不久他就感到不妥,此后拒绝再出庭。
最终法院对张怀兵维持了原判。几个月后,戴新华被石嘴山市大武口检察院以涉嫌伪证罪带走。
2011年4月,大武口法院一审判决戴新华无罪。
此后,大武口检察院3次抗诉,大武口法院、石嘴山中院分别4次开庭。2次被判无罪后,2012年2月石嘴山中院最终判决戴新华伪证罪成立,拘役6个月缓刑一年(详见本刊2012年第15期)。
“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戴新华不服,向石嘴山中院提出申诉,却被驳回。于是,戴新华将申诉状递到宁夏高院立案庭。同时,他开始向宁夏自治区各部门写信反映情况,走上信访之路。
与普通的上访者不同,戴新华更希望通过正规的上访渠道解决问题。
2012年全国、宁夏“两会”期间,戴新华先后到银川、北京上访。路上,他看见“两会”代表的车辆从身边经过时,“一刹那间我有向车扑过去的念头”。
最终戴新华并没有动。“我眼睛不好使。当我看清楚之后,车已经过去了。”他解释称, “后来我想,还是走正规渠道,找党委政府信访部门吧。”
一年多来,戴新华唯一做得比较“出格”的事是,将自己的情况发布在网络上。
有媒体报道此事后,拿来200多份报纸,让戴新华买去发,“扩大影响”。最终他只拿了30多份。
“我的事情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戴新华并不想通过舆论来施压,尽管他部分朋友视之为软弱。
戴新华也尽量避免在上访中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
由于戴新华坚称无罪,缓刑期间拒绝到当地街道办司法所报到,石嘴山中院的相关程序一直无法走完。
今年年初,他到宁夏高院拿申述通知书时,石嘴山中院相关人员突然出现。言语与肢体冲突中,戴新华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地不起。
在医院简单治疗后,戴新华当晚就匆匆赶回平罗,并未节外生枝。“我要的是重新开庭,还我清白。”他的目标很简单。
戴新华认为,曾经的官员身份,除了让接访人员感到“同情、震惊”,陡升“搞纪检的监察局长怎么会受冤”的疑问外,没有任何帮助。
其实不然。公职身份更容易引起关注。戴新华上访不久,宁夏自治区纪委、检察院等均先后专门派人调查过此事。
宁夏自治区检察院还曾向戴新华出具了正式的答复函,称此案中检察机关确实有瑕疵,但并不影响判决结果。
因为离他重新开庭的要求相去甚远,“我没有去拿答复函”,戴新华显得有点固执。
心境变化
“他上访的事我们都知道,自治区领导也知道”,平罗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我们不干预,也不反对”,“他要上访就上访吧,这事是经过司法程序的”。
戴新华很明白平罗县的态度。现在,他最主要的精力是给中央、有关部委、宁夏自治区主要领导写信、寄材料,“每周一次”。
一年多的上访,显然改变了他的心境。
回家后,戴新华越来越沉默,不愿意提及上访的事,也很少表露他的真实想法。
曾经作为监察局长,戴新华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受理控告与申述。“我也知道信访作用不大,有些上访材料不会转到领导那儿去”,但又不得不走这条路。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体制外的上访者不同,戴新华内心承受的压力与煎熬更大。
“如果能碰上一个正直的人,能把我的材料转达给领导,就好了。”采访中,戴新华数次如此说到。
有两次偶遇宁夏高院李彦凯院长,戴新华抓住机会快步过去介绍自己的情况。
虽然李彦凯均因有会必须参加,让秘书处理,收下材料。“我当时也就没有继续纠缠,因为我听说他是个清官。”戴新华称。
采访中,戴新华一再提及宁夏数个上访翻过来冤案,那是几个比较极端的上访案例。
记者提醒他,案件中他也存在瑕疵,是否考虑过放弃上访,重新走申诉之路。
戴新华称,“上访压力非常大,内心非常痛苦。我不愿意上访,但是实在没有办法。”虽然路遇熟人还会听到那声熟悉的“戴局长”,可对方逃避的眼神,令戴新华痛苦不已。
此前同事认为的那个谨言慎行、中规中矩的戴新华正在蜕变。他说“上访太难”已不足以概括自己这一年多的感受了,“我们的制度需要进行反思”。这样的话题,是他此前不会谈及的。
“上访对我的性格、信仰,包括奋斗都改变了。”戴新华自言。
虽然上访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但上访越来越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郭学宏:从法院副院长到上访祥林嫂
7月初的一天下午,郭学宏踮起脚,颇为费劲地昂起头,打量着自己家楼道里的一个新安的监控摄像头,“还没到国庆啊,这玩意儿怎么又装回来了”?百思不得其解后,他把这个“料”抛给了几家媒体,在网上再度引爆“上访法官被监控”的话题。
8月7日,47岁的郭学宏在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会心一笑:“原来不是监控我的,是监控这幢楼里一家新开公司的,但很难说国庆前会不会再专门给我装一个。不好意思,家人都说我是惊弓之鸟了,老是疑神疑鬼的。”
新院长的“一根筋”
撤职之前,郭学宏是伊通县管民事的副院长。伊通是吉林省唯一的满族自治县,虽然离长春很近,但长期是省级贫困县。当地多名官员向记者证实,像郭学宏这样解除职务和级别,仅保留公务员待遇的,一个月全部加上有2000元左右。
“老郭算不错了,还保留了公职,要是直接开除,就啥都没了。”这是伊通了解郭的官场中人普遍看法,“一根筋、不听领导招呼”是钉在郭学宏身上的标签。
“有人说他当上副院长,是因为无党派的身份来配班子。”郭的一名同事则向《廉政瞭望》记者透露,“但我不这么看,老郭在法院系统干了20多年,当了4年多副院长,业务上是过硬的。”
就这样,在伊通官场上被视为“很倔”的郭学宏从未想到,2009年接手的一起普通经济纠纷案会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2007年10月26日,长春商人马东昌与浙江商人邱冬华签订了一份采石场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马将自己的伊通县财源采石场承包给邱两年,每年承包费220万元,按月支付。由于邱冬华未按协议支付承包费,双方发生纠纷。2009年1月6日,马东昌将邱冬华诉至伊通县法院。当日,该院管辖的马鞍法庭受理了此案,庭长张志信负责审理,而分管此案的正是郭学宏。
因担心邱转移采石场的固定资产,马东昌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伊通县法院6天后裁定,将财源采石场的生产车辆和设备、1.2立方米石料查封。“为了不让他(邱冬华)有经济损失,我们明确告诉他,查封的设备可以继续使用,但不能迁走。”郭学宏说。
3月2日,伊通县法院判定马东昌胜诉,并要求邱冬华在“本判决生效后10天内给付承包费152万余元”。
此后,邱冬华以实物担保等方式要求解封。但都因为资格问题,被法院拒绝。其间,伊通县法院已退休的院长戚长玉多次找郭学宏和张志信,要求在解封财产一事上“行个方便”。
“老领导说情,我很为难。不过最后还是跟他说,自己刚上来,还是让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吧。”郭学宏说。后来,伊通县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不同意解除查封,待被告(邱冬华)提供现金或有效实物时再议。
“软办”的硬实力
然而,让郭学宏没有想到的是,当年5月13日,此案在吉林省软环境视频会上被通报批评了,而吉林省整治和建设经济发展软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软办”)属省纪委下属部门。
随即,伊通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郭学宏回忆,会议正式开始前,时任县长徐远征曾向郭学宏询问过此事:“你的通报批评到底是怎么回事?”郭学宏当时拍着胸脯,朝这名很了解自己的领导保证,绝没有原则问题。
5月23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给郭学宏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一年后,这颗定心丸药效过期。
2010年6月3日,四平市纪委召开涉软案件新闻发布会,邱冬华案被作为典型涉软案件再次被通报,伊通法院被严厉批评。
据知情人士介绍,“软办”介入调查一个月后,曾给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过通知,要求他们对邱冬华案有关问题做出说明。当时四平中院的一名副院长带着郭学宏和张志信一起去“软办”主任李明国的办公室,向其做了详细汇报。
“领导觉得我们没有保护好软环境,破坏了招商引资。”郭学宏说。
记者采访得知,吉林省软办的结论是,伊通县法院在审理邱冬华案中,不正确履行职责,违法超标的查封,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而该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不予办理,致使财产被查封长达17个月,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直接负责该案的法官张志信认为,当时裁定书中说了邱可以继续使用那些设备,很难界定有多重大的损失。郭学宏则表示,当时李明国要求伊通法院无条件解除之前的查封,并允许邱冬华将保全的财产拉走。但按照法律规定,案件的对错与否,应该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研究确定。
郭学宏清楚地记得,遭到拒绝后,李明国非常生气,还拍了桌子。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明国三天两头就打电话让郭学宏去他在长春的办公室解释问题。
多次交涉无果后,四平市纪委决定,伊通县法院院长姜守臣因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建议免职,分管副院长郭学宏因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马鞍法庭庭长张志信因负有直接责任,被建议撤职。
时任四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姜焕昌则强硬表态:“今后,凡是涉软案件,无论涉及到谁,必须一查到底,绝不手软,并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至此,郭学宏才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邱东华找了浙江商会帮忙,并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而这属于“软办”的“业务范畴”。
2010年7月,郭学宏正式被撤职。5个月后,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依然判决马东昌胜诉,但郭学宏的处分也没被撤销。
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得知伊通县纪委副书记殷国军的两点意见代表了官方的调查结果,一是当年处分郭学宏仍然是因法院办错案,二是吉林省纪委未干涉伊通县法院审判工作。
一名当地信访部门官员则告诉记者:“郭这个人啊,怎么说呢,一开始是指责纪委违规干涉审判,后来又咬定是对他撤职的程序不对,甚至找上当时被处罚的三个人一起上访,不过另外两人很快就退出了。现在他又患上了‘迫害妄想症’,老以为有人要害他。他本身有脑溢血,说真的,我们有时很担心他一时激动,出什么大事。”
押宝“温家宝秘书”
截至目前,郭学宏已经到北京上访过10多次,但基本不去长春上访。“我这案子省里定的调,只有去北京,毕竟在体制内这么多年,这些门道我懂。”郭学宏说。
四平市信访部门一名干部则指出,郭学宏走的不完全是正常上访渠道,他去北京越级上访就属于违规,除此之外,他还动过“歪脑筋”。2010年,郭学宏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自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田野和自称在《人民日报》工作的高小丰。
经过几次接触,田、高二人自称可以帮忙找时任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的秘书帮忙,但需要20万元来“活动活动”。郭学宏立即给了他们5万元“首付”。
“当时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我们3个几乎天天见面,光是请他们吃饭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田野是个女的,特会给人下迷魂汤。”郭学宏陷入痛苦的回忆。
又过了一段时间,田、高二人联系不上了,郭学宏此时才意识到遇到骗子了,选择了向北京警方报案,但没有下文,“毕竟是自己没走正规渠道,也不好去追查了。”他说。
“作为一名曾经的法院副院长,你怎么想到采用这种非正规做法?你是不是依然觉得批条子最管用?”记者不解。
“当时是很绝望,感觉那是唯一的指望了。”郭学宏有点后悔,“事后才意识到这种方法本身的确是错的。”
当时被撤职的3名法官,如今只有郭学宏一人仍在上访。原院长姜守臣和庭长张志信没多久后就被安排到别的地方上班。知情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姜的亲戚是吉林省上某重要部门的一名领导,记者在一份四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名单上看到,2010年12月14日,四平市人大任命姜守臣为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此时距离姜被免去伊通县法院院长职务尚不足半年。
一段时间后,姜又担任了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助理;而比郭大8岁的张志信由于本身年龄和职级因素,在贬为执行局一名普通干部后,淡出了公众视线。
“老郭越访越病”
伊通县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也找过郭学宏谈话,希望尽早解决此事。郭学宏要求“软办”向自己道歉,撤销对自己的处分,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对此,伊通县方面表示,关于撤销处分,县里肯定是无权做主的。经济补偿问题,可以慢慢商量。
既然上面都松了口,那郭学宏为什么还要一直上访?
这里面家人的作用是巨大的,郭的家人表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让他讨回‘公道’。社会上对法官犯错是很关注的。现在一出去,街上人都议论老郭贪赃枉法了,我们受不了这个打击。”
此外,还有一些过去同事的“撺掇”。郭学宏一名曾经的同事就多次“替他不值”:“2006年四平市的7个县区选拔了7名副院长,你是最年轻的。现在这里面3人都是副县级了,而你……”
还有人对他说,“你运气不好啊,你当副院长时是副科级,现在的法院副职都是正科级了。”
很难说这些刺激性的言语,在郭学宏这里起到了多大作用,但对其或多或少有点转变。记者多次劝他:“要不稳稳,先把身体养好了?”
“我肯定还要上访,上访是有《信访条例》规定的,选择上访是遵法。”郭学宏朝记者信誓旦旦,“我不会做那些极端的事情,第一,我曾是法官,对法律还有起码的信仰;第二,我既然来自体制内,就不会‘闹访’,‘闹访’是一种很低级的手段。”
郭学宏的律师林波则告诉《廉政瞭望》记者,“老郭是病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其实对他的上访,我并不是多支持,这件事很可能不会有一个他理想的结果。”
而连续几周来,郭学宏反复在网上展开实名举报,并贴出有人在微博私信上给他的警告:请不要与某些部门作对,否则下场很悲惨。
“这肯定是李明国一伙干的!红尘万丈,人生浮沉,我早已看破。要来就来吧。如我突然消失或被捕或死亡,必有黑幕!我早已把遗嘱写给了我的律师,现我已无畏生死!”他有点“语无伦次”地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虽然这个发出“威胁”的ID,一看就是个安徽的普通网友。
前警察十年难觅“清白”
“我们的确集会搞过活动,但这次真没有!”
何祖华怎么也想不到,今年5月,因在北京国际园艺博览会的门口站了一会儿,几天后,他和同伴会被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刑事拘留37天。
进了北京市看守所,他才知道,原是警方抓错了人,误以为他们参与了当天的一起群体闹访。
何祖华自叹运气不好,却也暗自庆幸,他是这批人中唯一拿到官方手续的。
所谓的手续,其实不过一张进所时随身物品的检查证明,以及北京市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同意“取保候审”的文书。但在何祖华的眼里,“这是非法拘禁的证据。”
记者问:“你的证据意识很强。”
——“我以前是警察,更早前,还是一名警校教师。”
咖啡因悬案
1993年7月,河南辉县市新辉制药厂业务员申伟举从湖南购买3吨咖啡因。货到新乡铁路货场(不属新乡县管辖)即被新乡县检察院越权以“打假”名义连人带货扣押,申伟举被刑事拘留。
在该院部分办案人员收受申家礼金并发现咖啡因并非假货后,将申伟举取保候审,又将咖啡因贩卖,共获利约14万元。
其后事情败露,案件于次年1月移交至新乡市公安局预审科,由李立富主办,何祖华协助。这是何调入公安局参与办理的第一起案件,那一年,他33岁。
李、何二人调查后认为:该案中申伟举是制药厂业务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其有犯罪事实(据申伟举事后供述,他第一次被取保后就回到药厂与相关领导串供,获得了伪证),且申已被羁押10个月,严重超期,又因咖啡因被新乡县检察院倒卖,两名民警旋即向上级汇报。局领导授意不再调查,市领导则指示交由新乡市检察院处理,最终申被释放,新乡县检察院有关涉案人员也未受到任何处理。
此后,新乡市公安局预审科撤销,并入刑侦部门,该案不了了之。直至2000年,事情突然出现转折,申伟举又因运贩大量咖啡因,遭人举报后被捕。
2001年新乡市检察院成立专案组,由该院法纪科主办。
时任法纪科长的卫安刚、副科长秦体全在调查中发现申伟举于1993年先被拘后释放的情况,便怀疑当年公安局办案人员徇私枉法。
适逢河南检察机关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打击黑社会保护伞行动,求功心切的办案人员迫不及待地向上级汇报,称“在新乡市公安局挖出一个黑社会保护伞”。
李立富、何祖华随后被拘捕。何祖华回忆,自己曾被当面呵斥:“你们的局长、科长马上也要进来。”
然而,在调查取证后,检察院逐渐意识到,他们对案情的预想存在问题。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正确做法是撤销案件,但那样就没法向上级交代。为逃避错案追究,他们选择了将错就错,制造伪证,对我和老李强行起诉。”何祖华说。
反对声中的判决
2002年,获嘉县法院两次开庭,何祖华与李立富拒不认罪,最后各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悔罪表现,却还能被判缓刑,这不是很荒谬么?”何祖华称判决书上漏洞百出,语气带有不屑。(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拒不认罪、无悔罪表现的犯罪分子,一般不适用缓刑。)
“在法院宣判的时候,我们实际已被羁押了351天。”他如此理解1年徒刑的由来,
在这351天里,何祖华、李立富被新乡市检察院转移了3次。
起初,他们被羁押在新乡市的延津县看守所,后转至焦作市修武县看守所,最后因回新乡市内审判,又移交到获嘉县看守所。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什么重刑犯,被这样重点‘照顾’。”
何祖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新乡警察干校当过5年老师,预审科撤消后又调入监管处,同当地收押场所颇为熟络。
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是,当他被送进看守所时,所里干警都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何老师,你怎么来了?”
在面对普通干警时,何祖华会收起硬气的一面,仍保留着文人的幽默,他会心一笑:“我是来卧底检查工作的!”
在看守所外,此案却引发了新乡政法界的轩然大波。
政法委曾会同相关单位专门讨论,认为案件存有漏洞,不宜追究。但在新乡市检察院的一再坚持下,依然诉诸法庭。
诉讼过程同样一波三折。
据知情人士介绍,原本新乡市检察院希望归属地新华区接手,但被回绝。其后指定到获嘉县法院,合议庭同样认为证据不足,案件不应成立。“他们不止一次向市检察院和法院反映,但领导却授意必须将此案办成。”
在获嘉县法院开庭审理时,新乡各地公检法职工三百余人涌入法庭。
庭审现场一度混乱。公诉人每每被回应得无言以对,好几次趴在桌上,旁听席上一再发出嘘声。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场面更是近乎失控,有人开始喧闹,有人喝倒彩……
而在宣判当天,更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等到公诉方离开法庭,审判长突然转向何祖华:“小何,对不起,请你谅解。”
“我愿干信访”
重获自由后,二人开始不懈申诉。李立富因年龄原因被公安局办理了提前退休,何祖华则被安排到局里办的“保安公司”。
“老李的(着落)比较好,可我还年轻,心理上受了摧残,一定要告回来。”
由于何祖华的一再状告,案件引起了各级政法部门的重视。曾有一段时间,他的确看见了希望。
2006年3月,新乡市政法委工作组对本案重新看卷、访谈,最后形成书面意见:该案的主要证据是证人证言,这些证据确实互相矛盾,建议商请省高院立案再审。
一个月后,何祖华又分别向河南省人大和省高院反映情况。省人大认为案件确有问题,便向高院行函要求审查本案,河南省高院也于当年6月向新乡市中院下达再审决定。
何祖华称,“这是在无数次的上访中,对我们最为有利的一次回应。”
然而,2007年底,新乡市中院再审,维持原判。
何祖华不服,他把判决结果归因于李绍君。李绍君现任新乡市中院副院长,主管刑事审判工作,而在此之前,他正是新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申诉没有停止。
后来,他又给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写信,获得批示。调查组来到新乡,待了近一个月,却依旧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在周边人看来,何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倔。同情他的人渐渐疏离,家人也遭受到莫名的压力。
“我爱人原是医院院长,只好调到其他地方;女儿在私企工作,后来企业施压,离了职。”何祖华心存歉疚,“保安公司也劝退了我,现在我没了工作,还得靠家里接济。”
但这些年来,家人没有过抱怨,直到这次,他在维权路上又被关押。
一向坚韧的妻子痛哭流涕:“你知道吗,全家人都快急疯了。”
何祖华却用自己的方式宽慰她:“很多人上北京回来,不是劳教就是拘留,我去了这么多回都没被处理过,因为我懂法,知道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这回是他们弄错了才把我给抓了。”
可事实并非如他所说的那般轻松。因长时间得不到满意答复,何祖华的行为也开始变得不大理智。
他接受过多家外媒采访,又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蒙冤”警察,搞了多场集会,还拍成视频传到网上,一时引发舆论热炒。
他也不止一次被不止一地的警方约谈,最终都因其曾经的“同袍”身份而被网开一面。
何祖华清楚自己是在铤而走险。
“这对你和国家都没好处,甚至会适得其反。”记者规劝他。
——“我认为,只有把声势壮大,得到最高层的关注,(案子)翻过来才有希望。”
“那你的诉求究竟是什么?”
——“起码要恢复我的名誉与公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去搞信访。”何祖华想了一会儿,补充说。
何称自己看不惯衙门作派。他曾亲眼目睹,有访民带着精心准备的材料去信访局,却只让填个表,材料一律不收。因自己的案子被卢展工批复过,信访局才答应收下。
“信访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人避之不及。但我的经历,一定能够将心比心,取信于民。”
自认蒙冤、利益受损、举报……每个体制内的访民上访理由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熟悉体制运作,更加克制、冷静,他们知道底线在哪儿,目标也更明确。
从官员到访民
不回家。
5月14日,董超出狱见到妻子,只留下一句话。
他是要去上访。
2007年,因被控通过虚开餐饮发票贪污徐州新典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经费5.1万元,董超被江苏丰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前,他是丰县发改委纪委书记、上述公司破产组副组长。
董超不服法院判决,认为多开餐饮发票是为报销工作垫支的费用,实际只有3万元,而且检察院提交的证物——2张领取破产经费的支票是伪造的。
服刑期间,董超分别向中央纪委等部委写了共208封信,但均杳无音讯。减刑提前释放时,他才知道,所有举报信都被监狱扣留了。
这让董超心里憋了口气,决定出狱后直接去递材料。董超早已被“双开”,但他曾在体制内。
体制内的上访,不是一种新现象。
早在1968年,周恩来就专门成立了“总理亲启信办理小组”,接见到北京上访的人,干部是其中群体之一。最近落马省部级高官背后,也总能看到退休老干部上访的身影。
三类上访者
“体制内的上访多着呢”,一名在市、县、乡均工作过的官员称,只不过他们很少为外界所知。
以上访理由为标准,体制内的上访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如董超这样,自认蒙冤而上访。他们人数不多,但外界了解最多的反而是他们,例如“湖南级别最大上访户”谭照华。
2003年,谭照华因受贿5万元、挪用公款4000多万元,获刑8年。但这名原湖南省物资厅厅长坚称自己无罪,此后6年间,申诉不断。
在超过40次进京申冤、写下两大箱申诉材料、从62岁变成72岁之后,2009年9月,谭照华案再审开庭。最终,昔日被称为“三湘第一贪”的“谭照华贪腐大案”,被证明是一起错案——2011年1月,湖南省高院宣布为谭照华平反:撤销原判,谭照华无罪。
谭照华并非典型的案例。这类上访中,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大多数均有瑕疵,但一方“非要有个说法”,另一方因当事人是体制内的人,判决牵涉较大而拒不松口,致使难以息访。
第二类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上访的体制内人员。2002年就退休的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内上访者。
2007年,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吴宗明家的房子面临拆迁。由于认为拆迁补偿和安置不合理,吴宗明从一个接待上访者变成了上访者。
“有时候想想,觉得也挺可笑的,信访办主任上访。”吴宗明自嘲,“然而,除此之外我已没有更好的办法。”
感觉穷途末路的也许还有梦鸽。8月19日,梦鸽因为其子李某某案件,到公安部信访办公室上访,递交资料。此刻,她与吴宗明并无差别,只不过一个已经退休,一个仍在岗位上。
当然,体制内的上访并非总是涉及自身,也有出自公心,上访举报腐败或其他问题。这是第三类体制内的上访者。
这其中,退休老干部是主要群体。例如2011年,因为时任领导借旧城改造“侵占耕地、强拆民房”,以及存在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山东平度市原人大主任等十余名老干部集体上访。
最近落马的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也因为主政六安市期间卖掉机关大院,引发老干部不断地给省市领导和中央领导写信。
他们是怎么上访的?
与体制外的上访者不同,体制内的上访者一般否认是上访,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例如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陈玉莲。
陈玉莲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2010年,她在去找湖北省政法委副书记时,在湖北省委大院门口被保安殴打。
虽然她否认自己是上访者,但找政法委副书记,陈玉莲主要是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
体制内的身份显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特权,制度面前无人例外。
但相比较而言,体制内的上访者更克制、冷静。他们熟悉体制的运转规则,知道如果过激,“接访人员或者相关单位只会把我们视为麻烦制造者,这样对于问题的解决反倒有反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吴宗明不主张“钉子户”们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因为“那里人那么多,不要说解决问题,能有说话的机会就不错了”;他也不参与“钉子户”们集体上访,因为人多了不符合《信访条例》的规定,再说“影响不好”;他承认上访作用有限,但“毕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个渠道”。
“我们不是要捣乱,只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一再强调。
他们大多知道底线在哪儿,除非迫不得已,更愿意独自走在上访路上,很少希望公众或者媒体介入,即便等待一个说法要很长的时间。
平度市老干部上访被曝光后,就颇为谨慎,不愿意通过媒体扩大影响。一名老干部说,自己是党员,上访举报问题是内部矛盾,应该在体制内悄悄解决。而且他觉得将举报对外曝光“没有意义”,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们的目标也更明确。谭照华近十年的上访路中,没有漫天撒网,就只找最高法院。
他们如何变得偏执
并非每个体制内的上访者都如此平和理性。
2012年4月,原福建寿宁县信访局局长柳乃华和家里的亲戚30余人,就在厦门市政府门前长跪不起,以此为在厦门打工突然死亡的女儿柳鏐“讨公道”。
“信访局长下跪上访”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
部分体制内的上访者之所以会越来越偏激,与他们的心理落差不无关系。
2008年,因为妻子胡敏面临被自己的单位解聘,湖北孝感中院助理审判员冯缤先到孝感市劳动局等部门“讨说法”。多次无果后,冯缤变得有些激动,不仅将自己的“老板”——孝感中院告上了法庭,还穿着法袍上访、与人拳脚相搏,甚至一头撞向从湖北省高院里开出来的车……
虽然孝感中院方面,曾多次与冯缤进行沟通交流,希望不要把事情闹大,但冯缤却固执地要求孝感中院必须与胡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尽管胡敏只在孝感中院连续工作满8年,而非10年。(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便可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冯缤与柳乃华一样,认为“信访局能力有限”,下跪、上访、拳脚相搏无非是要见“领导”、盼“批示”。也许正是基于对“法治”的缺乏信心和对“人治”的依赖,以及对“信访局夹在老百姓和应该负责的相关部门中间,难受啊”的职业理解,才让他们的上访之路越走越偏激。
偏激的体制内上访者,最大的相同点还有“执拗到底”。这与他们个体的“上访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下跪后,柳乃华解释称,当初到市政府门前上访更多源于亲戚,“我那么多亲戚在那里陪我们一个多月了,天天都盼着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们都很急很急,所以就跑到那边去,想找到市主要领导。”
之所以会下跪,更是因为“我的亲戚们先跪下去,我后来到那里,我支撑不住了,一下子就蹲下去,就摔下去,后来就坐在那里。”
与体制外的上访者相比,他们显然更容易被现在朋友、过去同事的眼光、劝说等外部因素裹挟,不得不在上访路上走下去。
应该反思什么
没有人想成为上访者。
体制内人员的上访不应该被看着是一种尴尬、悲剧,或者幽默戏。面对“信访局长上访”等事件,嘲讽甚至快意其个人“报应”,既不厚道也没有多大意义。体制内上访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同样,他们也需要依法上访,避免上访过程中的情绪表达。相较体制外的上访者而言,他们的行为更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性。
不能说上访者都有理,他们的诉求有时也偏激,但对于制度来说,不管是面对体制内的上访,还是体制外的上访,需要更多承担与勇气,更需要认错、纠错的意识与机制,尽可能给所有愤懑、冤屈一个出路,哪怕“泄”掉他们心中的火气也行。防止“访”上邪路、绝路。
2009年9月,谭照华案再审之前,就有人提前放风,“如果给谭照华平反,会引起湖南动乱。再审开庭后,湖南省各政法机关对于谭案是否平反意见并不统一,有政法机关人员甚至表示:若对谭案平反,未来工作很难开展,举报人会对平反有意见,同时也会影响领导的威信。
湖南省高院最终宣布谭照华无罪,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值得肯定。
但社会矛盾的纾解不能仅靠某个群体的自省。充分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真正的法治社会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而非仅仅依靠信访。
一旦“信访不讲法”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选择,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利益诉求不断向信访渠道汇集,那么,在不堪重负以及地方政府“维稳”压力下,再加上“信访”固有的权宜性,“信访”自身势必也将不断趋于变异,同样变得越来越不被信任。
所以,归根到底,民众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纠纷、冲突的解决,还要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
2011年底,湖北高院驳回冯缤妻子的再审申请。冯缤从湖北高院接过民事裁定书后,在博客上写道,“为了法律的尊严,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尽管他的上访行为有时偏激,但他上访目的还是想依法解决,“无论是多大的官,职位有多高,今天还是需要法律来保护你,你终究还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