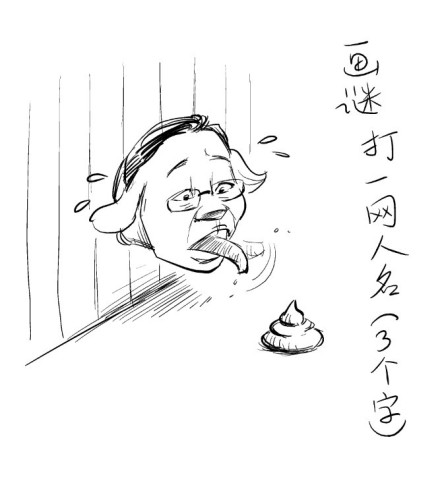一、《环球时报》社评最爱用修辞
中国媒体评论,与过去几十年居高临下的宣传教化的姿态相比,当代的突出特点,就是更为平等(因此也更为强烈)的说服动机。尤其是在多元的——乃至冲突性的议题背景下。这个特点表现在写作方面,就是修辞的自觉使用——我不是指文艺学意义上的那种使词句优美的修辞,而主要是指古希腊公共辩论时代就已被开发出来的、具有强烈说服效果的修辞。
在我看来,在我国的《环球时报》社评中,修辞意识最强烈,修辞案例也最丰富。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环球时报》社评:“他们喜欢将象的概念具体化,当他们把现今的中国比作‘堆满问题却充满希望的码头’,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再次装修’,把西方的干涉比作‘自摆乌龙’,把诺委会的作为比作‘构筑人类观念的三八线’。”
对于一般说来要比新闻报道要抽象一些的评论来说,满纸“形象”不是总要比满纸“抽象”更有亲和感吗?
比如,2012年6月,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邀请22个国家,却没有邀请中国。《环球时报》社评《有点“孤独”是中国崛起的正常境遇》就有这样一段修辞:“中国遥望这个军演,当然不会舒服,但这种不舒服应像要出门游玩正好碰上下雨般不愉快一样很快被忘却,而不应长久影响我们的心情。看上去宏大的环太平洋军演,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小动作’,是美国因种种现实问题长期郁郁寡欢时给自己办的一次大派对。”
这是把国际战略描述与普通人的生活语汇“接通”的修辞策略。严肃的议题也轻松化了。这在《环球时报》社评中比较普遍。
再看这个——2012年4月18日社评《东京花钱买不到钓鱼岛主权》:“石原培育了一些日本人在全球化时代神风队飞行员般的慷慨激昂和悲壮,他给日本人戴上3D眼镜,那些成队驶来的中国商船看上去就像攻击日本的航空母舰。日本成了随时都需要奋不顾身进行保卫的国家。”
——这不是很有一种奇妙的画面感吗?
二、修辞的水深了去了

有一部美国的批判性思维教材,由余飞、顾友倩两位学者译入中国,叫做《批判的思考》。它对修辞有这样一个界定:“有时在不提供理由的情况下,说话者和写作者也能使人们接受一个判断,或者影响某人的态度或行为。我们把这叫做修辞。”
你看,这个对修辞的定义,其实并不太友好,是吧?还有比这本书说得更不客气的。《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8期曾有书评介绍过英国《每日电讯报书》书评编辑莱斯的新著《你是跟我说话吗?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巴马的修辞》,其中写道:
“修辞是语言的游戏,是它在说服和勾引,激发和欺骗,惊吓和误导,它使罪犯被判刑,接着又在上诉时使那些罪犯获释。它使政府上台和垮台,使理智的成年人淡定地朝着机枪挺进。修辞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成双成对的词语;排比、重复的句子;半真半假的话,悦耳但无意义的话,虚假的对比、抽象的名词和没有根据的推论。”
正是针对这一类对于修辞不太友好态度,当代西方倡导“新修辞学”的英国著名学者图尔敏才用这样一句话为修辞抱不平:“与逻辑的‘形式证明’相对照,对修辞学的损害名誉的描述是‘不诚实的说服’”。
——他认为修辞学被损害了名誉。
关于“在不提供理由的情况下,说话者和写作者也能使人们接受一个判断”这个对修辞不够友好的定义,如果不举出一个案例,人们不太容易理解。那么,我就举出一个来吧——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培根,中国人大都知道。因为他的一本《培根论说文集》,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版本之外,在中国还有多种译本。其中有一篇《论国家的真正伟大》有这样一段修辞:
“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
你看了这一段,可能会认为对外战争对于国家是必要的。但他除了把国家比喻为生物体,把对外战争比喻为运动之外,却没有为国家发动对外战争提供真正的理由。
实际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比喻之上的“国家有机体论”,后来被德国纳粹的军国主义理论和民族扩张理论积极吸收了。
我引一段墨索里尼的话为证:
“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其效用,因此,法西斯主义拒绝永久和平主义——它源自放弃斗争以及怯于牺牲的懦弱行为。战争将所有的人类活力提升至最高的张力,并将高贵的标志印在有勇气迎接它的人身上。”
(引自(美)利昂·P•马拉达特著张慧芝,张露璐译《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10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版,256页》)
这是培根没有想到的。培根不能任其责。但这种依靠修辞进行思想与说服的方法,恐怕难辞其咎。
其实,反法西斯的西方民主国家领袖,在论述国家的伟大时,对于这种基于“国家有机体论”的修辞的力量,也没有免疫力。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1941年的一篇演讲:
“国家像人一样有一个身体——它必须以我们时代的目标为标准,得到吃、穿、性、活动和休息。”
“国家像人一样有一个脑袋——它必须了解情况和处于戒备状态,它必须了解自己,了解邻居的希望和需要,这个邻居就是生活在这个狭小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其他国家。”
“国家像人一样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它还有更深、更广、更持久的东西。这就是关系到它的前途的东西——唤起民众最神圣地保卫其现在的东西……”
“它是精神——它是美国的信念。”
你看,他只是为了说明“美国精神”,竟然把国家与人一一对应起来,居然还谈到了国家的“性”,倒令人无从索解了。
而我们习见的“国家脊梁”或“民族脊梁”的修辞,也无非是这一脉源远流长的“国家有机体论”思维模式基础上产生的赞语。只是到了2010年,当一位原央视主持人被某机构评上“国家脊梁奖”机时引发的争议中,我才有机会看到一篇对这个词语的尖锐批判:
“在政治、文化领域套用自然科学术语是用词不当。把国家、民族想象为一个有机体,不过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对“有机体”这一化学词汇的滥用。在习惯于用整体论的方法进行思维的人们那里,这种拟人化的词汇混用(活用)才是有效的。对于反对用整体论的方法思维的人们来说,国家、民族由一个个的人所组成。这些人不可能像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那样被当成零件来组装成一个超人的活体。
国家不过是由独立的个人按一定规则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个人仍然是独立的行为主体,个人对于共同体的作用和价值固然存在大小之别,但每个人在生命与权利诸多方面却是等价的,不存在谁谁是少不得的心脏、脊梁,谁谁是可有可无的毛发、指甲。”
——这是2011年8月2日《南方都市报》“虚拟@现实之乐天马专栏”的文章。我读了这一番话,心有戚戚焉。长期以来,我就觉得,应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揭示人们思维和表达的误区,揭示表达方式——修辞对人们思维的限制。这正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批判性思维对人们现实观念的重要影响作用。而这篇文章则揭示了表达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世界观。
三、《环球时报》社评修辞的强悍与委婉
好了,上面我想说的只是:修辞的水很深。不过,我们倒是不必对修辞抱什么成见。我还是拿《环球时报》社评中一些有意思的修辞案例来说吧。
比如,藏在隐喻中的贬抑是最为常见的案例。说白了,就是人常说的“骂人不带脏字”。
在2013年4月一篇社评《无论起因是什么,朝鲜都做过了头》中有一句:“朝鲜政权在使劲跺脚、敲锣,震动了世界。”
这个形象的描述是一个隐喻:它暗示朝鲜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一样。其中潜藏着负面评价。
隐喻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修辞格,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的说法,就是:“若诗人说阿基里斯‘像一匹狮子似的冲了上去’,这是一个直喻;而若说‘狮子冲了上去’,就成了一个隐喻。”——这看似很简单,就是不出现喻词“像”“如”和比喻的本体。但上述《环球时报》社评的隐喻更“隐”,它隐去的是明确的贬意。因为这么明确地贬抑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太合适的。
同样的案例还有:在2012年4月的一篇社评《一次在南沙海域维权的成功之举》中,有这样一句:“中国没有向菲律宾嘴里塞糖果哄它的义务。还请菲律宾自重。”。什么人才会让人“嘴里塞糖果哄”呢?自然是小孩子。但是,我可没说啊。
在对外关系议题的社评中,《环球时报》的社评,还有更狠的。
2012年7月的一篇《中国在南海是被蚊子骚扰的“被动”》中,有一句:
“中国看上去被动,但我们是被蚊子骚扰着的被动。我们可以晃晃头避免被咬,但急了我们可以动手打这些蚊子。”
2012年5月9日的社评《常此摩擦,中菲不动武将是奇迹》明确表达了对菲开战的诉求。文中有一句:
“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的骚扰挑衅像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粘在中国脚上,要彻底把它蹭干净看来不太容易,中国将不得不在很长时间里感觉脚底下黏糊糊的。但中国的确要把鞋底找个硬处使劲蹭几下。”
这一类在感觉上显得“粗直”的修辞,都增加了《环球时报》在对外部冲突议题中的强悍风格。这已经同以往党报评论在涉及对外关系议题中至少大面儿上保持的平等姿态相距甚远了。
与“粗直语”相对、相反的一种修辞格,就是委婉语。
委婉语作为一种修辞格,其实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语汇中,比如,“厕所”就是委婉语,尽管你已经不觉它委婉了,所以你接受了更委婉的“洗手间”。
我录一段我们学院教务秘书的一段通知,你看看其间哪个词是委婉语:
“鉴于去年有学生毕业论文重复率过高,得到学校责令其延期毕业的处罚,今年,恳请指导老师从学生撰写论文开始,就务必提醒并严格把关。”
——其中,“重复率过高”就是委婉语。它实际指的是什么?你明白的。
而《环球时报》社评中有一些委婉语,同样表达强悍立场。
在《环球时报》9月18日社论《回望918 中日实力已发生历史性逆转》中有这样一段:
“中国老百姓上街抗议日本等‘列强’,曾是孱弱中国对抗外部侵略和挑衅的主要表现之一,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社会很突出的爱国主义习惯。或许这一页该逐渐翻过去了。中国已是有国家力量的大国。美国的民众从不上街抗议外国,美国靠的是行动。但中东的弱国小国只有民众抗议这一个办法。中国的对外反应应向大国强国的做法逐渐‘转型’”。
这一段有委婉语之效,即它认为,中国的对外反应应当转变得像美国那样:“行动”,而不只是“抗议”。而谁都理解美国那样的“行动”是什么。我们通常用比“行动”一词更负面的词语来描述之,并批评那样的“行动”。所以“行动”就是委婉语——它是“战争”一词的委婉语。
然而,在其英文版《Sep 18 offers chance to reflect on war》中,这一段却似乎更为“委婉”:
“Demonstrations used to be one way that China dealt with invasion and provocations by other countries when it was a weak country. It is still the means through which Chinese show their patriotism. Perhaps we should gradually leave such means behind us, as China has grown powerful.”
——在这一段中,中文版关于像大国那样“行动”的意思不那么突出了。只明说:“随着中国的强大,我们应该逐渐告别示威游行这种方式了”。
这是不是因为,这种本来就需要委婉表达的意思,在外部世界可以直接看懂的语言中需要更加委婉呢?
四、《环球时报》社评的修辞在中、英不同文本中的差异
由此,我顺便谈谈《环球时报》社评的修辞在其中、英文版两张报上的差异。
一种最简单的差异,就是中文版社评中有的修辞,在英文版中消失了。
比如,前面列举的“蚊子”“口香糖”的修辞,在相应的英文版中都没有。可能是因为翻译不出来,也可能是因为它们表达了对一个国家的蔑视。
一个比较典型对比案例是:在2012年7月的社评《菲律宾不值得中国集中精力琢磨它》有一句:“菲律宾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中国外交大战略中的一个‘玩偶’。它耍浑,我们就给它来硬的。它软下来,有了一些教训,我们也可以给它台阶下。”其中,“玩偶”这个修辞,英文版中换成了“small player”——小玩家,两者明显是不对称的。英文版之所以换成“small player”,这不仅因为后者其实更准确,而且因为前者具有明显贬抑性。
在2012年1月21日《环球时报》中英文版的同题社论《中国是什么样的龙”》中发问:“中国是条什么样的龙?这个问题是忧虑的,甚至不怀好意的。”
而其在英文版(Chinese dragon waits for recognition)的相应句子则是:“中国是一种什么龙?这个问题是充满忧虑的,有着含蓄的动机”。(What kind of dragon is China? It’s a worrying question to ask, with implicit motives.)
相较而言,“不怀好意”所表达的负面的、攻击性的意思,就比implicit更明显。后者直译就是“含蓄”,是中性的。此例反映出:在表达负面的、攻击性的意思方面,中文版比英文版表达得更为明显。
2011年12月27日的社评《“抗议之年”,思想不能输给口号》与英文版同题社论提到:“在西方,抗议成了社会的出气阀,主流社会对抗议很宽容,同时也很蔑视。”
而英文版对应的文字中,“同时也很蔑视”这一分句竟然不见了。
但也有的时候,反过来,在中文版里没有的内容,英文版里却被加上。比如,2012年3月27日社评《舆论不应鼓动超现实的福利目标》有一句:“曾有名人在两会上宣称美国的电话如何便宜,后被证明说错了,但没受到什么谴责。”
这是谁啊?没提。而在相应的英文版中,则指明此人为崔永元。于是,中文版中的“名人”就成了修辞——“崔永元”的委婉语。
这可能是考虑给英文读者留下更详细的信息,而给小崔留下一个面子。
(责任编辑: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