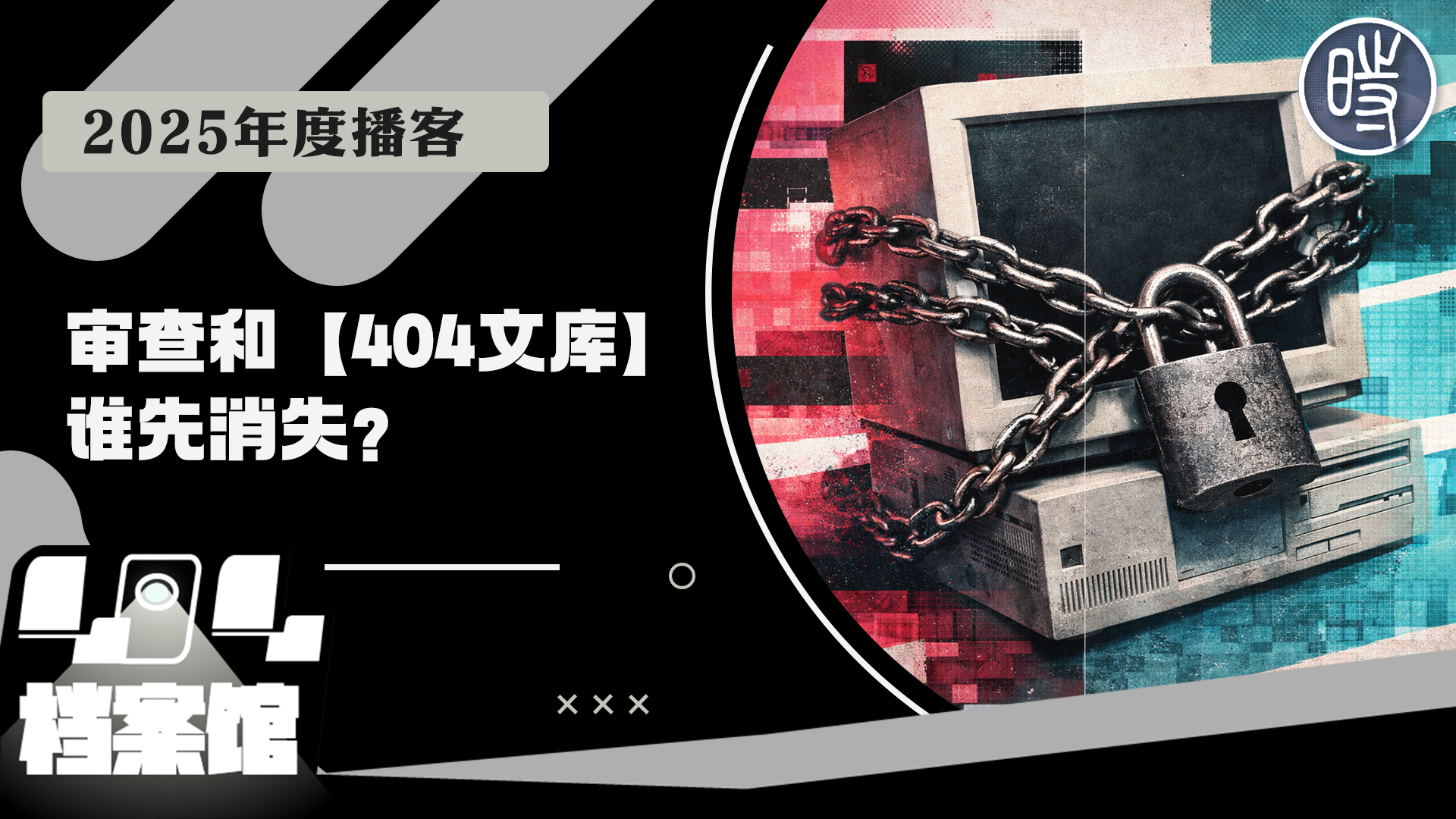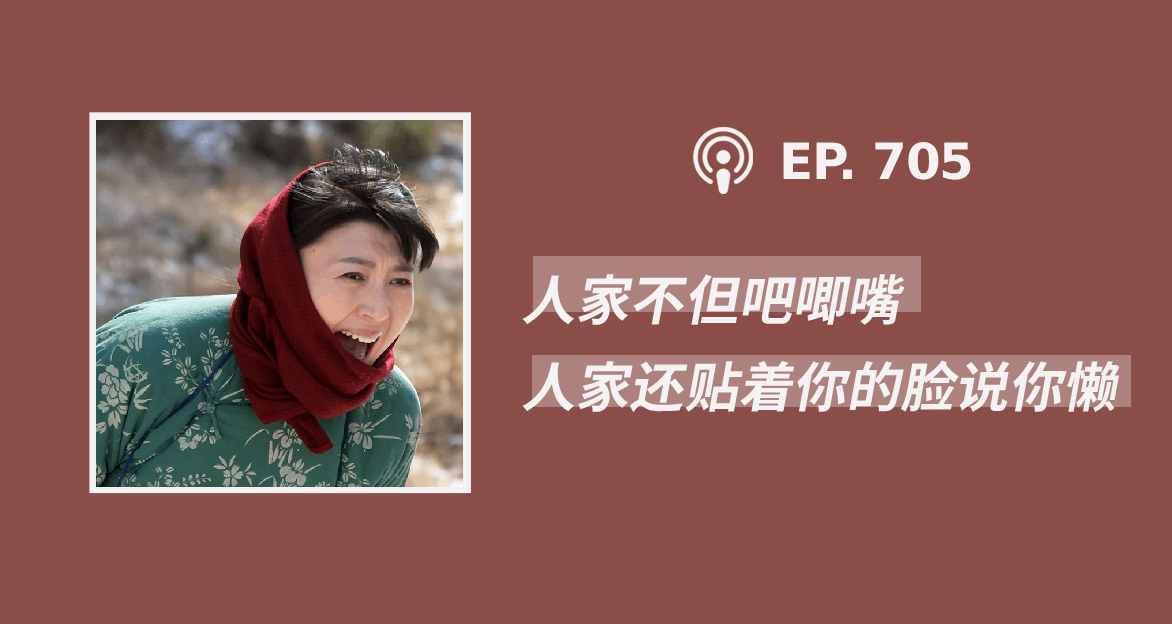“延安时代”在中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介绍延安方方面面的书籍文章虽称汗牛充栋,却多属云山雾罩的政治宣传;既如风行一时的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点研究价值的如当年苏联塔斯社延安特派员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孙平)、美国“延安观察组”成员等、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相关著作,则嫌太“隔”。至于那些到此一游的边区访客,虽有立场比较超然、角度比较个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浅。文革以后,“延安老人”可以讲话了,回忆文章时见报端,细读仍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年淹代远,故事的真实度、完整性,不是从“记忆的筛子”遗漏过半;就是被变迁的时代、转变的立场,潜移默化偏离了本来面目。
终于,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许多偏颇。历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刊出过分日记,这里更全。
延安整风
党史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在“后记”中无奈地叹到:“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延安整风”,曾是中共禁忌的话题。文革中毛泽东本来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陈毅以“文革”比拟“延安整风”,致使毛泽东大怒。于是,我们知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其特色,其做法被历次政治运动沿用。后来,针对“延安整风”的揭发、控诉,也都围绕着无端被怀疑、长期受打击的主题。然而,那次整风更深层次的悲剧则鲜为人知—–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可知:“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为了解脱困境,他们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此等行径的直接后果,使党员与党的事业之间离心离德、党员与党员之间仇怨暗结,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
萧军日记中,初始提到“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大约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页数,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文抗在开讨论宗派主义大会,每个人全在发言,说自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不能勇于举出实例来。”响应号召是“党性强”的体现。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相信党、维护党,党却并不领情。领导整风的“学委会”一看,既然唾面自干,肯定心里有鬼!加码、再干!为严肃气氛,各单位的运动封闭进行(下卷P78)。此举施于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4月9日:参加杨家岭特务反省大会,……这是个特务自白的会,一共五个青年人,一个青年女人。” (下卷P81)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时、康生和刘少奇。(下卷P82)从此,运动进入“肃反”,特务大批涌现,罪行则无奇不有、证据确凿。如工业局长,使边区损失两千多万,政府秘书,借参加舞会绘制王家坪的地图;还有特意来延安熟悉生活习惯和术语的变节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抢救结束大会”上,“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个机关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会开得热烈而煽情,看似人们以“落水”为荣了:“趁了这机会,他们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愿坦白的条子。……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敌特分子现身说法的大会经常召开,“日记”时有记述,故事量大且繁、具体而微。特务之所以会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萧军袭来:“陈云给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连‘同志’两个字全没加”。(下卷P95)却原来,“康生在大会上说有人过去曾替王实味辩护过,招待所的人们就说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我对证。”(下卷P459)还“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下卷P564)(后来,雪苇向萧军表示了惭愧—–下卷P571):“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买物,据说组织部已经注意了,从此我知道他们对我似乎还在作一种无谓的‘怀疑’和监视”。(下卷P255。按:当年被派去“侦查”萧军的社会部干部、解放后官至边防保卫总局局长的慕丰韵,曾为文专述此事)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下卷P657)“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边区的文化人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畬、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湜、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启东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欧阳山来谈了一些闲话。我回来他又到我的屋子来,提议给我们四人—-艾青、罗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钱,算作《文艺月报》的编辑费,我拒绝了。1、边区无此例。2、我们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赃之嫌。……”(上卷P229)
这样的文化人,对“革命圣地”的态度,也很暧昧。“日记”中基本见不到他们因投身革命而热情、忘我乃至亢奋。常见的是气馁、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赵文藻告诉我,她初来抗大时,抱着怎样的光明理想,结果她被偷……被欺负……她背地里去流泪,现在她说,她已经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上卷P171)
“夜间作家俱乐部开观摩会,吃了酒。每个人全疯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滚着……这是人性和兽性的倾泄!李又然几乎成了狂人,他凄惨地叫了又叫,他因会上遭了凯丰的评论,黑丁底谋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于以个性乖张而不为人们所喜的王实味,这部日记也颇提到了几次。其实,萧军不仅并不认识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颜色。不顾安危地为王实味辩护,完全是打抱不平、对事不对人。
诚然,萧军比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隶属文化艺术圈,军队和机关中人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队伍,参与者中最狂热的部分多为文化者、艺术人,他们的兴奋点较低。这个圈子氛围不过如此,其他单位和部门中人的政治热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810.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中国数字时代亚马逊镜像(墙内可直接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