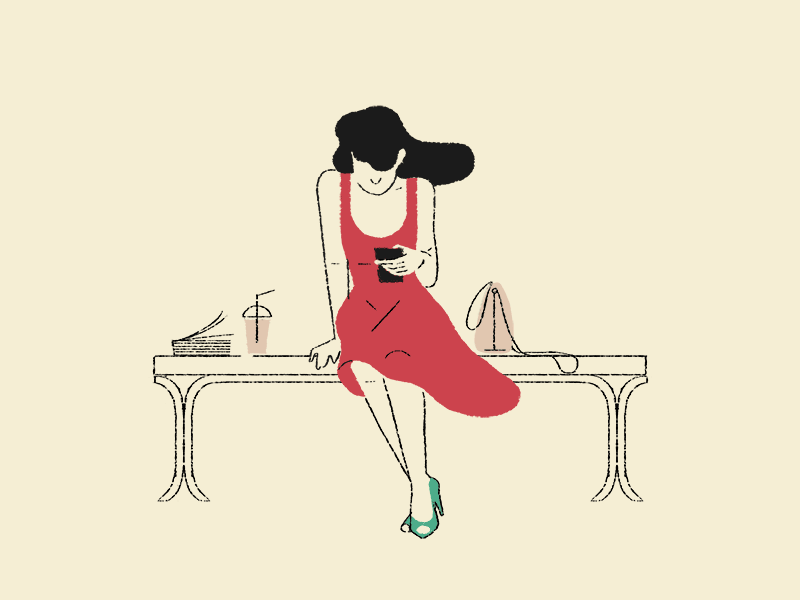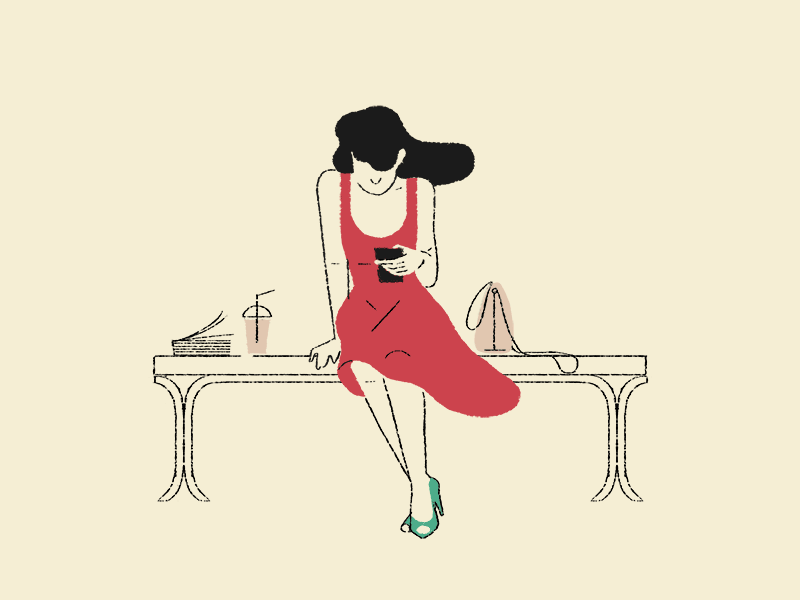我姥姥去世时,一个记录着全家族男性名字,包括刚出生不久的男婴名字的大花圈,醒目地挂在灵堂最中央。她的亲生女儿,在她临终前辛苦照料的我母亲,没机会把名字写到集体祭奠的花圈上。我这个外孙女更是外人中的外人,只在鞋上塞了一块白布,不可以和舅舅家的子女一样穿上孝衣。
你们听说过「绝户」这个词吗?念出来像一个诅咒。如果一个来自山东聊城的家庭,被用这个词形容,并不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意思,而是说这家人下一代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女儿是进不了族谱的,于是这家人就在家族名单里断档消失了,这就叫「绝户」。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出生。但聊城人有的是办法。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那边,三代人大家族里,并没有一个家庭在 80 年代之后成为「绝户」。约一半家庭是独生子,另一半家庭,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为什么第二胎都是弟弟,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就是一个有弟弟的姐姐。我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我妈精确计划着在过年的时间生产,弟弟刚出生就被抱到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两年之后才回家。父母按照我的出生日期登记弟弟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们真的是双胞胎。
成长过程中,我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因性别被区别对待。从出生就被迫和父母分离的弟弟,有远比我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斤斤计较着父母分给我俩的零食数量,先给谁洗澡,先哄谁睡觉,把这些视作「偏爱」的证据,在感觉不公平的时候放声大哭。
我想,在我家这种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双职工家庭,重男轻女已经失去了实践上的可行性,但「一定要有儿子」的社会规则,还是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观念里。哪怕为了达成目的,受到伤害的是儿子。
除了一定要有儿子,还一定要给儿子娶个媳妇。在聊城,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城市的同龄人都立志考公务员,进医院学校获得事业编制。很多这样的职位月收入一千多,却需要家长拿十几万去买。
在家长眼中,这笔钱一定要花,因为稳定的工作可以提高子女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工作,结婚,生子,是人的头等大事,每一项都值得花大价钱去完成任务。
在这里,婚姻是双方家长进行的一次交易。聊城一直有结婚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风俗。对彩礼数字非常讲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三万一千八,婆家娘家一起发」这几种。
「万紫千红一片绿」就是指一万张紫色的五块,加一千张红色的一百,再加一百张绿色五十的,总共十五万五千块钱。「三斤三两」就是用秤称出三斤三两百元大钞,约合人民币十三万六千元。
除了彩礼,还要给儿子准备婚房。对城市家庭来说,婚房加彩礼还不至于太为难。而对县里和农村家庭来说,一次结婚足以让男方家庭倾家荡产。在农村,彩礼通常直接落到女方父母手中。如果是姐姐出嫁,那彩礼也许就是她弟弟娶媳妇的本金。
农村出身本身就是减分项,加上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超过 120 : 100),农村男孩对娶媳妇的要求被简化为「是个女的就可以」。很多男孩在外打工,父母在家花了十几二十万,终于给儿子娶到,更精确地说,是买到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可能不是头婚,是二婚,甚至是三婚,是从上次不幸的婚姻买卖中逃跑出来的。
在聊城,很多恶性刑事案件很多都跟彩礼有关。比如骗婚诈取彩礼钱,婚后感情不和因退还彩礼的事酿成血案等等。
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子,一小伙家里条件很差,父母倾家荡产,还动用母亲出车祸得到的赔偿款,凑够二十万彩礼钱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可结婚后媳妇跑了。小伙迁怒于岳父岳母,将他们一个捅死,一个捅伤。这些新闻在当地也没有引起过特别大的波澜。大多被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聊聊就过去了。
我却始终无法把这些事当成日常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波澜不惊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才是这片土地对人们最大的诅咒。我为这一切感到愤怒和委屈。当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意识苏醒,想要自救的第一步,就是逃离此地,自己选择亲密的爱人,从事的工作,要不要生孩子。
想要逃离的,并非只有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有侥幸躲过生育筛查,又躲过了在婚姻中被交易的命运,或者从不幸婚姻中半路出逃的女性,都不愿意再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很多农村姑娘都去了城里打工,做一些零售行业,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只要基本生活能够保障,她们就会努力通过自由恋爱,把自己留在城市里。
自由伴随着升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感。但只有自由,才能提供人性伸展的空间。我现在北京,无法预测自己明年的生活状态,和很多「不正常」的人厮混在一起,总是被人类的多样性刷新认知。北京放大了每个人与众不同的那部分。我想,北京被推高的房价中,也包含了尊严和自由的价值吧。
我不知道是因为基因中的特别之处把这部分人带离了家乡,还是家乡的压抑环境杀死了人性中的差异,又或者两种情况都有。那列连接了家乡和北京的火车,每次乘坐,都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穿梭。
小耳朵说: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开明的家庭环境,让杏免于成为重男轻女的直接当事人。然姥姥去世不见母亲姓名的花圈,抖落着恐怖气味的「绝户」,新闻里数见不鲜的彩礼刑事案,已足够让她见识那片土地性别不公的可怖,继而做出自救逃离的决定。
那列连接了家乡和北京的火车,隔断了家乡的压抑与落后,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而那些频频从不幸婚姻中出逃,又被屡屡捉回的女性;未及成年便被安排婚嫁,以便为哥哥提供彩礼钱的女孩,她们的出口,又在哪里?那些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例子,哪怕是只是少数,也值得用力书写。
一如尼采所说,「个体必须始终挣扎,才能不被族群大众所淹没。倘若尝试,孤单常有,恐惧有时,但为了拥有你自己,任何代价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