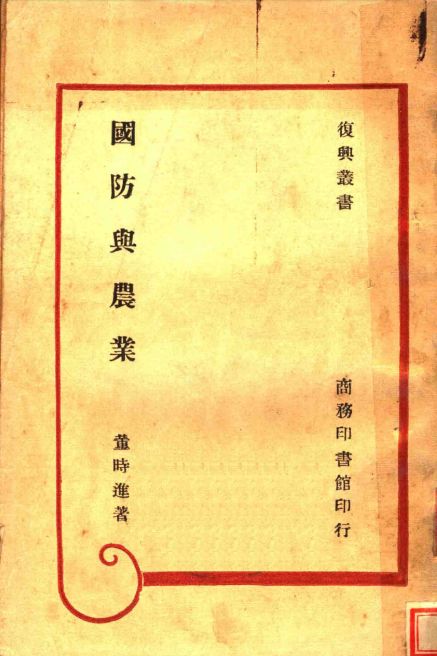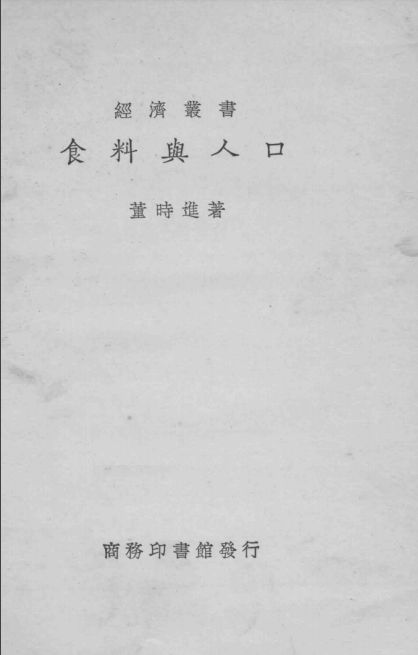文 | 黄家杨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1924年赴美留学,获农学博士学位。曾到欧洲考察农业和土地制度。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1949年后赴美定居,于80年代辞世。
由于各种原因,董时进一直被深埋于历史尘埃,未被国人所熟知。
对中国土地问题的“非主流看法”
1950年前后,董时进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土地经济以及土地改革的“非主流看法”。
董时进认为,中国土地制度的问题,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地主富农收取地租是合法收益,拥有土地并不是一种恶。
他质疑了“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的这一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该数据缺乏依据:
“第一,中国缺乏大规模的土地分配的普查,而且这种普查在中国近年的情况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姑不问其可靠性如何,至多不过是局部的调查查料。第二,表上的地主、富农、中农等分类的方法并无一定的标准,是可以随人而异的。”(《土地分配问题》,1948年)
并引用民国期间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数据,否定“土地高度集中”这一流行结论:
“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
董时进还以工业化最早和最彻底的英国,和实行土地改革较早的罗马尼亚为例,说明中国土地集中程度并未到“惊慌程度”,现时不应急于重新均分土地。他明言,中国当下的土地分配状况,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我们至少可以明了,中国土地分配情形还没有到使我们过分惊慌的程度,尤其在目前,国家更紧急的问题和人民更切身的痛苦很多的时候,更不宜不顾一切的,而且不择手段的,要硬把土地拿来全体重新分配过。我们又一看英国的情形,更可以相信,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并不一定就是工业化的大障碍,也不一定就是国家贫弱混乱的重要因素,因为英国的土地分配比中国欠平均得多,而英国却是一个很富强,很民生,工商业很进步的国家。”(《土地分配问题》,1948年)
至于农民的贫穷,董时进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事绵亘。租佃对地主和农民而言,是一种共赢的经济模式:
“农民贫穷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是战事绵亘,治安不好,捐税繁重,以及各种灾害等,而人稠地窄,产业不兴,也是根本的原因。至于地租,不过是一种寻常的经济行为,对于租佃双方都是有利盈的。租地耕种的人家,生活得到解决及逐渐起家的很多,因为租种他人的土地,越租越穷的很少。”(《土地分配问题》,1948年)
董时进还认为,耕地过分零碎将妨碍经营,地权不稳定将造成田地肥力下降。他说道:
“中国的耕地,本已过分割过分零碎,于经营上颇多妨碍,再要人人平均细分,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减少农业生产。”
“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都在那里转念头了:现在我的地,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那么,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是一点,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堤岸田埂崩垮也罢,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补?田地随它瘦下去,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残余。董时进强调,中国土地制度是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的私有制度,与传统封建国家中代际传袭和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不同,故此并不是封建性的。他在1949年的上书中写道: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
“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至于地主富农,董时进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乃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土地不过生产工具之一种,买地不过储蓄方法之一种,地主出租土地获得收益,跟存款或出租房屋是一个道理,拥有土地并不是一种恶:
“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许多人硬说,土地是地主用来剥削农民的武器,形容得非常可伯。也不过是生产工具之一种,买地不过是储蓄方法之一。有一些人拿着这生产工具,不能或不愿自行利用,因而转借与别人利用,收一笔对方所同意的租借费,这就是地租。……地主将他的土地出租,和城市里面租出货栈,店房,厂房,机器,车辆,船舶,耕牛骡马等意义,并无分别,而租费用或更低廉。在承租人拿去生产题营,可以得到收益,也是与在城市租房屋车辆等一样。”(董时进《土地分配问题》)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他认为,瓜分他人的合法资产,让贫民不劳而获,会使“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退出民盟与赴美
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民盟政纲。董时进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为表达自己的上述主张,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在成立宣言中,董时进将该党的核心任务定义为“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
“我们组织本党的动机,曾经在本党的缘起上详细陈述,大意即是说: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本党虽是代表社会上一行职业的政党,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一切主张,必须顾到国家全民的利益,我们的主要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这都是整个国家所切需的。至于本党的党员当然最大部份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但是我们也欢迎一切同情者参加。农民党是要农民都能当国家的主人,却并非要他们都去做官。”
董时进认为,民国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是来自政府的政治剥削:
“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因此,我们认定,改善农村经济的办法,应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纪,使乡间所生产的财货不再被非法剥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
故农民党有意在保护农民私产方面致力:
“本党真诚的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使他们期待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喜,隔夜发横财,因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农民能收得自己辛劳的结果,不被他人掠夺,并能藉自己的勤俭与经营逐渐改善其境遇。”
“八年抗战下来的国家,浩劫余生的人民,牺牲惨重,痛苦万状,内战再打下去,非至同归于尽不止。我们要求一切军队都无条件的向全国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将他们的枪炮一齐放下来,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我们认为内战的根本解决,不仅是目前不打的问题,而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
乡村教育,被认为是农民党可以选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过去中国不是没有建设与教育的成绩,然而建设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品。结果是建设反加重人民的负担,都市愈发达,乡村愈残破,教育造成了社会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众,剥削农民者愈多。本党必须力挽其弊,特别注重乡村生产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知识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一个平衡健全的国家。”
农民党成立后,主张“为农民谋利益,不一定要损害地主,更犯不着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亦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3编 政治》,中国农民党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949年1月,国共和谈,农民党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同年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6月5日,李维汉约见董时进,劝其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 6月25日,农民党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哪些政治派别和团体未能参加新政协会议》,慕安,人民网》
1950年,董时进赴港。1957年赴美。198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