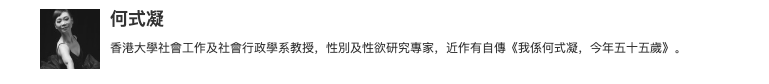我和反送中运动的一场爱情
作者:何式凝

练乙铮 x 梁继平
前一阵有幸能和「唯一得到陈祖为 A+」的梁继平对话,感谢立场新闻邀请,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被定性为一个「甲级战犯」,本来就是不能再次在公众场合说话,不应该再站出来,不应该如常生活的一个人,还想在观塘游行的那一天入观塘?我犹豫了十秒, 还是报了名,我真的很想亲口告诉梁继平,除了立法会的宣言,他在816 遮打「英美港闻主权在民」集会的视频发言的确是近日其中一个最能安慰我的声音,在我躲起来不敢出外的日子,他的声音就像黑暗中的一线阳光,照进了我阴暗的房间。
他说:「所谓的共同体,就是能想像他人痛苦,并且甘愿彼此分担的群体。」他还说:「只有当我们将他人所受的痛苦,视之为自己的痛苦;他人所作的牺牲,视之为自己所作的牺牲,并且将每一场的抗争,都看作是对前人所付出的肯定和追认,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够成立。」
透过视频,我跟他说:「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么动听的话,没想到还有人会说这么温柔的话。」我问他:「我很想听你再说,你口中的的共同体其实是怎样的,这个香港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
他说:「是我们共同的绝望和悲愤,无论是勇武还是和理非,我们的底层是这种共同的感受,这种despair 把我们连在一起。」
我说:「明白,非常 queer theory!」他也笑了。似乎,他也明白我的学术取向。
Queer Theory:个人是什么?
Queer theory 不就是说我们要超越 identity politics 吗?身分政治很多时带来的是不同身份不同派别的对立,而我们性小众的团结唯有基于我们共同被打压的经历和记忆,不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立场和利益。我所理解梁继平的政治理念,是某一种意义的「大爱同盟」,所以我句句听得入心。
我再问他对于我这一条女被网民定性为「甲级战犯」,他有什么看法?这件事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能从当中看到运动正在经历什么转变吗?
他说对于个人的创伤和当中的恩怨情仇,不便评论,然后就解释他对这个政局的分析。
我心里当然很不舒服,于是我再追问:「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这一件事不是也反映了由雨伞运动左右之争遗留下来未完全化解的矛盾吗?这些事情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不过,也可能是我这个人所代表的一切,例如我撑黄心颖、我在高教界的位置和对大学的批评,在此刻是为世所不能容。这个社会已没有空间让我这样的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表达我的意见。」
我实在难以自制,一轮咀的 Chur 下去。他也表示明白我的说法,不过,他认为雨伞运动中的公民社会的分裂在这次运动中神奇地得到一些和解。如果雨伞运动是一个 thesis, 鱼蛋革命就是一个 antithesis, 反送中就是一个 synthesis! 他这个人真的很浪漫。
我一再解释为什么我要这么Chur, 因为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看个人和这个共同体的关系,这也是他用的framework 中重要的一环! 既然他一直说要把他人所作的牺牲看成为自己牺牲,他是怎样看待有人被老屈、被欺凌、被批斗,而高等教育界和性别组织都没有人伸出援手,他是怎样看待这种沉沦?这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我当时的确有点 emotional。看见梁继平还是愿意听下去,我就不理大家如何,即使很多人想转换话题去讲国泰事件怎可成为国际议题,我还是要问,那么我们相信的其实是什么,我说:「是否如当场练乙铮所言,和理非已经成为了一个手段,不再是大家珍而重之的价值?」
甲级战犯左与右
由始至终,梁继平始终希望能说服我要多一点理解勇武派曾经受过的打压,而这些未有完全化解的仇恨是基于过去受过的屈辱。末了,他还给我一个这样提议:
「你还记得2014年11月有一群黑衣人想冲入立法会,结果他们被大家排斥,被大家割席,他们回家之后,也跟你现在一样,欲哭无泪,觉得自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如果你能够把这两种感觉连接起来,可能你会得到大家更多的谅解,或者也会对化解你现在心底的怨恨有一点帮助。 」
我马上笑了。不算什么 comic relief, 但我和他都笑了。不苟言笑的他,语气是带点幽默却没有很多讽刺说出这个建议,像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没有贬意),所以我也笑得出。如果他的语气是这意思:「你们这些死左胶,当年咁样对人,你都有今日了!」我肯定会反台。我不觉得他想讽刺我,当时我清楚感觉到他是想我明白今天我承受的苦,可能是为了让我这种人更明白曾经受了委屈被运动排斥于外的勇武抗争者的感受。他好心相信:如果我能够更理解黑衣人当时的状态以及这些经验留给他们的伤痕,可能我就能够稍稍释怀。
他还说:「如果你写了这篇文,我应承你一定会share!」
他相信在反送中运动,勇武派与和理非在某一程度上是已经能够达到一种和解,这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大家要为这次运动的成就而骄傲,不能对运动失去信心,要看到这个运动美好的一面。作为一个一往情深的抗争者,其实我怎会不明白他的心意。我再一次看见八月五日之前的自己,只不过,来到八月尾,我不能不追问:这一种和解是怎样产生的?这种他见到的 synthesis 是要靠压抑多少声音多少异见,要有多少不同类型的牺牲才能有的一个局面?大家要把多少罪恶看为是战争、非常时期的寻常,才可以对运动里的丑恶视而不见?
照顾受伤的同伴
现场参与讨论的人,有些一言不发走了,令人有点难受。我并不是说大家如果没有留意到天水围事件,不明白当中的所有因由,就必定要发表什么支持何式凝的言论。我觉得很难受的是,一位女性抗争者,多年来一向一往情深的抗争者,站在你面前,where 烂哂块面,说到她怎样由保护者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大家竟然没有一句安慰她的说话?他们不单没有礼貌,亦没有表态,更没有尽一种基本责任 – 我们作为一个抗争者,关怀受伤同伴的基本责任!
梁继平说得对,「我们决定踏上抗争路的时候,就注定被这个城市放逐、唾弃。每位抗争者都承受着家人的不谅解、朋友的疏离、建制支持者的指骂… 。 」那么,被同路人老屈和批斗,被自己人报警叫人拉你去坐监,被好朋友一而再叫你去自首,认为这才足够赎罪,又是什么一回事?
在他的 framework 中,这些事情是否毫不重要?在社会运动中,这些伤害是否只能被看成不那么重要?见到有位少女被警察抬走时露出了底裤, 我们跑了去天水围警署声援。六日之前,我们在葵涌警署门外,声援杨政贤和中上环被捕者;元朗黑夜翌日,我们也去了元朗警署,要求见 Madam, 。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可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对运动还是有意义的吗?如这不是勇武,这是什么?
等到和平之后
今天我能面对一个为了香港人而冲入立法会,可能要流亡海外的年轻学者,绝对是应该更谦卑的学习,不能对运动失去信心,我真心尊重眼前的这个人,感谢他的付出,明白他的牺牲也是为了我,但我不能不提出我的质疑,不能不表达我的看法。
梁继平说:他决定冲入立法会的一刻,就是他的「 moment of truth」(体现真理的一刻),是他要体现自己所相信的理念的一刻, 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抗争者都可以有自己的moments of truths, 可以是捐钱、绝食,可以是各种各样站出来的行动,试问有谁可以判断哪一个行动才是真正的革命,哪一些永远只能是辅助服务,哪一些是鸠做,哪一些人是阻碍着别人真正的革命?这些等级、定位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要把判断交给了连登、所谓的勇武派或其他抗争者?
梁继平从来没有说反对我的说话,都是耐心聆听,并说:「雨伞运动之后的检讨不多,这次运动之后大家一定要好好反省和检讨!」
他不说还可以,他一说到这点,我比先前任何一刻都更emotional! 我问他:「这个运动什么时候会完结?会有完结的一天吗?为什么要等运动完结才反省?我们此刻不说,以后还会说吗?」
我们参与任何运动,不是都应该时刻反省吗?我们常常都抑压着真心想说的话, 我们说什么话都要考虑到连登的「主流意见」,大家都这么恐惧,这对运动是一件好事吗?
再回到练乙铮的说法,他说性格培养、心理结构的 robustness, 对这个运动很重要。说得对,但这种性格的培养,是怎样成就出来的?是一个人的修练就可以吗?还是我们可以透过互相守护,在爱情中、在友情中、在运动中都 speak the truth, 并保护大家表达的自由,才能成就出培养这种性格robustness的环境和文化?
席间有人提出运动要有新的 agenda setting, 但谁敢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其实也需要修订?还是西瓜归大边好了!大家每晚对着窗大叫,当然只能叫可以说得出、会有人够胆回应的说话。那些不能说的、等待爆发的,又可以向谁说?
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些事的反应,都反映了自己内心的黑暗,人生中遭遇过的创伤,包括运动的创伤,但我们经历到的绝望和创伤并不是用来合理化各种丑陋的籍口。
Queering 勇武
我这样的死左胶女权捻,凭什么敢跟梁继平或任何人说,其实我的牺牲也是为了他们,是为了让运动中人对性别议题有多一点认识,大家能对别人的痛苦有多一点想像。
我常常记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后来自杀过身的林奕含,她在自己的婚礼上说结婚是做个新人,其实就是要成为新造的人,就是一个对别人的痛苦有更多想像、可以帮助精神病人去污名化的人。她和卢凯彤一样,希望公众更多理解别人的痛苦,她们的故事让我不能不打开一扇窗,尝试了解一些我一直没有能力想像的痛苦,学习尊重别人的选择, 这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一环。
我很高兴能认识梁继平,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人,他鼓励我去明白勇武派的痛苦。我很骄傲港大能有这样一位A+ 的毕业生。如果有机会,也希望立场新闻能让我们可以与中文大学的同学,进行另一场对话,这位蒙脸的同学是这样跟校长段崇智说的:
「看来全副武装,好像很劲很勇武。但其实,勇武不是在装备上体现出来,这身装备体现出来的是恐惧,防毒面具是对致命武力的恐惧,黑衣蒙面是对白色恐怖的恐惧。」
这位中大同学认为勇武是这样:
「若没有人敢做,而你做了,这就是勇。勇是对恐惧的克服,武是外在的行动。对我而言,武不是狭义的武力,而是广义的行动。勇武就是克服自己的恐惧,付诸行动。」
他和梁继平,无疑是勇武。但他觉得还有很多人也是勇武。
「我认为行得上街的人,都是勇武派,郑国汉校长是一个勇武派。」(八大校长中亦只有郑校长愿意现身元朗游行)
「勇武这回事,不是政治立场的表现,不是一种武力的象征,而是爱的体现。」
我和梁继平可能都不够蒙面同学queer, 这位中大同学可以颠覆大家对一个人勇武派年青抗争者的看法,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没有假装成无畏无惧,然后他敢在强权面前,在一个公共空间发表一些和传统勇武不同的概念,让我们同时看见平凡抗争者的贡献,又把窝囊的校长都拉进来,希望众位校长和不同光谱的香港人可以重新得力,或许能够为这个运动注入新的能量。这位中大同学re-present了郑校长和段校长,让我们看到一些被抑压的真实,颠覆我们对这些人的了解和想像, 叫我们不能抹杀其他人的贡献, 包括被大家歧视的人, 他真系queer 到爆!
Queer theory 对identity 的看法正是这样,每一个身份,包括勇武派,都不是一个自有永有、完整无缺、可以一成不变的实体;它比我们想像中更具有流动性, 有时像water,可惜很多时都很胶。这个身份和其他身份其实不是对立, 是互相成就的,和理非和勇武一直在互相监控着对方,互相说明对方是什么和可以怎样,可惜这个说法并没有受到真正重视。
勇武是什么,梁继平可以去界定,蒙面同学可以有他的界定,每一位抗争者都可以有他们的界定。这个概念和所有概念都要受到挑战,才不会那么快「胶化」。
作为「甲级战犯」,我说这些话,内心也没有太多恐惧,我只能 keep calm and dance on, 这是每一个受伤而死唔去的女性抗争者还可以做的事情。恶毒的说话都听得不少了,心都伤过了,警察未来拉我之前,我不能只被恐惧支配,要好好过活,利用我新的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要为这个运动每天披头散发,当我被迫离开了那些最容易被侵犯的第一线,我才可以回顾我和反送中运动这一段爱情,想想自己是否痴心错付,我还要不要一往情深。不过,好朋友竟然说:「我认识的何式凝是不会对爱完全心死,只是会换另一个模式去爱。」我是香港人,无论我身在何方, 我所思所想都是要维护香港人的尊严和自由,我被迫离开了这场运动,却永远是这运动的一部份,不过,现在我要做的不再是每天疯狂的跟着每一场抗议和示威活动,不再是每天都在想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做、没有人去做就自己去做,我可能要找另外的一个位置,另一种爱的方式,去我要去的地方,做我还可以做的事情。
天水围事件,是我的人生和抗争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再次感谢立场新闻和杨天帅的邀请,他们没有加入孤立我的行列,让我可以说出心里的话,在这场对话中得到一点治疗和启示。感谢当晚留下来给我亲切关怀的立场bloggers,让我重新感到人间有情。
相关阅读:
【网络民议】“香港加油!有良知的大陆人和你们站在一起!”
罗世宏:想活趁现在──为正在反抗绝望的香港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