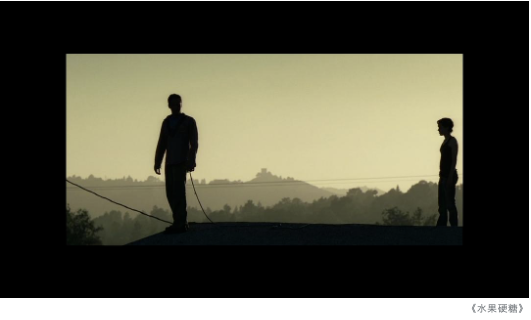作者:詹青云 来源: 看理想
鲍毓明案公布了调查结果,但讨论并未平息。
根据通告内容,“鲍某某明知其本人和韩某某的情况都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收养和被收养条件,且在自认为韩某某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以‘收养’为名与韩某某交往且与其发生性关系。”
“鲍某某当时是并不知道韩某某的真实年龄,但是他对法律的嘲弄是真实的,法律的漏洞是真实的,他基于自己的法律知识,设计的环节是真实的,教科书一样想钻法律空子是真实的。而且几乎得逞是真实的,QQ群上的送养产业链是真实存在的”,水木丁在《鲍毓明案结果出来,我没有后悔发声》一文里写道。
不要轻易就以“反转”的说辞去嘲笑讥讽当初为此发声的人,恰恰是因为发声和讨论,才让问题有了更多曝光和得以被推动解决的可能。
在这几个月内,许多女性站出来勇敢指出了那些在童年时经受、尤其是来自于熟人的性侵案,社会中隐秘的“恋童癖”现象被提及和指出,“血赚不亏”这样带
有调侃性侵的弹幕和评论,也被自发抵制。
现实生活也并不是像悬疑剧那样有一个确定的大结局,还有很多挣扎在灰色产业链之中的“星星”们,“鲍毓明”现象也依然并未杜绝。
正如詹青云所说:请看见并记住它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永远保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在法律的层面上,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为什么要去讨论“标准”为何?为什么强奸案界定中的有那么多不确定性?为什么为何现今的法律在强奸案中难以做到绝对的正义?
01.
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
在强奸案的判决中,年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如果这个女孩在14岁以下,那整个的论证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只要有性行为发生了,它就已经构成强奸罪”。
还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具体的法律规则,比如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如果女方有精神性的疾病,有智力的缺陷,被认定为是不可能表达出自己在性问题上的自由意志的,那也可以直接认定“只要有性行为发生,也是违背对方意志的性行为”。
在有些比较“激进”的地方,比如麻省(马萨诸塞州),它规定“不管你的脑海中真实相信的是什么?只要你犯了错,只要这是违背对方的意志所发生的性行为,那它就是强奸”。
在这些被切割出去的具体情况严格责任之外,在大部分的领域里,我们面对的是大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法律体系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我们国家法律的措辞里,它可能表现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种不确定性有它的价值,也带来它的困难。
在强奸罪的定性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对行为判断的不确定性,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所谓暴力?受害的这一方什么样的行为能够称其为反抗?小声的沉默可不可以?小声地说“不”可不可以?大声地说“不”,持续不停地说“不”可不可以?还是一定要动手才可以?
叠加在对行为判断的不确定之上的,是当事的双方对于这个行为的判断,在很多的例子里,两性之间的沟通总是存在思维模式的差异。
如果是一个男性强奸一个女性,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个男性觉得“他没有使用暴力,他们只是‘正常’的一个性行为”。
本来在性行为当中男性是占主导地位,且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这被他认为是这个“正常”的性行为的一部分,甚至是使他更刺激的一种方式,可是女性已经感受到了,她在暴力的强迫之下。行为可能是明确的,可是双方对于这个行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那更多的例子里,对于“什么叫做反抗认知?”这个女性可能觉得她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可是另一方觉得他没有接收到这种反抗,就还认为对方是同意的,这不就是一个合理的错误吗。但这个错误真的“合理”吗?
这就是不确定性叠加着不确定性,它有双方对于这个行为的理解的不确定性,法律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和判断当事双方的行为和这个行为的性质?
但在现实一个案子的侦办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和问题,还不是在判断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而是事实本身就不清楚。
当然,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法律规则本身的问题,看上去是可以明确讨论的。
比如我们的《刑法》里是不是该引入“婚内强奸”在定义强奸罪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女性对男性的强奸?同性之间的强奸?先把这些法律可能还没有追上时代变化的、明确的问题先弥补上。
还有一些问题的讨论答案是更加模糊的。比如要不要接受“人可以犯‘合理’的错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的任何一边都有相应的利弊。
如果一个人可以犯“合理”的错误,他可以错误地认为“对方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它本身不确定性的辩护,可能成为很多人脱罪的理由。可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个人可以犯“合理”的错误,也可能很多人他们罪不至此,却要一辈子背负上强奸犯这样的恶名。
又比如,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衡量“反抗”的标准?是不是应该画出一条清晰的“界”?只要一个女性说“NO、不”的时候,对方就必须得停下来;或者是更激进一点,她必须得先同意这件事情才能开始。
又或者是我们依然坚持沿用现在的这种操作方法,把指导性的因素、可以考虑的因素列举出来,但是“具体的每一个案子怎么去判断?”交给每一个法官去做。
这两种操作手法也都有它的利弊。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能在定罪的时候会更容易,原告的论证责任更清晰,有更强的威慑力,不会让施暴的这一方抱有侥幸的心理。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明确的标准到底应该以什么为标准?
这种标准是不是真的适应于当下多元的文化、不同人的不同的相处模式?当标准和文化本身相冲突,它带来的是不是实践当中的无法操作和混乱?
保留法官自主裁量的权力,是不是给予法官真正保护那些弱势的机会?那些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人,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是不是给了一个法官去考虑他们的苦衷的机会?
这些不同的标准,大家可以讨论,可能不一定有最好的答案,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
02.
对未成年的保护,为什么要一刀切?
根据我们国家的《刑法》:如果和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违背幼女的意志,都构成强奸罪;而所有14岁以上的妇女在强奸罪的定罪标准上是被一视同仁的,除了两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也有很多学者的比较对象是美国。在“性”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国家,但是美国的性同意年龄也比中国高。
美国的《刑法》是以州主导的法律,所以它的法律协会推出《模范刑法典》,但是实际上发挥作用的都是每一个州自己的规定。绝大部分州的同意年龄是16岁,但是这个年龄也分很多种其他情况讨论,没有那么“一刀切”。
比如说美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法”。这条法律对应的是一些未成年人,他们虽然是在16岁以前发生了性关系,可是他们是和自己的同龄人,在恋爱关系中发生了性行为。
当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不超过3岁(有的州4岁、5岁,因州而异)法律便把这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这种情况下,性同意的年龄可以适当降低,一般来说大部分州会把年龄降到13岁。
如果一个15岁的少女跟一个40岁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在这个法律之下,男方就是法定强奸,受限于严格责任。
这背后的逻辑也非常简单,当一个未成年人和一个成年人相遇,他们在智识、社会经济地位、过往经验上,有种种不对等的情况下,这是对年龄小的一方的一种保护;而当双方的年龄比较接近的时候,这种不对等也就不存在了。这是适当降低性同意年龄的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会升高性同意的年龄,这几乎在所有州都有类似的规定。当性侵案的被告利用双方特殊的关系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性同意年龄会被提高。
有的州的法律会把特殊关系列举出来,包括家人关系、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还有师生关系;有的州会比较笼统地说,当他们之间存在依附关系,一方滥用这种关系去与年龄小的那一方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性同意年龄就会被提高,通常会被提高到18岁或更高。
这背后的逻辑也很明显:在特殊的依附关系当中,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当双方的年龄和社会地位差距过大,这种自愿可能是诱骗的结果,表面上看是自愿,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自愿。
为何会有这样一个“一刀切”的标准呢?就14岁以下幼女的情况而言,不问她是否表达过意愿,也不问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知不知道她的年龄,一律以强奸罪论处,这是法律中一个特殊的责任划定的类型。
这是背后有一个更加普适的原则,叫做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有的地方还有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
刑法里面有两种最典型的严格责任,一种是重罪谋杀(felony murder doctrine),另一种是法定强奸(statutory rape)。
检察机关要决定用什么样的罪名去起诉一个人,就必须要证明构成这个犯罪的要件。这些要件可以笼统地分成两个核心的部分,一个是行为,一个是当时的意图。
我们都知道在刑法犯罪当中,定罪的最大困难常常是去衡量:这个罪犯做出这个行为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而在严格责任这一标准之下,这就不重要了。
和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违背该幼女的意志,都构成强奸罪,这个就是法定强奸。它只看行为,你的行为是跟一个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了性关系,它不问在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你的意愿,即是否有意要去犯罪。
这就是为什么“14岁”这个概念如此重要,它的定罪标准和14岁以上的,通常意义上的强奸案的定罪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14岁”标准背后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保护。
这个社会认为针对未成年人所发生的强奸案,它是极其恶劣的,会对社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用严格责任这一标准降低它的起诉门槛,让这种罪行更容易被证明和成立。
03.
强奸案为什么定罪困难?
法定强奸的概念背后的另一个核心逻辑,还在于强奸案的取证是困难的,是难以被证明的,难以被定罪的。
以我们国家的《刑法》为例,当“是否违背意志”这个问题不清楚,双方各执一词,受害一方的心理状态不明确的时候,法律要做一个综合考虑:包括两人之间的关系,交往的历史,性侵行为的发生时间、地点,当时的状况,包括当事双方在事后的反应,特别是第一时间的反应。
在许多性侵案件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综合考虑的复杂性,因为这不是一个单次性侵事件,这些性侵事件发生在一段连续的时间里,甚至是一段连续的关系之中。
从法律层面上看,我们很难退回每一个时间节点去确定当时的各种因素,而我们除了对具体的事件做判断,还得对他们的关系做判断,而这个对关系的判断,也会反过来影响大家对每一个事件的判断。
关系所带来的模糊,给整个事件的判断叠加了新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糟糕的问题是,作为这种连续的性侵的受害者,她们所受到的伤害绝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还有自由意志的摧残。
在受到了这么多年的伤害后,会伴随着严重的抑郁症和创伤性后遗症,所以她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很难稳定地和别人合作。作为受害者,受害的后果却会反过来影响她作为一个证人的能力,这本身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很现实地说,在现在的医疗手段之下,只要报案比较及时,要证明有性交发生,这个是容易做到的。可是要证明在性交的过程当中,伴随着其它形式的暴力,有的时候这种暴力是可能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在人的身体上留下了明显的伤痕,或者有比较清晰的证据的记录,有人证、有录像带或者有证词。
但是也有很多的情况,这些什么样的力、到什么程度的力,构成“暴力”?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明确。有很多一定程度的“暴力”,是足以使受害的这一方放弃或者没有能力反抗的暴力,它可能并不会留下清晰的证据;也有很多时候这种“暴力”是隐性的,它是威胁、它是精神上的恐吓或者精神上的控制,它是在漫长的共同相处当中,所形成的一种威慑力。
这些东西更难以用证据证明,所以不同的论证责任,它就会提供不同的报案的门槛,或者论证为一个罪名的门槛。
如果一个法律体系之下,它要求有性交行为以外的额外暴力,那么它通常是要求受害的这一方证明自己“有过反抗”,这就是一个额外的论证责任。她/他要证明“我反抗过”。
反抗在有的地方是一个“一刀切”的标准——如果你没有反抗,那么法律就默认你是同意的;有的地方则认同说,你有的时候不反抗,并不是因为不想反抗,而是因为没有能力反抗。
今天有很多的女性站出来,揭露她们人生中遭遇性骚扰、性侵犯的经历,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她们很难在法律层面上证明性侵的存在,她们所依赖的是他人、社会大众,对她们的信任和善意而已。
04.
标准是否真的理性?
可是也有大量类似的案子,在过往的法律之下,因为它要求额外的“暴力”元素,而没有办法被定性为强奸。它的隐含的意义是在绝大部分的强奸案当中,女性受害者需要反抗。
所以有很多人批评这种法律概念这是在要求一个女人在被侵犯时还要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反抗,才能自证清白。
从这一点出发,有很多法律理论家深刻地指出:这种两性文化,或者是传统的性别观念传统,它对法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深埋在大家的潜意识之中的。
明面上,法律可以随着时代相对容易地改变,但真正难以实现的改变是大家脑海深处的对性暴力事件的固有印象。
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律文化里,真正缺失的是从女性的视角去看待性关系。
在现有的社会认知里,我们都认为在性关系当中男性有一定的攻击性,男性占有主导地位,女性适当地反抗其实是一种顺从。
所有的这些概念都深埋在我们的文化里,它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影响法官的判断、陪审团的判断、律师的判断,甚至影响受害人自己。
这种意识形态才是最难纠正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法律文化是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去理解一个女性在被侵犯的情况之下,她所感受到的恐惧。
当她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陷入无法思考、无法反抗的状态时,法律如何保护她们的权利?
法律认同“如果这个时候受害人因为感到恐惧而没有办法反抗,那只要证明这种恐惧是合理的”就可以了,这是法律当中通行的所谓“理性人”的标准。
问题就在于这里的“理性人”是理性的男人,还是理性的女人呢?
如果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法律都是理性男人的视角,大部分的法律工作者都是男人,大部分的警察和检察官也都是男性,他们以男性的视角出发所衡量的“理性人”的标准,又是不是一个女人身处那样的状态之下的“理性人”的标准?
我们在这个时候应不应该把个人的过往经历、性格特征,也都纳入到理性的衡量的范畴里呢?这才是更现实的问题。
05.
女权主义对强奸案件的改变
关于什么行为构成强奸、强奸应该被视作何等程度的罪行、强奸犯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是深受罪行背后的社会文化,还有很多意识形态所影响的。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我们开始重新看待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去看待所谓的性自由、性同意,去看待受害者,一个女人(或男人)对于自己身体的完整性的控制,对自己身体不受侵犯的自由的坚持。
女权主义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法律。比如还在不久之前,婚内强奸是不被认为是强奸的。婚内强奸变成一个罪行,就是被这些兴起的权利的概念所支撑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强奸”中的“强”字指的是“性插入”这个行为以外的暴力。
比如把这个人压制住,让她/他无法反抗;比如用暴力伤害她/他,让她/他不敢反抗;或者是让她/他陷入昏迷,失去反抗的能力等。
在裁定“一个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的时候,法官要去寻找在性行为本身以外,被告方还使用了额外的暴力。而女权运动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推动了“暴力”这个理念的改变。
在过去二三十年之间,越来越多的法律和判例认定“性插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传统的强奸案谴责的是“在发生性行为的过程当中,额外对受害的一方所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现代的法律理念里,会认为它首要的伤害是“违背对方的意志,而强迫她/他进行性行为”这件事情本身。
这件事情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人格尊严意义上的。
一个人身体的完整性受到了伤害,这就足以构成暴力了。
这个界定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不止体现在“它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权利理念,它的背后是一种我作为‘人’的完整性,我的尊严不受任何侵犯和践踏的理念”,它也体现在法庭上要用什么样的证据去证明有“暴力”。
尾声.
鲍毓明案的背后,有一个一直让我们在道义上感到困扰的难题:任何法律体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套规则,那会不会存在有聪明的人去利用这套规则为自己谋利呢?
本质上来说,在法律规则之外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被惩罚的。
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简单地改变法律规则本身就可以解决。这些天然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一味地降低论证的门槛,降低论证责任就可以改变的。因为一味降低,带来的一定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平。
在这些不确定性的面前,法律体系必须要做出某一种选择,这是法律所要求的确定性。
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在不同的规则上去权衡不同选择的利弊,也可以在倾向性上考虑时代的特点。例如大部分情况下,是谁在利用规则?是谁长期地被这个规则所束缚,而没有办法伸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一个社会整体作出的选择,落在每一个个体的头上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法律只能尽其所能找到那个最好的,充分保护各方权利的平衡。
在一个案子里,我们可能注定只能接受某一个结果,但请看见并记住它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永远保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