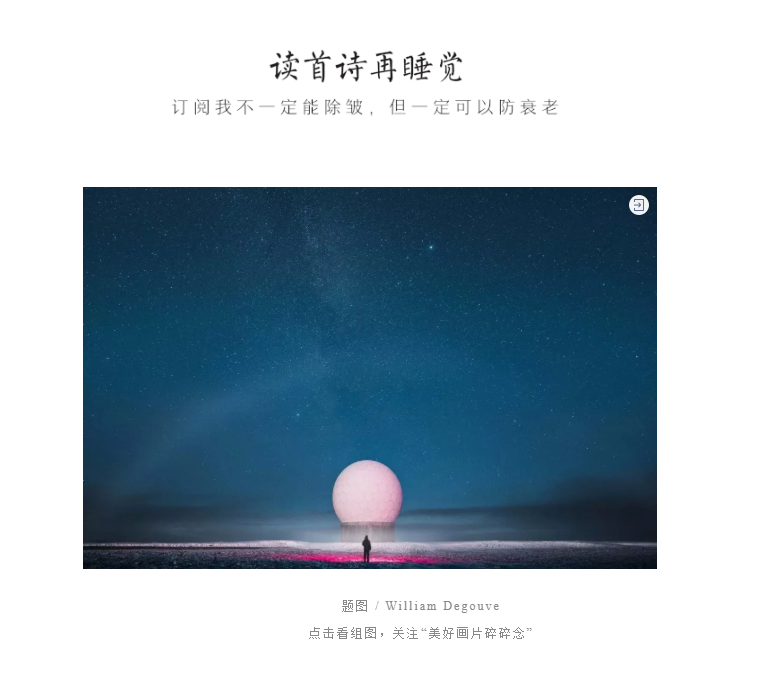谈海
谈到海
我好像想起点什么
是可可西里的那片海吗?
好像是好像又不是
它离我是那么的遥远
我倒开始为骆驼悲伤了
羊群我也开始可怜起来
他们的世界除了风沙和草原
再也没有什么念头
每每听到一点不同的风声
就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
那般的好奇
那般的无知
现在只要骆驼轻轻地
走进沙漠
那么每一粒沙都会变成水滴
草原上的每一堆羊群就会变成帆船
从此我也就见到海的模样
自然花也就开了
从此我不必再提起可可西里
也不必再想起亚丁湾的深蓝
我会把他们的旧名字统统烧毁
然后重新给他们取个新名字
管沙子叫作水滴
羊群叫作帆船
沙漠叫作大海
草原叫作港口
冬天无风夏季无雨
它是一片特别的海洋
2019.8.24
作者 / 燕子
这是一首自觉之诗,就是标志着一个人进入真正的“诗人”状态的诗。每个真正能被称为“诗人”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作品,ta了解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以及能力。这种状态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始给事物“重新命名”。
比如最开始的海,还是真实的海,但诗结尾的海,就成为了诗人创造出来的一片海,而她创造海的方式,就是“重新命名”,运用想象(不管是神启还是开天眼什么的)把沙漠改造成大海,羊群改造成帆船,还蛮有气魄的。
而且这片海“冬天无风夏天无雨”,还是一个蛮有寄托,让人感到安稳的地方。
但唯一有个突兀的地方是,“从此我也就见到海的模样 / 自然花也就开了。”
上下文里不是沙漠草原就是海,为什么突然提到花呢?
大概因为作者的本名:吴花燕。
没错,就是最近两日舆论中心的“吴花燕”,一个身在贵州,“被贫穷逼迫而死的当代女大学生”。屡屡与她的故事相对照的,是管理她所在省份的官员,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往下水道里倾倒茅台酒销赃,还没有倒完。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诗在一千多年后依然是现实,甚至更加恶劣。但选择这首诗,并不完全是因为这样令人惊愕的故事。汹涌的热议,往往会凸显一个人的标签,而遮蔽了这个人其他也许更珍贵的侧面。
吴花燕的一位朋友把她的朋友圈和部分作品截屏,那里面可以看出她最真实的生活与想法。她的朋友圈里经常会转发诗歌,以及发表自己的作品,就像许多文艺青年一样。比如2019年,她就在朋友圈里转发了15首诗,里面有聂鲁达、卡瓦菲斯、奥克塔维奥·帕斯、佩索阿、玛丽安·摩尔……
今天推荐的这首诗,就发表在她8月24日的朋友圈里。她吃过非同一般的苦,但在她的诗里却没有苦的味道,诗里写到了“悲伤”、“可怜”,但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骆驼和羊群。所以这也不是一首小女生简单的哀怨之诗,“把旧名字烧毁”,“把沙子变成水滴,羊群变成帆船”,简直有神奇女侠的味道了。她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蛮富有的,并不需要别人的可怜。
可惜的是,在跨过“诗人”之门的4个多月后,2020年1月13日,她便因长久贫困引发的疾病,殁于人世。
最后,
我将回到云贵高原
在贵州最高的屋脊
种上一片深蓝色的海洋
在那里
会有一艘丰衣足食的小船
带我驶向远方
《远方》吴花燕
媒体的报道里,经常会提到她另一首比较直白的诗,写于2019年9月18日,同样有着对海洋的向往。在她一生的故事里,“丰衣足食”四个字甚为扎眼,是个愿望,但这愿望对我们其他所有人,简直像个讽刺。
作为写作的同侪,推荐这首诗,是希望今后人们想起吴花燕来,不止记得她是一个被盛世遗漏,被贫病击倒的人,也能记得她有过富有的灵魂,创作过优秀的诗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荐诗 / 照朗
诗人、译者
著有诗集《野游》、《一居室》
译有《玛吉阿米容颜:仓央嘉措清歌》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