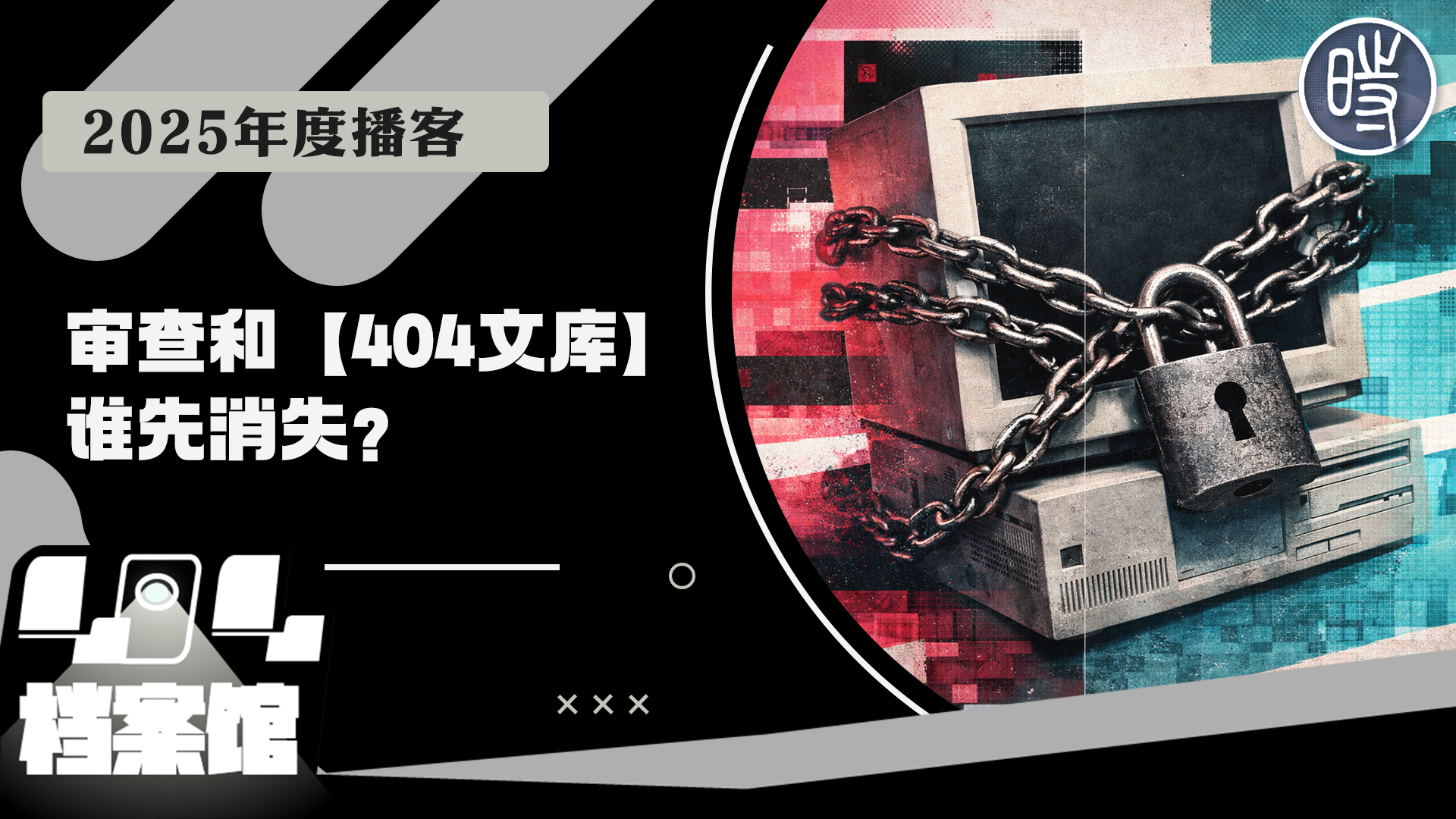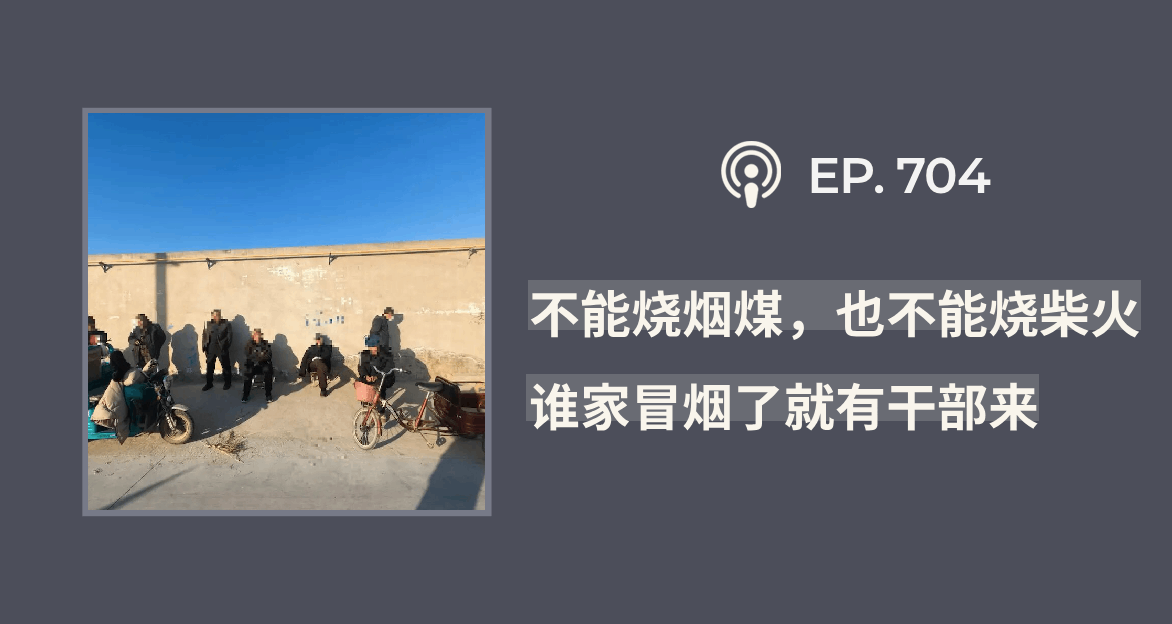http://book.ifeng.com/dushuhui/special/salon041/
凤凰网读书会 No. 41
闾丘露薇VS胡泳、金玉米
拒绝“偏见”报道
本期凤凰网读书会于2011年1月15日在单向街举办,邀请到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闾丘露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及来自南非的金玉米。闾丘露薇的新书《不分东西》完全是站在一个媒体从业者角度看待和思考中外媒体存在的“偏见”问题。近两年,中国的国际角色日益凸显,此次我们希望通过借闾丘的新书,从中外从业者、研究者的视角来看看偏见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避免。
欢迎来到凤凰网读书!2011年1月15日,第四十一期读书会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邀请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闾丘露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和单位网站创办人,来自南非的金玉米一起聊聊“拒绝‘偏见’报道”。
本次活动我们在凤凰网读书会官方微博(http://t.ifeng.com/ifengdushuhui)及凤凰网读书会微博小组(http://t.ifeng.com/g/1453/)进行了预告和提前交流,欢迎加入和关注。
编者按:
本期凤凰网读书会邀请的嘉宾是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闾丘露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还有单位网站创办人,来自南非的金玉米。
闾丘露薇出的新书叫《不分东西》,风格与此前出的两本带有自传色彩的书完全不同,这本书完全是站在一个媒体从业者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中外媒体存在的“偏见”问
题对于很多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或是媒体人,这应该是最佳读本,从而摆脱那些陈旧和过时的理论。该书深入浅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它能够开始提醒我们在面对铺天盖地的时事新闻的时候,是否能够有比较独立的辨别能力去把碎片信息里的有效内容吸收,把糟粕去除。在近两年,中国的国际角色越来越凸显,国外的媒体也加强了中国方面的报道,关注到普利策新闻奖,就会发现,获奖的报道开始涉及到中国经济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国外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没有停歇过,
有时候,他们或许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了“偏见”。
我们中国媒体的报道又何尝不是呢?
媒体的话语往往会影响民众们看待他人,看待国家、社会的态度,所以此次我们希望通过借闾丘的新书,从中外从业者、研究者的视角来看看偏见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避免。
《不分东西》,闾丘露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出版
闾丘露薇:国际新闻容易忽略日常报道
凤凰网读书:欢迎各位来到凤凰网读书会。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嘉宾。我们欢迎《不分东西》作者、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闾丘露薇,欢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还要欢迎单位网站创办人,来自南非的金玉米。今天闾丘会作为一个发问者和大家聊聊由于中外媒体的不同视角而可能产生的偏见问题。
闾丘露薇:谢谢。金玉米的中文讲的很好。其实你对中国应该是有比较多的了解的,比我们对你的国家要有更多的了解。虽然我去过南非很多次,但是每次去都是带着一些想法去的,去了之后觉得有一些经历会让我对你的国家有一些新的看法。另外胡老师是做研究的,您现在已经可以被定位为“网络传播研究”。
胡泳:专门研究互联网。
闾丘露薇:对,专门研究互联网,在我的书里面有很多提到了资讯的传播对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多少。我粗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很多时候,偏见肯定是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否认这样一个现实,也不要害怕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说偏见不分东方、西方?因为它让我们有一个警醒,让我们去对待一些新的事物,看到一些陌生的东西的时候,不要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不要带着一个预设的立场,只有这样的,我们才有可能了解更多确信的真相。
另外一点,传播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因为资讯太多,很多人都觉得资讯泛滥,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资讯越多其实越有助于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有限的资讯下,你往往更容易产生偏差。在今天的座谈里面,我们稍后也会就这样一个话题进行一些探讨。我想首先问问金玉米,你很早就接触了互联网,你做“单位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眼光去告诉那些英文的读者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在互联网之前,外国人就是中国之外的人,英文的读者,他们了解中国的话可能只会通过媒体,就是驻华记者的报道,但是我觉得互联网会带来一个另类的选择,因为你会发现你在里面翻译的这些文章,选择的很多内容,可能还没有在这些英文的传统媒体里面被报道,所以我会觉得,互联网对于包括英文受众来说,是了解中国社会很好的一个渠道。
金玉米:我是03年开始做网站,当时美国、欧洲的报纸对中国报道的新闻还是特别简单,要么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或者是有很可怕的一个自然的灾难,或者是中国政府干了负面的事情,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中国人开始赚钱了,中国人开始买很贵的车,现在中国有很多特别有钱的人等等,基本上都是这两类的东西。一个是非常不好的新闻,一个是经济,泾渭分明的信息。
通常的生活信息基本上没有,所以除了一些喜欢看关于中国经济报道的西方人以外,一般人除非是专门对中国感兴趣,知道中国不太像咱们看到的这个中国。所以,最早我做单位网的想法是通过用一些中国报纸的文章翻成英文,或者是做介绍,可以让不读中文的人,不了解中国的人,能对中国平常生活有一种概念,做一般的新闻媒体不做的事。
闾丘露薇:事实上在我的这本书里面是花了很多的篇幅,想跟大家解释这样一个现状,因为所谓的国际新闻,就是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国家之外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报道哪一些国际新闻,选择报道和其它的国家有关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觉得那些国家的人和日常的生活好像跟我们这些自己的受众没有太大的关系。金玉米来自南非,问大家看到过的中国媒体对南非的报道的话,我们可能在之前就知道曼德拉,最近就知道了世界杯,但是真正对于南非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是很细节的状态,我们没有太多的概念。如果反过头来我们想一想,透过媒体的构建来了解中国的话,大部分英文的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跟我们对于他们很模糊的了解是差不多的。所以想请问一下胡老师,你是研究互联网传播的,互联网出现后,包括透过这些网站有很多的网友互相翻译媒体的一些新闻,而且非常关注的是那些网友炒的很热闹的新闻……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凤姐,或者是这种现象,外国的传统媒体,或者是驻华媒体对此不会关心,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或者又有什么新的政治政策,或者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的事情。其实从我们教国际新闻的角度来说,这些应该不属于国际新闻的范畴,而且也不太鼓励我们的记者和学生去关注这些东西,认为它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您怎么看?
胡泳:闾丘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她能把所有的活动都变成采访,我到这儿来好像应该谈谈新书,结果她把我们两个人都变成采访对象。实际上我自己是单位网的忠实读者,当然这个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因为我研究传播嘛。金玉米不是一个职业的记者,但是他做的事情就是针对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记者,或者是传媒行业的忠实读者的,那就说明现在整个传播主体对象以及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获得信息来源的这种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国际新闻可能是一个什么概念,他所提供的包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中国互联网那些有意思的东西,可能超出中国传统的范围,因为这里都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在于说我们今天所有谈的东西,都可能变成国际性的东西,因为全球化链条无法不在,每个人可能都不会回到一个原本意义上的一个封闭的家园。我也去过南非,这些年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跟整个世界的脉络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在现在这种全球化或者是网络化的一个时代,原来有一句有名的诗叫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现在真的是这样——你甚至可能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比如说你可能在富士康打工,你可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但是你做的事情其实好多是你控制不了的,是整个全球化的轮子推着你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诞生一种不像媒体却做着媒体的机构,也不像记者但是做着记者的事情,我觉得都是特别正常。
闾丘露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议题设定者
闾丘露薇:想问一下金玉米,你刚才提到像我们做记者报道国际新闻的话,其实希望我们的中国观众能够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包括希望让中国的受众明白世界是怎么看中国人的。在做了这么多年之后,你觉得作为个体的网友,他们在改变以往的我们获取信息、获得信息来源的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大?因为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靠媒体给我们传递的信息,然后再构建出来的。在以往,这些构建的信息都是被媒体主导的,我让你看什么样的事情,关注什么样的话题,我是很被动的跟着媒体去走,但是有了互联网之后,你会发现,如果积极参与的话,每个人都会成为这个议题的设定者,而我的选择就会多了很多,我可以根据我感兴趣的议题去挑选信息。你做网站这么多年了,坚持了这么久,你觉得有没有达到当时所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期待大家对于中国的了解可以多元化一点,而不是只是从媒体上看到的政治、经济或者是一些和异议分子这些方面。
金玉米:怎么说,我觉得有改变,但不是特别简单。第一,现在不是我们一个网站在做,很多美国人到中国游学,自己开博客,甚至是传统媒体也开始用跟我们同样的做法来报道中国。《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博客,主要是北京、上海的记者在这个博客里写东西,最近我发现他们跟单位网或者是跟其它的英文网站的做法一模一样,他们经常会去看微博,把一些网友的评论翻成英文。传统媒体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很看不起博客,是很看不起网民自己做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公民能当记者,公民当记者,那记者干什么?我觉得中国不一样,所以中国记者一般看博客,看网络,觉得这是一种自由。西方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看网络,就觉得是威胁他们工作的一个工具。
这还没回答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影响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可是无所谓,并不是因为很多住美国的美国人看单位网,住美国的美国人不喜欢汉语,或者跟中国没关系的基本上不看我们的网站,谁看我们的网站?记者。所以通过影响驻中国的一些外国记者,我们可能也影响了国外的观众或者国外的读者对中国的看法。
闾丘露薇: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其实这样的变化跟中国的记者现在面对的一个变化,以前涉及的变化也是很相似的,现在中国媒体记者的很多消息或者一些线索就是来自于网络,来自于微博或者博客,以前是帖子,现在我如果看《纽约时报》的话,可以发现它报道速度真的很快,报道像乐清的事情,这种事情在以往是不太可能。以往可能还是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它才能会有兴趣或者说做出一个反应,而且对于驻华记者和外国媒体来说,这些事情好像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那种新闻的高度,或者说没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可是现在你会看到,他们跟着网络上的热点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我想问一下胡老师,互联网在中国的作用和国外比起来真的是不一样,包括博客或者微博客这样不同的形式,很多的网络词汇出来后,把它定义或者标签为一个好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东西,当然我不太喜欢标签一些东西,比较喜欢警惕任何一种去把一些东西提得过高的提法,你也写过一些文章,提醒大家关于微博对社会造成的乐观影响不要期待太高。你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讲?
胡泳:记者和公民之间的角色转换
胡泳:我希望待会有机会转过来作为记者进行采访。实际上刚才金玉米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察,他说,可能中西方对于公民记者或者公民新闻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在中国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会注意到现在公民和记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便举个例子,你看闾丘露薇的这本书,这书的第二部分叫做“从记者到公民”,我觉得研究记者和公民之间的角色,是个特别有趣的话题。
在中国,很多记者不得不变成公民的身份来发布新闻,尤其是当他有了博客、微博这样的平台以后,他可以不发在供职的媒体上,他就有记者和公民这样一个角色转换。与此同时,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公民现在拿起照相机、摄像机、手机和所有的新闻媒体平台,变成记者。
所有的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我们经济上去了,但是其他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结果就导致大家都蜂拥地挤到一个渠道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可以看到如此多的热闹事情,如果三个月里你完全没有看中国互联网上发生的
事情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落伍,因为很多新的人、新的事、新的词语你就不知道了,这就是当所有人拥挤到一个通道的时候,它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因此,在中国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应用来到以后,它本来很多技术应用可能是满足其他的需求,而现在微博的媒体功能远远压倒它的社交功能,就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前提存在——大家需要表达。而且不仅普通的公民需要表达,记者本身也需要表达,因为记者相对公民来讲,本身已经被视为有话语权、有表达权的一群人,但是他自己在供职的地方表达不了,所以他也到这个地方来表达,所以你看到在微博上最活跃的一帮人其实是传媒人士,然后再加上所有的这些公民。
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互联网,每天会发生新的事情,这就回到刚才的一个现象上,为什么说网民不仅设置了中国媒体的议程,现在正在设置外国媒体的议程,比如金玉米已经举到像《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实时报,开始大量地关注中国的微博空间里面人们在说什么,你还看到中国所有的网络上热炒的事件用不了多久就会登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经济学人》,所有的这些最大牌的媒体都会追踪这些线索,然后写成故事。
闾丘露薇:说到“李刚事件”,我感觉比较深刻的是像这种网络热门词,以前很少机会出现在国外大报上面,可能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觉得好像没有大到大家改变对国际新闻的定义,它属于比较本土化的、本地化的话题,但是现在可以发现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
金玉米:吃饱了撑着的外国人
闾丘露薇:我在这本书里面谈得比较多的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涉及到中国人对国外媒体很多的批评,包括在气候峰会上,很多的中国人对于外国媒体的观察不是太好,觉得它们不太友善。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教研究生的时候,99%是来自内地的学生,当我让他们做功课,把中国的、西方的媒体的同一个报道都拿出来,让他们分析中国和西方报道的不同的时候,我的这些学生们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些西方媒体是站在自己国家的利益上,所以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等等。他们非常自然而然的会把媒体和政府的立场去挂钩,把媒体的一些负面报道等同于政府的态度。
我发现,这么多年了,这样一种思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很多的年轻人的脑子里会重现。虽然我不停地给他们解释说,在国外是有所谓商业媒体的,商业化媒体是听老板的,当然根据独立制,影响状态也未必100%。我想问一个金玉米,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你接触到的身边的中国朋友,包括中国媒体,对待其他国家的认知会不会出现偏差?或者是因为我们对于国外的一些媒体属性没有一个太清晰的认知而导致这样的结果?
金玉米: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南非还是种族隔离时,黑人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人权的情况很糟糕。基本上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觉得我们有严重的问题,都觉得南非政府不好,白人不好,我们家是属于比较自由派的人,我爸妈都不喜欢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属于左派。
闾丘露薇:我想问一下,左派跟我们中国的定义一致吗?
金玉米:不一样。我们是反对政府的左派,比如说去英国,很多英国人会批评我们南非白人, 他们对南非没有什么了解,对我们家的思维方式也没有什么了解,一听到我们是南非人,就说你们南非白人如何,虽然当时南非政府是不好,但是我们第一反应是:你是谁啊?你了解南非吗?你去过南非吗?你没去过,说什么废话啊。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所以中国人看西方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很自然的反应是“吃饱了撑着的外国人”。
这个没办法,你不喜欢外人来说你的坏话,谁都一样。有的时候比较难判断是偏见,还是人家说你自己国家的坏话,你不喜欢。
第二点,有很多优秀的外国记者也不希望只报道中国的负面,可是在纽约或者伦敦的编辑就不一样了,他们对中国不了解,说白了就是他们对中国无所谓。所以如果新闻没有一个很刺激的内容,没有工厂长做坏事,没有战争,没有很大的经济新闻,他们一般不感兴趣,很多问题都不是在中国的这些驻外记者做的,是总部编辑决定,比如说2008年有名的西藏照片被剪事件,很多中国人都不开心,这不是在中国的记者做的,都是美国总部做的,这些也得知道、得理解。
中国的记者也是同样的情况,怎么办?我觉得如果要对其它的国家有一个比较公平的看法,不能只看一个电视台,不能只读一份报纸,不能看一个博客,都得研究研究。
闾丘露薇:我非常赞同金玉米讲的,就是你清晰的来源不能依照一个信息源,如果太过于信任某一家媒体或某一家信息源,你总有被误导的一天,因为没有一家媒体能把一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总有犯错误的时候,我的书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在2008 年到2010年,发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其实就像金玉米讲的,有的时候是后台的编辑决定的,这个编辑可能根本不知道中国在哪里,根本不知道尼泊尔警察和中国警察的有什么区分。
说老实话,如果我们来看非洲某个国家的话,我也相信没有几个记者能把南非的警察跟相邻国家博兹瓦纳的警察分清楚,我觉得也很难,都是黑肤色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把别人对我们的印象看得太重,觉得中国那么大,你怎么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警察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误解。就好像《纽约时报》犯过的一个错误,把我们的主席和总理的名字写错了,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接受,很不幸的是对于很多编辑或者很多国外的人来说,他确实并不知道你的领导人是谁,而且他也觉得并不重要,我为什么一定要记住他到底是谁呢?当然,这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说,看到之后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气愤。
继续采访胡泳,我想请您谈谈您对中国媒体的一个看法。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依照中国媒体从世界各地发回来的报道,或者我们翻译外电的报道,导致了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外界的看法。
从我的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时间紧张,就没有那么认真,觉得反正你也看不懂,稍微错一点点问题也不太大,当然,这不鼓励。但是很多时候确实会发现我们在批评西方媒体犯错误的时候,中国媒体其实也经常在犯,最明显的是我们在翻译别人原文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翻译错误,或者断章取义,而这些错误往往会让我们产生非常激烈的反应。
类似事情2010年发生的非常多,我在书里面也特意提到了我们亲爱的《环球时报》。展江在微博上说,《环球时报》出了一大篇的报道说,外媒报道中国建造航母之后,中美必定会有一战。这个外媒就是《马来西亚日报》,很容易去查证它,挺可惜的是展老师也没有去查证。其实是马来西亚在东马的一份西方媒体,发行量不多,属于快要倒闭的状态。但它毕竟是一份外媒,有时候你会发现中文媒体经常引用外国媒体,
但是造成了一种外国主流人群就是这么看中国的印象,事实上,它经不起推敲。
警惕每个人会提出自己的真相
胡泳:对,展老师没有去查证,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基于原来的一种认识。就是《环球时报》经常造假。
其实,你会看到媒体在建构大家头脑当中的认识的时候,作用非常大,因为它可以做很多的选择,它做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选择,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认知是有选择性,可以是选择性的认知,可以是选择性的记忆,你可以不去记忆你不想记忆的东西,只记忆你想记忆的东西。所以对于很多读者形成这个事件的看法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新闻媒体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所在。
在今天,你会遇到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你们看闾丘的书,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所有的记者都会声称自己是追求真相,媒体都会声称以追求真相为自己的一个宗旨,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真相是特别扑朔迷离的,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真相,说不清楚真相的一个最核心的结果会比较可怕——每个人会提出自己的真相,不管你提供多少证据证明你的清白,但是如果我自己有一整套的逻辑,我会始终认为你是在掩盖事实,反过来讲,其他人看这个事情也会是同样的逻辑,真相是特别难以捕捉的。
所以我在北京大学讲新闻学的课程,经常说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已经是过时的东西,大家应该张扬的是,如果你要讲媒体或者新闻的价值的话,最关键的词不是客观性,而是平衡。这个平衡其实跟刚才金玉米讲到的非常相关,你不能只看一种报,你不能只看一个电视节目,哪怕这个博客你多喜欢。比如你特别喜欢韩寒,你也不能只看韩寒一个人,你一定要做到平衡,因为平衡才是最有效消除偏见的办法。当真相无从捕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去看各方的东西,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眼中的真相里面都搀杂了他的偏见,所以我认为平衡的价值远远高于客观性。
闾丘露薇: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人、一家媒体很难捕捉到真相,好在大家有很多的选择,否则的话,你永远是在有限的资讯里面去进行判断。如果你依赖的信息源就那么多的话,再聪明的人也可能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天上午,我跟于建嵘有一个对谈,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我之前在伊拉克的时候遇到的事差不多,我在这本书里面也写有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常从一张照片或一张构图里面判断出我知道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
在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印象当中是萨达姆倒下来,全广场欢呼的场面,我们就以为所有的伊拉克人 都在为这样的解放而欢呼,但忽略了旁边茫然的人,伤心的人,或者是神情复杂不知道怎么办的人。同样的,于建嵘讲到的是当我们看到乐清的一些民众下跪场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他在现场看到情况是这些村民是看到人就会下跪,而且他们只推出年老的人在前面,当有摄像机在现场的时候,你们获取的真相到底是多少?其实也是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在我的书里面,我们拿出了一张照片,是在“七·五”的时候,那位站在武警装甲车前的维吾尔族黑色衣服妇女,很多人,尤其是西方的读者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会有一个判断。但是如果你看看这些在现场的记者的博客,你就会发现现场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事情要比看国外的事情复杂很多,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金玉米,当你看到网络上的一个热门事件突然跳出来的时候,你应该有经验跟大家分享——先不要去急着判断,要去找很多的资讯查一查。
金玉米:现在有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的说法:你在中国待了一个星期能写一本书,待了一年能写一篇文章,待了好几年之后,一张明信片都写不了。就是说外国人待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懂,我觉得有的中国人可能能理解这种感觉,中国特别复杂。
这也是任何外国记者在中国很大的一个挑战,有时候中国确实被烙上负面印象,但是也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尤其从一个南非人的角度来看中国,这30年的成绩,我们南非人只能很佩服。
所以没有任何简单的办法来说中国的故事,我觉得还是以胡老师提的平衡的概念为主。前几天《华尔街日报》博客把很多中国网民的评论翻成英文,都是关于歼20飞机,很多美国人吓一跳,然后发布了很多比较负面的网民的评论。它们一篇文章都是这种批评政府的,这说明很多中国人也并不是那种西方人想象的机器人,有自己的言论。
我自己看了微博,发现并不是那么多反动的评论,其实很多中国人都很为这个事情骄傲,如果你要平衡的话,也得承认有很多言论是看不到的。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他们应该怎么办?这个很难。所以通过信息来源多元化达到平衡。
但是讲中国的故事还是特别特别难,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概念还是特别的简单,就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吃狗肉,这个听起来很傻,但是我每次回南非都会有人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所以不容易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