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本身
我每天上班乘坐的楼巴在楼盘里有两站要停,随着楼盘的扩张,居民越来越多,乘客也就随之越来越多,近一个月来,自第一站时车内座位已基本被坐满,到第二站就常常会出现座位不够的情况,而根据交规,大巴内的乘客数目若多于座位数目的话,一经发现,司机将会被扣分罚款,所以,物业给那些没有座位的乘客留了两条路走,一是回家,二是再等一个小时,直到下一班楼巴到来。
尽管几乎所有被遗弃的乘客都会跟负责验票的保安争辩几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愤慨,但他们还是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选择了那两条路中的某一条;然而,就在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位执意要开辟第三条路的家伙。在7月广州上午9点毒辣的阳光下,他一屁股坐在了车头前方的马路上,大声地向那位保安表示,他将这样一直坐下去,直到可以改坐在物业提供给他的,一个楼巴的空座位上为止。
刚开始,人们都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很快就会跟前些天与他同样遭遇的人那样,怏怏地为车让出道来,所以,大家都很镇定,对此一言不发,该发呆的依旧发着呆,该玩手机的依旧玩着手机,只有保安和司机与之交涉。5分钟之后,那人没有站起来,人们开始相互间低声议论起这件事;15分钟之后,那人还是没有站起来,议论声变得越来越大,并有坐在车后排的人跑到前面去,观察事情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
这时,有一些乘客开始彬彬有礼地向保安或坐在街上的那个人提出询问和建议。向保安提出的询问无非是有没有可能满足拦车者的要求,在得到斩钉截铁的否定答案(“所有的车都已发出”,或“你们为难我有什么用?我不过是一个打工的,这件事也做不了主”,诸如此类)后,他们也就识趣地不再向保安提任何建议,而将力气全部放在了拦车人一方——实际上,大家一早已经意识到,将这个人作为突破口在客观操作上不仅更为简单直接,甚至更为情安理顺,而之前向保安提出咨询,不过是为了令后来向那人提出建议这件事,变得更为情安理顺而已。
大家向拦车者的建议是:首先,希望他能冷静下来,然后,请他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思考和行事,要识大体,不要一个人影响一车人,赶紧站起来,让到一边去,好放我们走——其实,说一个人影响一车人并不准确,多出来的乘客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有四五个,他们形成一个奇怪的团伙,表情尴尬地远远站在一边,既不离开,也不呈出自己的态度——但即便仅仅不离开这一现象,似已构成某种倾向乃至压力,笼罩在人们的头上。
渐渐,出离所有人预料的是,30分钟竟然过去了,而那人还是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人们已经失去了耐心,提出意见和解决方案的人越来越多,其言辞和口气也愈显激烈。
一位怀里抱着小孩的年轻妈妈厉声喊了一句:“再这样拖下去,孩子去幼儿园都要迟到了!”
一个理性沉着的男声随之传出:“如果车里有要去考试的孩子,急于看病的老人的话,你耽搁大家就是在犯罪!”
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叹了口气,质问拦车者:“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这样一意孤行,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有没有想过以后在路上遇到我们时,你该把脸藏到哪里好呢?”
一位老人家痛心疾首地说:“看看现在社会沦落成了什么样子?人们连最后一点舍己为人、集体主义的精神都丧尽了。”
一位大学生模样,吐字很快的姑娘清脆而亢奋地号召大家:“他这样做就是拿我们一车人当人质,对于这种类恐怖主义行径没必要客气,让我们一起下车去把他拉开!”
对此,坐在她旁边的一位应是她男朋友的小伙子说:“使用暴力终归是不对的,就算非使用暴力不可也轮不到我们,让我说,不如打110算了。”
这时,一位先前一直低头读书,摆出副不闻身外事的样子的中年男人嗖一声站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车前,以一种刚从妻子那里获悉自己头戴数顶绿帽后的心情方能逼发出的,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尖声尖气的腔调,对司机叫道:“给我开车!踩油门!向他压过去!看这个傻逼躲不躲开!”
……
就在这乱糟糟的争论中,车突然开动了。也就是说,那人让开了路。他之所以这么做,究竟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物业同意了他的要求,甚或是为了躲开果然在戴绿帽者鼓动下赫然向他压过来的大巴,我们一无所知——事实上,从车内很快恢复的,通常那种和和气气、死气沉沉的气氛来看,已没有谁还对这件事感兴趣了。尽管车开动后人们还是就其议论了一阵,但这议论平息下来的速度显然要比事情刚发生时议论渐渐喧嚣起来的速度要快得多,显然,相比于忘掉一件令人烦心的事,要比面对它容易得多。
为什么还要为之烦心呢?反正车已经开动,一切即告结束——即便,也没有谁可以担保明天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事实上,大家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能估计到,令这件事得以发生的各种客观条件,当然不会因所有人目前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发生改变,这样,它继续发生几乎是势必的——大家不对此感到好奇吗?不仅修建大坝和砍伐森林的人,此时此代,连不过坐个屌楼巴上个屌班的人都要与时俱进地摆出一副老子仅活到今天为止的姿态。
从这件事中想到的
我没有仔细读过物业方面相关楼巴的服务条例,但我想,在他们同意并实质上将车票出售给我之后,双方已建立了一项契约,在顾客不违反卖方服务条件的情形下(如可证明楼盘业主的身份,已购票,依照卖方制定的时间点去排队候车,没有传染病没有携带危险品不会在车内满员情形下强行登车等等),那么,卖方就应该保证每一位顾客在按时侯车后可以准时乘车。诸位,如果要讨论这件事,这个前提不知你是否同意。
那么,在整个事件中,若将车内的乘客视为一个团体,且称之为“我们”的话,请问,我们究竟跟谁是一伙儿的?
保安在用诸如“大家都赶着上班呢”、“车里有老有小”、“你不能强制所有人为你一个人上不了车而摊付成本”之类的说辞劝告拦车者时,却多面朝车内,语气煽情,显然,对于这几日中央正在号召开展的群众路线,他掌握并响应得相当不错。我们呢?在事件发展至白热化时,我们对拦车者的憎怒和要赶走他的决心,表现得比物业方面还要强烈得多;若拦车者再坚持拦个十几二十分钟,引发我们下车将其群而殴之乃至失手打死的结果,一点儿也不会令我感到奇怪。至于拦路者,起初他也不是没有试图博得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但随着时间逝去,在我们跟物业愈演愈烈的同仇敌忾的逼迫下,彻底被孤立的他也就毫无退路、毫不含糊地自绝于人民,再也不流露出一丝请我们站到他那边的意思,不但一句软话不说,反而铁口咬定:“我走不了,谁也别想走。”
综上,从三方面的客观所为来看,显而易见,我们跟物业是一伙儿。
然后呢?然后让我们先把昨夜跟老婆的争执及公司打卡制度的落实放在一边,想想“一伙儿”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难道不是指身份、处境和诉求相同的一帮人吗?若你同意这个解释,那我们又只能跟拦车者归为一伙儿。
我们和拦车者在身份上都是乘客,在诉求上都是坐车走人,这个好理解,关于处境相同指的是,拦车者所处的看似特殊的处境,我们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可能置身其中——这也是本文刻意没有描述这位拦车者性别年纪等个性化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与此同时,正因为我们有可能陷入的跟拦车者相同的困境是由物业一手造成,所以我们不但不该跟后者一伙儿,反而应站在其敌对面。
多么奇怪,是什么致使我们在化友为敌的同时认贼作父?——是我们那双跟老鼠一样,只能看到自己眼前一寸远的地方的眼睛——加上物业的唆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拦车者的拦车行为本身之上。这一行为诚然不当,属于标准的牺牲集体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即便他已明知难以如愿以偿,物业是不会为他新发一趟车的,拦车不过仅是为了出一口恶气罢了,而“出一口恶气”当然也算一种利益),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同意这么一个道理:人类社会的一切恶,皆基于靠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获利的念头与行为。难道,除了盘剥别人之外,人就没有别的办法(与别人平等公正地相处互用或独善其身)活下去了吗?对一伙儿人而言,牺牲一小半人的利益来换取剩下一大半人的利益跟牺牲一大半人的利益来换取剩下一小半人的利益同样不当,进而,牺牲一个人的利益来换取剩下所有人的利益亦为不当。这样来看,我们渴望将拦车者像口痰般吐掉的行为,跟拦车者企图像个瘤子般长在我们身上的行为,犯下了同样性质的错误。
据此,你如果还要执意谴责拦车者的话,在谴责之后,请加上“尽管我和你是一伙儿的”这样一句话作为补充。这句补充,哪怕拦车者不再拦车,换成更极端、更骇人的行为后,亦必不可少——因为那是整件事的开端和本质。
此外,请格外注意,拦车者的行为证明了与之一伙儿的我们的处境已经糟糕到了须用拦车这一,如那女大学生所说的“类恐怖主义行径”方能处理的地步,只要拦车者不是疯子,导致其拦车的所思所想什么不可能在我们每个人脑中重演呢?不要用性格不同作托辞,只要我们中有一个人去拦车,我们每个人就都要做好去拦车的准备。
这三方里,物业看似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制定并执行我们的乘车规则),而这权力仅基于其售卖给我们的服务——对物业而言,其所谓权力跟它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一样都是虚拟的玩意儿,我们凭什么要指望物业服务于我们是源自某种爱呢?源自某种理想主义、人性的本来、美德、必须秉持方不会疯掉的社会观念?乃至神的指引?诸位,这些指望若都不可喻为狗屁的话,什么才可以喻为狗屁?物业唯一在乎并令其存在变得合理的仅是盈利,而为了保证盈利,他们必须要保证公正行使我们赋予的权力并保证令我们感到舒适的服务——请相信我,若换一套背景和视角,若为了盈利他们可以滥用我们赋予的权力并杀害我们的孩子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照做不误。
由此,真正的权力正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整件事情中唯一使用并正确使用了这项权力的人,没错,正是拦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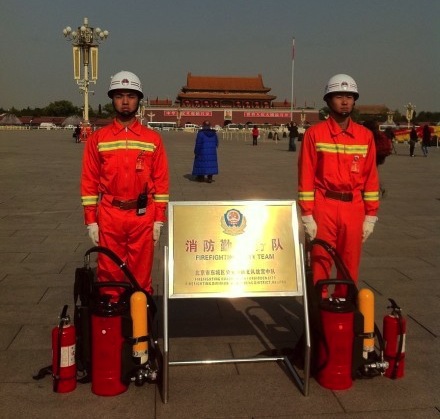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