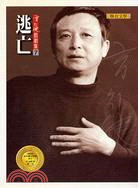
(原文刊于2017年6月4日星期日明报,此版本经过修改。)
「时间,首先令我们变得踏实,然后令我们困惑。我们自以为变得成熟,其实只是懂得令自己安全。我们以为自己变得有责任感,其实只是懦弱。我们所谓面对现实,其实只是避免麻烦而不是面对问题。时间⋯⋯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自以为有理有节的抉择,都会变得摇摆不定,自以为确定不移的事,不过是霎时冲动。」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在《回忆的馀烬》(The Sense of an Ending)裡告诉人们,时间令记忆变得不确定。六四已经过了二十八年,有些人选择老一套的方式悼念,另一些人选择另一种方式来纪念。早在二十八年前,已经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想像的途径,反思这场悲壮的民主运动。文学一直帮助我们收集记忆,重现历史,形成记忆的共同体。
在逃亡中相遇
二十八年过去,回看高行徤的剧作《逃亡》,仍然令人感概两代人对民主运动的不同看法。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逃亡》很有可能是首个反思这场运动而在海外上演的华文戏剧。当年八月高行健在巴黎见到第一批离开中国的流亡份子,九月底开始写作,一个月后完成。这个剧只有三个角色,两名二十来岁从广场逃出来的学生,避险时遇到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同样在逃避搜捕。两名学生在广场上度过了许多跳舞、广播和集会的日子,男学生坚信「不自由毋宁死」,人民最终会取得胜利,女学生则开始思索运动结束后的前路,想做回本行当个演员,最好能够组织家庭。他们逃过了士兵的子弹,可是逃不过世故的中年人对他们的质疑。中年人是个作家,经历过中共假人民之名干下的政治运动,见証了最终受苦的还是人民,因而不再相信「人民」的名义。他质问男学生:「也不要说什麽最后的胜利,要是自由只带来死亡,这自由无异于自杀!命都没有了,那最后的胜利遇有什麽意义?」中年人的政治热情大概早就被文革埋葬了,失掉了学生的理想主义,深明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持政权。这麽多年过去,中年人的悲观态度和学生的理想主义,谁更接近现实的考验,相信大家心裡有数。
抗拒虚无主义
然而,高行健并没有渲染虚无主义,教训大学生一切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只需遵守后极权主义定下的规则,享受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剧裡,中年人同样参加了民运,联署各式各样的公开信,他和学生的分别不在于是否反抗国家对人民自由的遏制,更不在于争辩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更民主、更适合中国,而在于他看重每一个人的思想自由,摆脱一切理论或主义给人的桎梏。显然,中年人就是高行健的化身,反映了「没有主义」的文艺观,带有逍遥无待的道家特色。中年人经历过政治理想的幻灭,面对「一潭髒水」似的国家,于是看到每个人「心中只有那麽点幽光」。要守护每个人独立的声音一点也不容易,「总像在冥河中行走,阴风四面吹来,随时都会熄灭」。剧中女学生的角色绝非花瓶,鲜明地表现出独立的内心追求。她目睹广场上的屠杀,惊魂未定,生死一线间,激发了她表露对生命的盼望。她无情地批评充当保护者的男生和奴化女人的男人,同时不讳言与钟情的男人欢好的欲望,纵使害怕政治这潭「幽黑的死水」,仍然勇敢地闯进去。无独有偶, 娄烨的电影《颐和园》,以1989年北京的大学生为背景,女主角是北大中文系学生余虹,跟高行健笔下的女学生一样,敢爱敢恨,民主运动尚未成功,她就首先解放了身体和情欲。
政治和情欲压抑
在后极权社会裡,文学艺术中常见政治和情欲的压抑,当政治令人窒息,情欲几乎成了最坦诚和最自由的表达途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在《爱情与垃圾》(Love and Garbage)和《我快乐的早晨》(My Merry Mornings: Stories from Prague)裡,描写捷克布拉格之春后的日子,捷克共产党的管治下,城市裡平凡的小人物,在婚姻内外强烈渴望被爱的感觉,到处寻找隐蔽的角落,躲藏起来享受鱼水之欢,他日想找回匆忙间亲热的暗处,却遍寻不获。在六四二十週年,流亡英国的作家马建发表了长篇小说《肉之土》(Beijing Coma),题材来自他在中国对六四的见証,充分表现了1989年那一代年青人承受着政治和情欲的双重压抑。《肉之土》的主人翁戴伟有过几段恋情,高中时跟女生偷尝禁果,被要求写检讨书。在广州上大学读医科,他结识了来自香港的女孩媚媚,二人在旅行期间租住宾馆,本来可共赴巫山,却遭旅馆店员提示要分房睡觉,以备公安查房。后来他们租住公寓,二人同居,恋情却没有开花结果,因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铁定回归中国,媚媚想到国外留学,家人又干预这段「中港关係」,视大陆学历没有前途。大学毕业后,戴伟考上北大研究生,认识了女生天衣,时常在宿舍八人大房裡翻云覆雨,有天到了圆明园以为可以放纵尽欢,不料遇上流氓勒索巨款,要胁呈报公安。政权似乎连年青人最基本的欲望也漠视,戴伟一句话彷彿道出了一个时代:「我要求的不多,就是让我们在大学裡自由恋爱就行了。」
理想主义幻灭
可是,马建的《肉之土》绝对没有把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简化为年青人燥动不安的反叛故事。事实上,书中描述北大学生关心国是,积极参与知识份子的座谈,讨论民主化的前路,在广场上协调各界支援,建立天安门民主大学等。当戴伟还在广州读大学时,他和媚媚就代表着两种典型,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对知识如飢似渴,精神分析、西方文学和科学理论的书,通通都贪婪地吞下去。香港学生媚媚反而从不看书,马建藉此嘲讽香港人没有文化,看不起落后的中国,最擅长过关时买免税品转手图利。在小说重现的情景裡,我们大概体会到当年香港人广泛支援天安门运动,代表了社会上稀有的理想主义,跟北京学生的热血溷在一起,冲破极度功利的社会表层,香港人乐乎从未如此团结地表达对民主的响往。也因为这种短暂而激烈的理想主义遭到极其粗暴的镇压,香港人六四的伤口一直未能癒合,记忆冻结在梦想幻灭的那一刻,九十年代的学运低潮和纸醉金迷的过渡期,反映了理想错败后的虚无主义来袭。
记忆冲破虚无
《肉之土》或可视为对虚无主义的回应。戴伟搜索枯肠,不是为了再次成为历史的主人,而是为了当历史的见证人。广场上的镇压,令戴伟受伤成了植物人,身体就冻结在六四那一刻。可是,在医院裡听见母亲和朋友的话,他努力地追寻各段回忆,重新认识父母的生平——他们在美国出生,一个是小提琴手,一个是女高音,不料回国后遇上文革浩劫势,被打成右派,终生鬱鬱不得志。他们那一代人彷彿完全是历史的受害者,戴伟却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得益于西方思潮涌入中国,80年代政府开始放鬆言论管制,这一代人勇于投身民运,期待急剧的改变,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然而,作为植物人的戴伟成了惨白的形象,多大的改革激情也无法再流露出来,反映了1989年那一代年青人遭受无情压制,只能变成历史的旁观者,甚至成了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当我们发现历史的巨轮不能改变,我们是否轻易就否定一切行动的价值,嘲讽别人坚持的原则?戴伟的肉身瘫痪了,但是没有停止收集记忆,他让自己、父母和朋友的各段记忆交会,彷彿「时间在眼前重叠,过去如血网在肉裡伸展」。围绕在他的床边,不是种种对历史的宣判,稳定压到一切或者人民终必胜利,而是彼此交错的历史见证,令他的身体得以活着,甚至重新动起来。
记忆的共同体
小说以一个颇为悲观的问题作结:「离开这肉牢,你又能到哪裡⋯⋯」也许我们能给予一种回答。当政府鼓吹人民避谈镇压来装饰其管治,唤醒共同的记忆就如同召唤许许多多受伤和放逐的灵魂,因承载了他人记忆而走在一起。我们应该看清楚,谁也不能离开历史这座血炼的牢房,历史不会转身就成了天堂。《逃亡》裡,中年人并没有对政治变得冷感,反而领悟到政治要求巨大的耐性:「小伙子,你不能忍受也得忍受,你得忍受失败,你那种盲目的热情在死亡面前无济于事。」政治运动遭受错败后,激情消耗殆尽,只有坚靭的耐性可以令我们度过权力的追捕和逼害,明白到政治悲剧揭示的世界——人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逃亡,不同世代的人们与其在逃亡中互相折磨,不如互相谅解。
活在香港, 最独特的是就算你不参加任何行动,社会都会有声音不断提醒你六四又一年了。新一代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如此震撼的时刻,固然不能怪责他们没有感受。想深一层,前些年社会辩论当年天安门到底有没有死过人、死了多少人,学生做得对还是不对,维园烛光晚会的形式是否过份行礼如仪等,这些其实都构成新一代年青人对六四的记忆,准确点说,是对他人的记忆的记忆,历史本身就是持续地忆述和记录事件。各种悼念和讨论六四的事件,都是收集回来的记忆,各式各样的记忆大柢构成了香港社会独特的记忆共同体,跟中国、台湾和海外的华人社会有所不同。在这个共同体裡,人们不分藉贯和语言,甚至跨越世代的界限,互相诉说对六四的记忆,互相印证和批评,由此再引起更多的回忆和共鸣。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说得好,只有当人们共同忆述往事,回忆才会变得更加鲜活,不致日渐面目模煳,终至遗忘。记忆的共同体成员,不必然拥有一模一样的记忆,他们分享着他人的回忆而连繫起来。文学正好丰富了回忆的世界,一切反省和批评在某个程度上,也令共同体更具历史的厚度。只要记忆的共同体能继续留存下去,就不用担心人们对历史罪行变得麻木,正如朱利安.拔恩斯写道,回忆「有所累积,就有责任,在此之外,有所不安,极大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