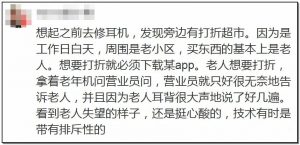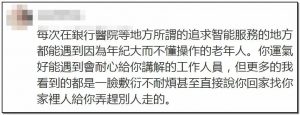几天前,浙江台州一位货车司机在公路上遇见了一位打招呼问路的大爷,大爷抱着锅碗瓢盆,从安徽来,准备去台州黄岩区投奔亲戚,他没法查导航,也没有手机,现在正徒步赶路,他问司机还有多远到城里。
大爷的故事,经自媒体平台传到网上,成了一个现代奥德赛的传奇故事,说大爷没有健康码,坐不了车,从安徽徒步千里来到浙江,引发全体网友的同情和愤怒。但6月23日早上,反转就来了:大爷是坐火车到杭州的,接着转车至绍兴。铁路部门还说,没有健康码,也能坐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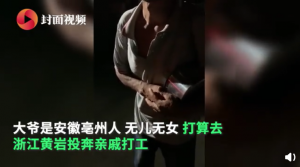
新闻报道截图
闹剧一场,人们很快也忘了这件事,至于大爷为何深夜还在野外徒步,也不得而知。但“徒步千里”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技术时代对老年人的确不太友好,几乎要把他们抛下了。
新闻再怎么反转,也无法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没有健康码的老人们,被公共交通抛下,被挡在小区之外,事情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数字鸿沟,作为一种社会鸿沟,是始终存在的,且逐年加大。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控制,更将其陡然拉开。
奔涌的技术时代如何面对庞大而沉默的数字遗民,这场大流行展开了新的维度,考验着我们的日常与社会伦理。
崩溃于智能手机
疫情期间,我采访过几位被智能手机搞到崩溃的老年人。
一位是武汉的阿姨,她在1月中旬感染了新冠肺炎,一个月后治愈出院。但麻烦并未到此结束,她身上还有癌症,化疗迫在眉睫。武汉此时大多数门诊都停了,她的主治医师叫她下载某个APP,虚拟问诊。
这位阿姨刚失去一位至亲之人,现在是独自生活。一位亲戚远程指导她,弄了一上午, APP始终下载不来。没被新冠肺炎打倒的阿姨崩溃了,大哭了一场。

许多老年人看病,面对网上预约挂号、缴费等流程往往无能为力
还一位是老陈,4月份,他从四川回南方某城市复工,老陈今年58岁,原本是建筑工人,现在年纪大了,改做保洁。他的出租屋租在某个城中村,那里平时管理松散,但疫情期间加强了控制,只留一个进出口,建了扇临时的门,且需要健康码。健康码要在小程序里设置,老陈有微信,但他从来没听过小程序。
他站在路边跟外地家人打电话,外地的家人对此也一无所知,弄了几个小时,天也黑了,手机也没电,他仍未能回到出租屋。
没有智能手机,在城市里变得寸步难行。他想找个住处都存在困难,便打算在地铁口对付一晚上。是附近一位年轻人路过,了解了他的困难,帮他租了个充电宝,并申请了健康码。
那位热心肠的年轻人,将此事发到了个人社交媒体,然后才进入了媒体报道的公共视野。原本,吃了闭门羹的老陈,跟沉默的老年群体一样,他的故事也是不被看见的。

2020年3月20日,一位老人使用非智能手机(俗称“老人机”)无法扫健康码,黑龙江五大连池市防疫人员与老人发生肢体冲突,导致老人“面部受伤流血”
信息化覆盖至社会的每个角落,给年轻人带来了不可斗量的红利,也造就了一条护城河,把老年人拦截着城外。
网络是个公共话语空间,它是年轻人的,是年轻人可以沸反盈天的世界,但在这里,老年人始终是数量庞大的失语者。
据国家统计局的2019年数据,其中60岁以上的人,上网比例仅23%。每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未曾接触过网络。此外,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也就是说,有5亿人是不上网的。
疫情加速了社会治理的信息化程度,网购、扫码等迫使一大批“数字遗民”不得不进行“赛博移民”,试图逃离由疫情及其控制措施所制造的孤岛。各大平台上,智能手机老年用户均剧烈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
孤岛
疫情期间,武汉的老刘几乎全家感染,女儿刚去世,13岁的外甥女急需救治,77岁的他不得不上网求救,他在发出的第一条微博,只有两个字:“你好”。
“你好”二字,像是拨通了一通未知的求救电话,是一场艰难的“造访”,跨越了巨大的数字鸿沟。
一次采访中, 我了解到一位武汉的独居老人。老人浑身基础疾病,家人们也纷纷确诊新冠肺炎住了院,独居在家的她没有智能手机,没法上网,也不能跟家人们视频通话。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翻座机旁的电话本,给所有能联系上的人打电话,打给亲戚,甚至打给不熟悉的人。她的家人告诉我,他们知道她孤独,孤立无援,想见儿女们,但却无能为力。最后老人在孤独中去世。
3月初,一位武汉的微博用户发出求救,她的奶奶在医院里情况不太好,家人想连视频看一看老人家,安慰她,减轻她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他们把平板送去医院,但始终没连上,也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应对新冠疫情的最好办法,可能是物理疏离,这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甚微,我们可以尽情地网上冲浪。但这让老年人陷入了孤岛,瓦解了日常生活的运作。
新冠疫情压缩了日常的生活空间,没有网络,他们便难以重建社会生活的参与感。有年长者曾说:”我们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一座建筑的外面,无法进入其中。”
美国网站“Senior Planet”的工作人员给全美2000多名老人打电话,询问他们在隔离期间需要什么,回答大多数跟网络相关。很多人想要Zoom视频会议的教程,这样才能跟人视频通话,也有人想要游戏、远程医疗、乘车应用等教程,他们想参加虚拟社交俱乐部,想在线约会,想跟世界保持联系。
生意应运而生。比如Candoo,这是美国一家帮助老年人浏览技术的公司,用电话教客户如何使用Zoom和其他视频通话软件,接管老人们的屏幕,并告诉他们在哪里点击。
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有的老人对媒体说:“跟病毒斗争已经不容易了,与技术斗争增加了另一个层次的压力。”
与社会隔离有关的风险是深远的,医学已经表明,老年人的孤独感与抑郁症、心血管疾病、功能衰退和死亡等息息相关。
技术应该用以减少这样的风险,而不是拉开其中的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消除横亘在老年人面前的数字鸿沟并不简单,必须要正视数字准入障碍的问题。
这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仅关乎日常生活,也可能给特殊时期的社会心理留下深重的影响,更涉及社会治理的的宏大命题。
“数字鸿沟”一词来自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一书,信息化带来了“数字机遇”的发展红利,但也因信息落差造就两极分化的趋势,潜藏着新的不平等,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不同种族或者文化程度或者收入水平。当然,也存在于不同年龄之间。
数字鸿沟应该具有一个公共性的含义。准确来说,是不同人在信息获取、使用和借助数字资源参与公共活动的程度,存在着日益扩大的差异。
数字能力强弱,带来强大的“挤出效应”:自动化,使数字能力孱弱的中老年工人,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在韩国最为明显。韩国是信息产业大国,同时也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字化带来企业大换血,很多员工远在退休年龄到来前,便被迫退休,只得从事一些低收入的工作。2018年,韩国有133万的60岁老龄零工,其中90%的人,从事快递、保洁等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
接下来的问题是,随着快递保洁等行业的信息化、自动化,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数字社会的进化,会形成一种反复叠加的阻力,妨碍老年人公平地参与社会。
2002年,世卫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它为各国的老龄化政策提供了框架:健康,参与和保障。当各行各业被大数据、AI、5G等创新技术颠覆时,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积极老龄化的内核、路径极其归宿。
老人们抛下公共交通,被挡在门外,事情零星地发生着,健康码的问题看似问很小,但也值得反思: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我们,对待老年人该有怎样的内在伦理和价值导向。
数字普惠的重要性,不会随代际变化而消失。技术社会在进化,每一次创新,都会给一代人带来适应性的挑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教授、老年病学家路易丝·阿伦森说:“我们如何对待长辈,既决定了老年人的现在,也决定了未老先衰者的未来。”
中国将在2027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也就说,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比例的15%,老龄化问题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压力,不得而知,但可预见的是,届时我们的经济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当我们谈论数字鸿沟下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时,我们谈论的,既是现在的他们,也是未来的我们。
编辑 | 董可馨
排版 | GI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