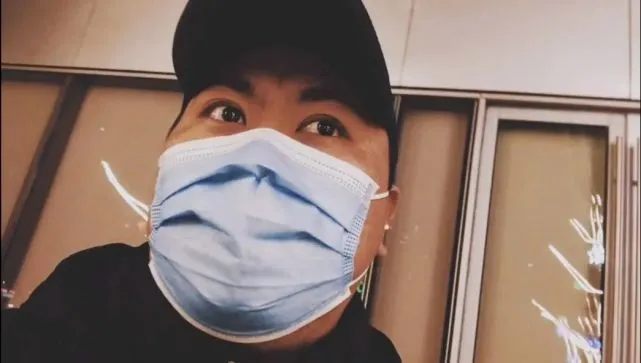在西杜兰村,你所看见的职业都与城市的运转紧密相关——快递装卸工、外卖员、保洁员、手机配件售货员、机场地勤、搬家工人,他们没有选择,大多需要密集接触流动人群,为城市的各个角落送上外卖和快递,搭载乘客前往各种目的地,他们为城市的流动做出了贡献,如今却要承受流动的代价。工作总不长久,很多人会一天赶两份工,甚至更多。
撰文丨荆欣雨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你只能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
顺义的西杜兰村不大,如果你试图步行的话,那么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一圈。在那些砖色或水泥色的房子里,住着4600多名居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打工者。每天早晨6点,他们陆续地走出村子。外卖员白晓光是其中的一员,他不吃早饭就开始接第一单,晚上则工作到接不到单为止,通常是22点多,甚至是23点。他的一个室友在物流园上夜班,他们几乎碰不到面——早上他上工,室友下班归来,晚上他收工时,室友已离开了。
最近半年,这两种职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上了新闻:出现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的确诊病例行程轨迹中。2020年6月的那场从新发地扩散开来的疫情中,一名外卖员确诊,流调显示他每日7时至21时工作,每天平均接50单左右,下班骑电动车接妻子回家。12月底顺义的疫情中,一位王姓患者在12号到19号期间,白天在贸易公司工作,晚上到顺丰大件中转场兼职开叉车。12月20日的上午10点,他陪出院不久的妻子去医院复诊,当天晚上,他再次前往中转场兼职。21号,妻子也加入了兼职,从晚上22时工作到凌晨2时。短短数行的公告中透露着难以喘息的疲惫。
2021年1月3日下午,北京顺义区一采样点,居民正排队参与核酸检测 ©视觉中国
在西杜兰村,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当下的生活。12月26日凌晨三点,村子封了——前一天的核酸检测中,西杜兰村有4人结果呈阳性,包括那对在顺丰上夜班的夫妻——白晓光和室友难得地陷入无所事事之中。同样情况的还有屋里的其他10位工友,他们共同租住在一间120平米的出租屋内。白晓光睡的那张1.5米的床一面顶着墙,两面被紧挨着的屏风包围,一面抵着张桌子,上面摆着插排和热水壶。房间昏暗,属于他的私人物品不过是些随身衣物和一床被子。
由于工作换得勤,他基本上每隔一年就要换到离工作地更近的住所。他的室友们也是这样来来走走,西杜兰村的另一个打工者说,“有些人刚脸熟就走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疫情让生活变得更不牢靠了——因为封村,白晓光和室友们有时间聊一聊,一交流,发现2020年都没挣什么钱。复工就比往年晚,“怕出去之后危险,也给国家添麻烦”,回到北京,隔离,找新的工作,“可能人家不招人,或者没复工,就在这个地儿工作两天,那个地儿工作两天。”每个工作都需要重新适应,“换工作也不好换,临时工通常还要核酸检测等等证明,反正今年就比较费劲。”年底刚安定下来,大家都攒了一股劲好好干,结了房租回家看孩子,病毒席卷重来,又是隔离,无法复工。
封村后的西杜兰村
在西杜兰村,你所看见的职业都与城市的运转地紧密相关——快递装卸工、卖煎饼果子的小贩、保洁员、手机配件售货员、机场勤、搬家工人,他们没有选择,大多需要密集接触流动人群,他们为城市的流动做出了贡献,如今却要承受流动的代价。工作总不长久,很多人会一天赶两份工,甚至更多。那位赶两份工的王姓患者不会让西杜兰村感到稀奇。
在知乎上,曾有很多人提问,自己背负了债务或即将交不起下学期的学费,该不该去中转场上夜班?底下的回复全都是“不要”,“这个不是你有心理准备就能承受得了的。”这是一份被称为需要“干一天休三天”的工作,但那位王姓患者曾经连续工作了10天。
快递行业白天的工作是收件和派件,每天下午5、6点钟,货车从营业部出发,抵达中转场时通常是晚上6、7点钟,甚至更晚。第二天早晨6点之前,货车要重新出发,前往下一站。发生在这中间的就是那些夜班打工者的工作:扫描、分拣、装卸。那里白天一片寂静,晚上灯火通明,传送带巨大的轰鸣声,组长或队长吼员工的声音,还有货车倒车的声音,构成了中转场的喧闹。夏天,气温达到30度以上,通风机聊胜于无,喝的水都变成了汗,难闻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冬天,曾兼职过一天的小红记得中转场空旷、漏风,“非常冷,要穿着羽绒服干活。”
无论具体从事哪种工作,本质上都是重复,你只能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王姓患者的叉车工作技术含量更高,每小时时薪会高8-10元。白晓光室友所从事的装卸则是纯粹的体力活:人被困在几平方米的货车里,把传送带送来的物品尽量节约空间地摆好。(在大件中转场,30公斤以上的快递很常见)如果想偷会儿懒上个厕所,回来后快递会堆得像小山一样,甚至迫使传送带停止运转,队长开始大声地责骂。这里的人来来去去轮换不停。冬哥是北京一家快递公司中转场的外包劳务公司的带班队长,即便脾气不好,他也牢记不要轻易对熟脸说重话这条准则,“尽量能留住就留住吧。”而在成都中转场做过管理的张强记得,“一批兼职的工人,今天看到了,明天也看到了,后天来的全是生面孔。”
午夜时分会有一顿饭,10分钟吃完,回来继续干活。后半夜是最难熬的,黑夜仿佛永远不会结束,手被麻袋或箱子边缘划破了,肩膀酸疼,腰像要断了一样,大腿失去知觉,人的意志会被摧垮。张强记得,清晨放工时,工人们脸上的表情像刚放学的小学生。中介拿走约30%后,累到精疲力尽的一夜值两百多块钱。
第二天,他还是照常出工了
对顺义的很多打工者来说,为了更多收入,在本来的工作之外再从事一份兼职并不稀奇。白晓光曾同时做两个公司的保安——第一份从早8到晚8,正式员工,下班后留一个小时吃饭换衣,晚9点到12点在另一栋大厦做兼职保安。两份工作加一起每个月能赚七八千,自己留1000出头,剩下的都打给在河北衡水的妻子。
同样住在西杜兰村的郑夏鹏本来有一份算得上稳定的工作,在建筑外装公司从事营销,工资可以达到一万块钱左右。4月份,建筑行业行情不好,大量尾款收不回来,公司要求员工每月到岗7天,发放半薪。为了补贴家用,他找了一份口罩工厂的兼职,每天160元。
他今年30岁,长着一张朴实的脸,和妻子租住一间15平米左右的开间,房租每月1000。口罩厂早上6点半上班,公交车还没运行,他就4点半起床,5点出发,步行一个小时去上班。走在天刚微微亮的马路上,他的身后不停有大货车驶过,他录了条视频,对自己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美好的一天从加油开始!”
郑夏鹏去口罩工厂打工的路上
第一天,他负责剪掉口罩的毛边,两个小时后,用剪刀的右手已然发红发胀,有其他工友手上起了两个大泡。中午吃饭时,他用疼痛的手拿起手机,总感觉手机好像歪掉了。下午2点半收工,他剪了1310只口罩,没有达到绩效要求,有些熟练的工人能剪4000多只。监工警告他,他剪坏了不少口罩,如果上报,他还要赔一笔不少的钱。第二天,他被分配去给口罩贴logo和装箱。同样是不断重复的工作。他和小组的其他人一天装了200多箱,最后被告知每个人要分别计件。当天晚上,他在微信群里被通知开除了,工厂给他结了320元工资。
他又去面试京东的酒类分拣工作,计件算钱,一件8分5,如果打碎了酒水,还要赔偿,他想了想,没有去。短暂的兼职生活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未来绝不能靠体力工作过活。6月,公司全面复工,但至今没有发过工资。
他是个对生活充满乐观精神的小伙子,在电话里用轻松的语气谈论着“7个月没有工资”这件事,他妻子所在的留学公司同样生意惨淡,也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北京的房价高不可攀,他们去年在天津贷款买了房子,这是给未来的孩子做打算,“尽量把孩子的起点稍微往高提一提。”房贷每月一万左右,今年主要靠借钱还,“我们当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读过大学,对未来的生活充满野心,毕业后只管家里要过2000块钱,以前他是建筑技术工人,但他认为技工的上限很低,做营销尽管当下的收入少些,但可以经常跟大公司的人打交道,可以学到更多知识,他相信这些东西在未来会派上用场——尽管现在他还说不清到底有什么用。
白晓光
仅读过高中的白晓光选择就没那么多了。10月,晚班的那份保安工作不再招聘兼职人员,他索性把第一份也辞了。看到有工友一个月能赚9000块钱,他也把目标定在这个数。听人说送外卖赚得多,就干起了外卖,每天早上6点出门,不吃早饭直接开始送,送到晚上接不到单为止。11月,有个小区突然不让电瓶车进了,那天他有15份左右的订单要送,无奈之下,他只能拎着外卖跑步送,“送完之后手脚都酸了,动不了了。就想着以后再也不送了,对,就感觉绝对不能送外卖了,太累了。”但是第二天,他还是照常出工了。
迄今为止,送外卖的两个月收入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来北京8年了,他做过餐厅服务员、大堂经理、交通协管员、热轧厂计件工,9000块钱看起来还是那么得遥远。他最近听别人说,有个工作叫古建筑装修,就是在公园里给仿古建筑贴贴砖瓦,收入可以达到9000块,他想着解封后或许可以试试。我是在一个短视频应用上找到他的,封村期间,身边的朋友告诉他,拍短视频转化率高的话,可以有些收入,他就注册了账号偶尔拍拍,“也没什么钱,一毛两毛的。”
打工者李志博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幸运的。他是搬家的临时工,主要业务是为要移民国外的人们打包家具,报酬也相对多些,8小时可以赚300元,加班每小时40元,一个月能有八九千。今年,这样的活很少了,他只能接一些办公室的搬迁工作,一个月只有7000左右。但为这群人搬家最大的福利是,雇主会在干完活后给他们点一份还不错的外卖,他记得最好的一次,有红烧肉吃。
他给村口的一位保安送去了两箱泡面
截止到今天,顺义区已有6个村庄被市疾控中心评估为中风险地区。在短视频软件上搜索这些村庄的名字,能看到不少打工者们拍下自己几平米见方、背景通常很杂乱的屋子,有位东马各庄的男人喜欢躺在床上对着镜头来一段,他写,“今年白干了一年,还好人活着,挣不挣钱就不说了。”一位东海洪村的女士拍下了核酸检测的现场,她说自己想家了,“今年太难了,让人挣点钱买馍馍吃吧。”在西杜兰村将近500人的生活物资团购群里,人们会在买菜间隙感叹两句,“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下面有人回复,“难兄难弟我们都会更好的,我们经历了一样的,加油。”
人们一再放低对生活的期待,“现在这个年头你看看干什么也不容易,稳当当的、平平安安的就不错,没有需求那么多”,李志博说。郑夏鹏一直想要个孩子,今年的种种状况让他退却了,父母上年纪了,工资发不出,房贷还不上,7月份妻子还住院切除了卵巢里的畸胎瘤,由于疫情,医院不允许陪床,他只能让妻子独自去医院。
他们用视频记录下了入院前夜的分别,妻子把卫生纸、水杯和换洗的衣服装进黑色的背包,郑夏鹏对着镜头,有些不安,“医生既然不允许陪床,那说明手术的风险一定很小。”他问妻子,害怕吗,妻子摇摇头,用玩笑化解紧张的情绪,“要那老爷们没啥用哈哈哈”那段时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能相互扶持走下去的也就是我们俩了。”
“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什么心情?”
十一假期,他回老家张家口帮父母收割玉米,家里二十多亩地,大部分用机器收,有七八亩散地要靠人工掰。前些天,父亲打来电话,说今年玉米的价格不错,九毛多出手了,卖了三万多,问他,要给他打点钱吗?尽管已经7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他还是拒绝了。
被困在家中的当下,他们的愿望更简单了:填饱肚子。郑夏鹏和妻子在村里超市关闭前囤了些洋葱、冬瓜、红薯、白菜,“没有肉吗?”我问,“我俩对肉还好,不太喜欢”,他回答。白晓光的室友在超市买了三箱泡面,这构成了他们隔离期的伙食,要精打细算着来,“如果一天只吃一顿就煮三袋,吃两顿就每顿两袋。”他家的暖气温度在十度左右,电褥子耗电大,他很少舍得开。
12月31号晚上,李志博决定,跨年得吃点好的,他团购了点猪肉,跟土豆一起炖了,又炒了个鸡蛋,整了一两老村长,“不喝醉”。吃过饭,他在视频网站上随便找了个晚会看,又给妻子打了个视频,打着打着累了,就睡下了。郑夏鹏囤的粮食快吃完了,家里的温度计显示16.3度,他和妻子都穿着羽绒服。年末最后一天的中午,两人煮了清汤面条吃,没有蔬菜和鸡蛋。晚上,他们用一锅红薯粥迎接了新年。
在困境中,他们仍能体谅他人。58同城上一位南法信镇的打工者拒绝了我们进一步访谈的邀约,但他在回复中写道,“我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还好,是阳性或者是密切接触者的,也是一种无辜。”郑夏鹏订了5斤香蕉,3斤橘子,香蕉送来的时候都黑了,他强调,“工作人员挺辛苦的,可能就是货积压得太多了。”
李志博希望我们可以帮他打听下,如何才能给帮他们看守村庄的保安们捐点钱,“我们在屋里还有暖气呢,舒服的时候人家还在外面为我们执勤。咱们在外面打工嘛,本来就不容易,我感觉他们(也)挺辛苦的。有什么电话吗?还是直接用现金捐,或者买点物资。”第二天,他给村口的一位保安送去了两箱泡面。
不管怎么说,新的一年总算是来临了。1号一大早,西杜兰村给每家每户发了水饺和汤圆,“总算有肉吃了”,郑夏鹏感慨,他煮了两袋猪肉荠菜的饺子,感觉像过农历年了一样,“这个饺子吃的比任何时候都有感觉。”3号,村里又给每人下发了300元代金券,解封后可以去指定地点领取现金。以前每年元旦,郑夏鹏和妻子都会去雍和宫祈福,今年他们只能待在家里,妻子的新年愿望是公司拖欠的工资可以尽快发下来,他希望新年多赚点,生活稳定下来了,就要个孩子。
郑夏鹏和妻子在吃村里发的饺子
8岁的儿子是李志博的精神寄托。以前打电话,儿子总是吵着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慢慢地,提问变成了,爸爸干完活了吗?“感觉孩子就长大了,”他说。他讲起2018年的暑假,妻子带着儿子来北京看他,他们去海洋馆看了海豚表演,儿子兴奋地跟海豚拍了很多照片。那天晚上他们没回西杜兰村,而是在附近找个200块钱的旅馆住下了。第二天,他们去颐和园划船,儿子又快乐地玩起了水,这些构成了他在北京拥有的闪亮记忆。
李志博的新年愿望是希望老婆和孩子平平安安的,(世界)不要再闹新冠病毒了。白晓光通过短视频发布了年终总结:“今年也比较悲催,除了疫情,就是疫情,天天的也没有个正经的工作。其实我在想明年不在北京了,在老家要么找份工作,要么自个呢折腾点啥。”随即他又想到,老家的薪资并不高,做小本生意客流量又不行,“比较头疼”。最后,他鼓励自己,“明年疫情一过,加油吧!”
1月1日下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呼吁顺义居民非必要不出顺义,在顺义过年,看到这条消息,郑夏鹏仍带着特有的幽默,表示想送给自己一首《凉凉》。而李志博则充满感伤,他清楚,如果真回家了,搞不好还要去酒店隔离,大几千块钱又没了,他愿意响应政府的号召,只是“我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给老婆孩子说”。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封面图来自视觉中国。邢逸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