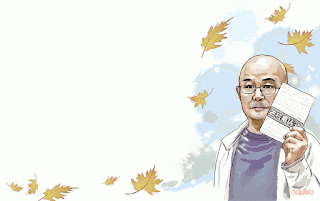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5日
你總嫌我的詩句太長
而現在,命運卻把你的兒子
壓縮成一個短句
這個短句還在被刪減
直到只剩下一堆皮囊
一個面目全非的強姦過的詞
我已經老了
看上去比你還老
當我有一天重歸故里
這顆禿頭還習慣當眾叫「媽媽」麼
我是否有力氣去感受愛
接納
太輕柔的風?
--廖亦武一九九一年三月獄中
她把一本薄薄的冊子借給我,放在一個信封袋裏。冊子是最簡陋的印刷,暗黃的紙,小小的鉛字。《古拉格情歌》,是這名叫亞縮的人在獄中寫的。他將短詩和書信藏入一本《三國演義》的書脊,趁手工勞動時,用漿糊封好。他說是上帝在保佑它。他出獄後幾經輾轉,還是找到了這本書。
那舊稿上的字體小得如針尖,如微塵,用放大鏡也看不清。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他用竹籤沾着紫藥水寫這些細密的字,打發獄中的孤獨與苦痛,並提醒自己絕不屈服。
這名叫亞縮的人就是廖亦武。
他在德國獲獎的消息,大陸被封鎖得結結實實,那篇演講,在微博上每有人發出來,官方便在一秒內刪除。他們特別害怕他,一如以往地怕他。從前不讓他走,他成功脫逃了,遠在德國,仍然是心頭刺。
一個人在五十歲的時候離開故土且心知永不能回是甚麼滋味呢?只有那夜幕下逃命疾奔不得回頭的人才知道,在經年的恐嚇、凌辱、打壓之下,不得寫不得說不得自由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種不得已的決心,連回頭都不可能。一回頭就是經年的舊事撕扯着心。
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兩種現實裏。他們全靠着回憶和書寫才讓人們得知有另一個世界。
作家野夫在四川鄉間度假,回憶着老廖出走那年。「他從成都匆匆到大理,打電話給我讓我也趕去大理,電話裏並沒說甚麼。我趕去的時候他已是失蹤了。他的女友也不知他下落。後來才得知他是從中越海關走的,是拿着護照正常出關的,算不得偷渡。他當時只是想試一試,所以沒有告訴任何人。」
廖的處境要比其他異見作家更難。省市的地方警界遠比北京更要嚴苛,為了不出意外,格外要對這些人施壓。事實上廖出獄後沒有做過激進的事情,除了寫書,便只有走訪朋友或是新書發佈,卻常常是中途被取消驅散了的。
借給我書的女人,是廖曾愛過的人。他們在十年前相識,有過徹夜的長談。她回憶廖拿出從不離身的長簫,在冷寂的夜裏吹奏給她聽,中間伴着唱和,聽的人,吹的人,所有的悲苦都會從身體裏向外湧,變成眼淚。
他去她家中做客,她在家中備簡單飯菜,弄得鍋盆狼籍,他一挽袖子做起了主廚,做飯對四川人來說太駕輕就熟了。他喜歡給別人做飯吃。他想過平穩的人生,不用心驚肉跳,不用在深夜裏蹣跚,不用吹着簫去四處尋找家園。她的家那麼溫馨,安全,她那麼柔美溫婉。那晚他沒走,睡在沙發上。
第二天臨別,他贈她這本小詩冊和《中國底層訪談錄》上下冊。他去採訪,說好再見面,「我不要只和你做知心的朋友,我想和我愛的人能一起生活,能摸到她的頭髮」。
見面那天他沒來,很久都杳無音訊。後來她得知當天他在去採訪的路上被蒙面押走。
再見到,他臉上沒有了神采,她形容是「驚人的萎頓」。「那麼陌生,冷感,和從前判若兩人」。
「他冷冷地告訴我,他不會再見我了。又說,因為愛你,所以要遠離你。」她靜靜回憶着某年某月這個人和她說的話,這些年她從未向任何人提及這段事,從沒向任何人提過廖的名字。
「他看着我的眼睛說,我希望你去過我不能過的生活。你應該永遠像現在這樣,穿得漂亮,去咖啡館,見任何朋友,過平安的生活。」他已經被剝奪了這樣的權利。
他在麗江住過一段日子,找個久無人居的荒院子,撿些桌椅,開了個沒有名字的酒吧,來往的皆是各路牛鬼蛇神,根本賺不到錢。養隻小狗和他相依為命,他吃雜糧,狗也跟着吃起素。
老廖又帶着狗乘車去大理,在南門外小院住下,月租四百五十元。他來和他的兄弟野夫相會,兩個光頭,一隻小狗。夜半的簫聲如鬼泣。
他的戶口一直在四川涪陵,他去申請護照,總被駁回:出國可能威脅國家安全。他每年申請一次,已是十幾年,當成一個行為藝術來做了。直到二○○八年四川地震時,廖才能趁亂辦到一本護照。這是天賜給人自由的機會。
野夫取得德國文學基金的贊助,會在柏林生活一年。他能和他的兄弟再見面,「除了在中國,可能我們在哪兒都能遇見。」廖在德國能順利拿版稅和金獎,又是大學的駐校學者。離亂一生,終得安寧,只是失去了故園。這種失去,不是因戰亂。看似太平的世界,人心卻失去了故園。「我相信他走到哪兒都能寫。我們這代人,野蠻生長的經歷,一輩子也寫不完。」
那本一九九九年的詩冊裏開篇這樣寫着:是的,許多人都死了,我們還活着,並且還將繼續活下去,活到底。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