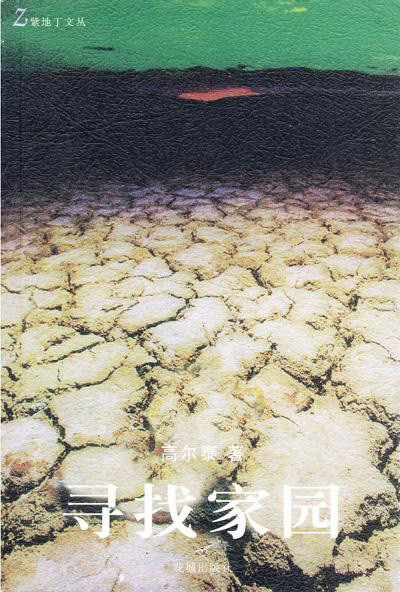1951年新春,翻译家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邀请他回国任教,巫中断在美攻读博士。同学李政道前来送行。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1957年打成右派,同年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巫1991年选择定居美国,出版《一滴泪》,讲述文革受难史,轰动西方世界。
上海即将失守,王鼎钧父亲的朋友说“国民党坏,共产党坏,何必跟失败者”。王父问王的意见,王鼎钧答“已经知道国民党有多坏,能应付。但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坏,估计应付不了。”后来,王鼎钧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又在51岁时移居美国,学术成就颇丰。
……
这类以人生选择为主题的真实故事,因为特定时代的因素,被后人挖掘出来许多篇章,很多内容其实如果不去看当事人姓名,剧情甚至都是如出一辙。历史的悲歌,因其真实性和相关性而永不磨灭。
今天分享媒体人苏更生的一篇文章,这是他在读过知名画家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一书后写的书评,与上面那些个故事相仿,在历经反右、文革等磨难之后,高尔泰先生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国,并在美国完成了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字著作《寻找家园》。
以下,是苏更生的书评正文:
在高尔泰一生数次逃离死亡之后,他已是一位老人,回到家乡之时,家破人亡,活着的姐姐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他那就是在1958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高尔泰父亲的凶手。他望着那个老人,在阳光照射之下,老人一动不动,可能已经睡着了 ,高尔泰看不清楚帽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摊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的枯瘦如柴的手。就在那一刻,高尔泰一下子失去了几十年来的人生支柱,那就是仇恨,浸透着血和泪的仇恨。
高尔泰是画家,1957年,年仅23岁,因发表《论美》一文被打成右派送往夹边沟劳改。5年后,劳改结束,逃出流放之地的高尔泰渴望安宁,一头扎到西北沙漠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绘画研究,在暂获休憩之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边陲之地又成了“揪斗分子”,一斗就斗了6年。之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了5年,1977年,终获自由身,调至兰州大学哲学任教授。
一段数百字的苦难履历表背后,是20年的时光,他由郁勃而有生气的少年成了沉痛的中年人。他在数度被劳改、揪斗、改造之时,他的父亲在大跃进时,因被打成“地富反坏右”,被虐待致死,母亲前去收尸时,父亲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在临死之前,父亲正在毒日头底下背砖头,从跳板上跌下来。母亲抱着父亲的尸体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被批斗;妻子在劳动改造中去世,留下几岁的女儿。此后,高尔泰带着女儿,在兰州大学、社科院、四川大学辗转漂泊,执教为生。
1986年,女儿19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因为“反自由化”运动,有人整理了高尔泰的资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南开大学因为录取了他的女儿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取消了女儿的名额。女儿坚持要去上去,打包好行李,在开学的前几天失踪,高尔泰在车站找到女儿时,她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往医院检查,确诊为精神分裂。几年后失踪,在郊外的树林中发现尸体。
这本《寻找家园》中所写的,正是高尔泰一生的飘零。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鲜少窥见怒意,在深重的苦难之间,高尔泰好像并不愤怒。有人称赞高尔泰学会了宽容和妥协,高尔泰解释,这只是误解。他说,宽容和妥协是强者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来的。是在无穷的漂泊中所体验倒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都让他涤除了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地观察和书写。
在《寻找家园》中,对苦难的申诉变成冷静的对人生的书写,甚至有一丝滑稽。在夹边沟劳改时,高尔泰和一干劳改分子要在盐碱地里挖沟,日出之前出工,日落之后收工,狂风呼啸,时间消逝,日复一日。被监工羞辱和殴打不算什么,他吃不饱,每天的早饭和晚饭是一样的,白菜和萝卜煮熟之后,掺和进包谷面搅拌而成的糊糊,很稀。大家吃完自己的糊糊,就到桶里去刮桶壁上薄薄的一层,起先是轮流刮,后来抢着刮,把饭桶倾侧过来,用铝勺刮,刮下来的汤汁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一并吃掉,吃完了还是饿,就出门上工了。
一日,高尔泰出工时,发现远处有一棵沙枣树,他眼睛一亮,在收工的时候故意掉在队伍后面,等队伍走远了,猫着腰,朝沙枣树偷偷跑去,他写道:“虽然猫着腰,远处队伍里只要有人回头望,也还是有可能发现我的。”好在并没有人发现他,他跑到沙枣树旁,树上果实无多,但足够他吃,他边采边吃,把沙枣塞进棉衣的破洞里,装了许多,然后往回跑,边跑边吃。但队伍已经走远,天色渐暗,他在戈壁中迷路了,他安慰自己不要着急,迷路的时间很短,后来顺着盐碱地里挖出的沟,悄悄跟上了队伍,他在夜色中小跑,快到场部的时候,终于追上了,一下倒在地上,人们把他抬了进去,醒的时候,身上的沙枣散在铺位上,被工友抢着吃。他想着他跑回来的时候,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在夹边沟的日子并非只是劳动改造,还需要面对各种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工友之间的相互举报。一次,场部连夜搭造了一个篮球场,因为有参观团来参观。在参观团之前,白天加强相互监督学习,晚上加强揭发批判,谁谁谁老是吊着个哭丧脸:你是对谁不满?谁谁谁一天到晚闷声不吭:你打的什么鬼算盘⋯⋯这样互相揭来揭去,大家都有共识,原来所有人的思想都没有改造好。要求风气立即改变。
于是在工地上,每个人都在微笑,随时随地都在微笑,眼睛眯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开着两角向上翘,就是微笑。工人们,笑着抡镐,笑着使锹,笑着抬筐跑上坡跑下坡。高尔泰也笑着,他写道:“我假想有一个不知就里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对这种独特的景观,一定会惊骇得张大嘴,半天也合不拢来⋯⋯我又想,假如这时发生地震,我们全部都突然埋进地下原样变成化石,异代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不能解释,这举世无双的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高尔泰在敦煌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安排打扫敦煌石头洞,在大大小小的洞中扫灰,他喜欢扫灰,躲在四面都是墙壁中获得片刻安宁。只是可惜天黑之后,他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的鬼魂,互相撕扯咬啃。
高尔泰所记录的生活,沉痛的苦难混合着滑稽、不易求得的片刻宁静、边陲之地的美景、所遭遇的人事之间的罪恶。他并不明白,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一生要被那些不爱他们,不理解他们的人在顷刻之间决定,为什么?他不服气,不论是在劳改或揪斗中,他始终不服气,没有片刻臣服于教条和权威而失去人的尊严。他只想在天地间舒展四肢,大写一个“人”字,获得应有的尊严。这或许也就是为何有人能在铺天盖地的斗争中求得自保而高尔泰始终被批判斗争的部分原因。他不服气,他渴望生而为人即有尊严。他是一个痴人,一寸山河一寸血,他却痴心一片写剩山。
在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高尔泰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始终善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几个牛鬼蛇神被送到荒山中垦地,粮食不足,想抓点动物吃。他们在山里放了捕羊的铁夹。高尔泰去看的时候,上面有一只黄羊的断腿,羊跑了。他和一个同行的厨师顺着地上留下的足迹追,发现了黄羊,黄羊一直在跑,高尔泰慢慢跟上了它。他写道:“我慢慢跟着它走。这个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对任何其他动物都毫无恶意、毫无危害的动物,惟一的自卫能力就是逃跑。但现在它跑不掉了⋯⋯全身躺在地上,血不断渗入沙土。后半身血肉狼籍,可前半身毛色清洁明亮,闪着绸缎一般的光泽。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高尔泰楞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同行的厨师跑上来,满脸放光,赞叹黄羊真大,扑上去把羊的四条腿——包括那条断腿——捆起来,把杠子穿进去,准备抬走。高尔泰坐在地上,抽了根烟,然后和厨师抬着羊下山回去。路上羊发出奇怪而悲惨的叫声,高尔泰放下杠子,让厨师把羊宰了再抬回去,厨师不同意,因为气温在零度以下,宰了抬回去会冻硬,硬了再化开不好吃。高尔泰生气地说:“它痛得很呢!”
正是这种人性中的善良更让人沉痛,他历尽苦难,还对一只垂死的黄羊有情,对同时受苦的人有义,但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这种在扭曲的人性,无边的苦难之间的泛着光的善良让人难以忍受。这是一本好书,但我无意赞美它是一本好书,由苦难练就文字不值得,因为我无意赞美苦难,无意赞美在无穷的残忍的愚蠢的苦难中所获得的美,这是罪过,这种美在罪过之前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