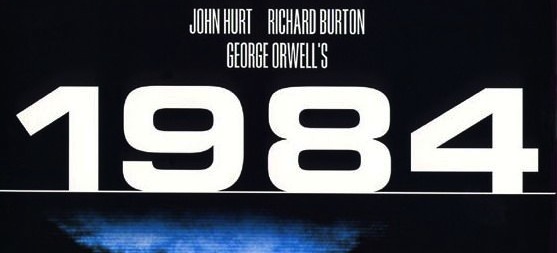奥威尔(1903.6.25-1950.1.21)生于英国殖民地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民众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社会的特点:等级森严,弱肉强食,鞭子教育,强制统一,敌视智力。(奥威尔晚年回忆《如此欢乐童年》)
后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作为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本可以享受随意处罚异国囚犯的特权,却无法忍受他人的呻吟,良心不安,毅然拒绝为“祖国”服务,辞职。
离开缅甸之后,他到巴黎流浪,做酒店洗碗工,书店兼职店员等底层工作。在酒店,每天工作达十三个小时,被迫剃掉自己的短髭,因为对于管理者,那是不服从的刺眼标志。后进伦敦收容所,生活贫困交加,长年穿着肘部有补丁的外套和旧裤子。他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底层的不幸生活,精神上的空洞与绝望,最终完成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
20世纪30年代,参加西班牙内战。因为苏联迅速介入,使之成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战场,其政策越来越充分暴露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性质,充满暴力、欺骗与阴谋。斯大林将镇压“托洛茨基派”开始的肃反经验运用到西班牙等国,动用秘密警察,清洗不同政见党派与个人。逮捕持续数月,肆意蔓延,马统工党成员,家人,包括孩子,残疾人,凡有联系和接触过的人,探监的人,都不断成为“托洛茨基分子”而被捕,无辜者如同动物那样被肉体消灭。专制权力支配一切,个人权利不值一提。
奥威尔冒着生命危险为马统工党辩护,结果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遭到追杀。为了营救一位被捕者,已经拿到遣散证的奥威尔,不顾个人安危,在杀机重重的作战局和警察总局之间奔走。便衣警察在午夜闯入奥威尔的旅舍,搜走几乎所有东西。他侥幸与妻子逃离后,却萌生一个无人理解的念头:重返西班牙。“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还是希望能够与其他人关在一起。”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以血的事实,描述了这段如同精神病院恐怖的历史,同时宣告了自身理想主义的幻灭。奥威尔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等,他把革命看作是被压迫者的权利,是消除不公和特权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书中,他多次写到革命,为其理想氛围所迷恋。但无疑,现实的悲剧残酷地击碎了他的想象。在全世界都被斯大林所震慑和蒙蔽之时,奥威尔是最早的极少数觉醒者和批判者之一。
从西班牙回来,奥威尔变化非常明显:“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奥威尔传》)在这之后,奥威尔写下《动物庄园》和《1984》。人类的自由、平等与正义,对人类的焦灼的爱,占据了他的精神内核。假如没有与广大被压迫被欺凌的底层民众一起,假如没有西班牙内战的切身经历,这两部传世之作的诞生几乎不可能。可以说,奥威尔的一生,就是为了写这两部书。这是他的命运,他及时洞察之,并承担之。
在动笔之前的较早日子,他就有这样的洞见:“我们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真正的作家比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都更敏锐。可以说,在揭露极权主义方面,《动物庄园》和《1984》的深广度,超过了相关的理论性作品。
“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它们,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我为何写作》)
“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任何一个意识到自由意义的作家,甚至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背弃政治。关心政治是一种极其稀有的情感,因为,政治不是观念,而是现实。政治不仅仅是可见宏大的革命和暴力,同样是琐碎甚至不可见的压迫压抑、梦魇、退缩与自我消失。
奥威尔倾向或醉心于底层生活的直接体验,即使在变得富有的晚年,依然安于清贫,以致患重病,决然如同自寻死路一样到孤岛居住。几乎所有人都努力往上走或脱离底层,他却放弃可能的精英生活,努力“向下层突围”,自愿成为被压迫者,与他们一起抗争,总为自己脱离底层而内疚,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
他既反极权主义,也反精英主义,两者共有的对立面是相同的,就是——平等、自由、民煮与正义。这是一个有如耶稣的伟大心灵,也只有这样的心灵,才可能孕育伟大的作品。
有人将《1984》与《美丽新世界》和《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就笔者看来,后者写得一般,多少有些文艺青年气息,而随着作者流亡国外,终生再无重要作品面世。最重要的原因,与奥威尔相比,就是生活直接经验的相对溃乏。
在专制社会,小说往往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专制者从小就向孩子一再灌输“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由此,“二加二等于五”,乃至人吃人,都正常正确不过。被压迫者相互揭发,相互伤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独裁者及帮凶藏在幕后,大吃鹬蚌之肉。
无知其实是一种罪恶,它使人丧失判断力,不辨甚至颠倒是非善恶。民众为什么无知,因为这是独裁统治的需要。所以,逻辑,理性,伦理,公*民教育,人*权观念,法律常识,都是多余的。你安于命运,没有反抗,安全第一。这是一个悖论,人有追求(需要)自油的天然倾向,但专制偏不给你自油,还让你痛恨自油以及追求自油的人们。最后,沦为非人,集体平庸。
奥威尔对普通人带着某种悲观,对民众的觉醒似乎并不抱有多大希望。“危害个人自油的最凶恶的敌人,正是那些最需要自由的人(被压迫者)。公众并不在意这个事情。他们不支持迫害异端,但也不会为异端辩护。”(《对文学的阻碍》)。这或许是平庸之恶的另一种表述。其实,无知的民众同样支持迫害被专制者认为的异端,所以才有菜市口掷到谭嗣同身上的烂菜叶。
奥威尔发现,扭曲历史,编造谎言是极权的开始。极权控制与公共语言的扭曲,使自由思想和独立写作(表达)变得不合时宜,极为危险。在书本,课堂和社会,谎言渗透一切,沦为人们苟活的面具。老大哥总在看着你。只有伟大的作品,才能神秘地穿透谎言,藏在老大哥的盲点里,得以传世。
1950年的今天(1月21日),奥威尔死于困扰其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在《1984》中,每一个人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背叛了自己最亲爱的人,或言背叛了自己的初心。1989年,苏东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在世界版图上消失。
奥威尔曾说,历史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终结了。“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所发出的超越时代的预言是尖锐的报警信号。在其离去68年后的今天,苟活在动物庄园的善于选择性遗忘的人们是否依然听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