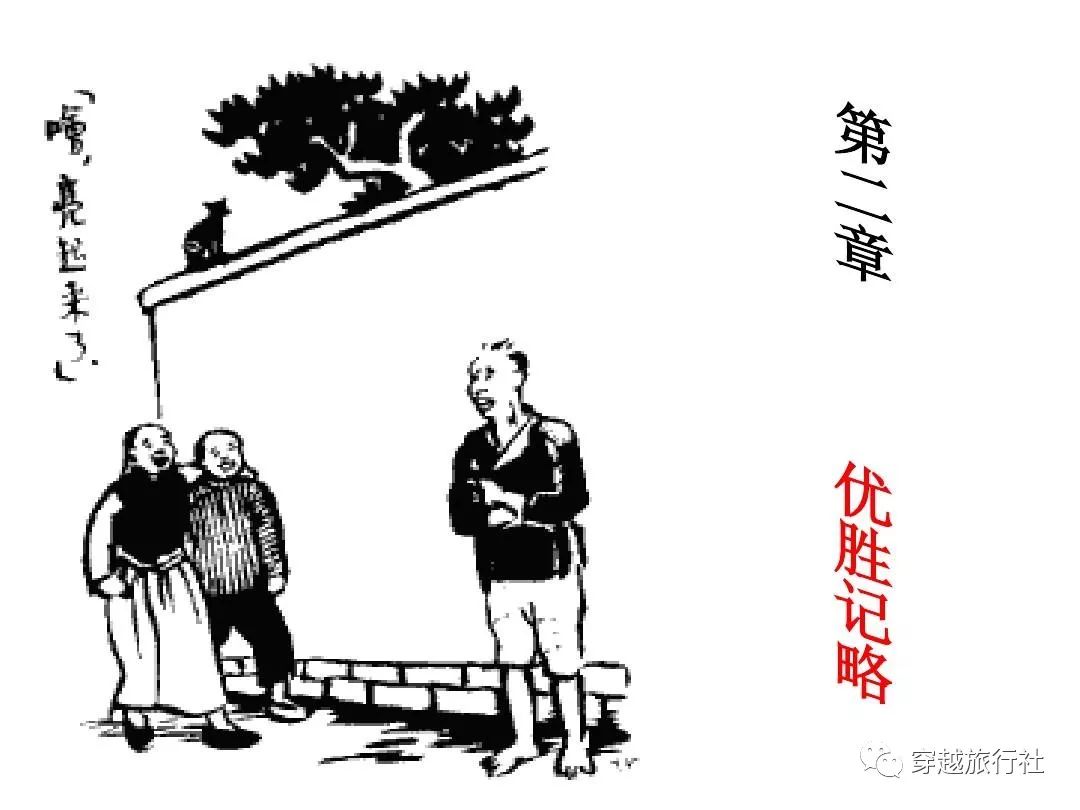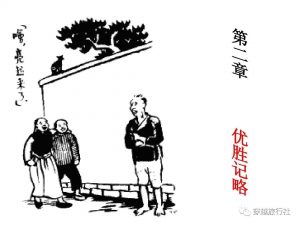“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正传》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空间|敏感词库
敏感词的历史远比网民们以为的更久远,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来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
一位叫田登的太守不允许别人直呼自己的名字,和阿Q一样避讳“灯”,一旦有人犯讳就要发飙。不少吏卒都因不小心犯忌遭到榜笞责打,整个州内只好统一把“灯”称为“火”。后来有一年过元宵节,按惯例百姓可以到州府看花灯,官府于是发布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
类似的敏感词被称为避讳,绝大多数都与人名相关。为了表示对统治者、长辈的尊重,人们不仅不能直呼他们的名字,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回避这些字,实在不得不用到的时候,就以近义词代替。这一习俗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桓公生了儿子,问大夫申繻该怎么给孩子起名,申繻讲了一通起名字的规范,“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也就是说,这些名词都是不能用于人名的,后面又说一句,“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大意是周人侍奉鬼神都要讲究避讳,名字也在避讳之列。
这种心理应当与原始禁忌相关,各民族早期都出现过类似习俗,人类学著作《金枝》指出,“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的联系,从而巫术容易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来为害于人。”
秦国的统一使避讳首次在法律层面得到明确。秦始皇名政,这个字当时通“正”,为了避他的讳,每年农历的正月就改称“端月”,《琅邪刻石》中有“端平法度,万物之纪”“端直敦忠,事业有常”两句,学者考证这两个“端”本来都应该是“正”;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楚”字也一并被禁,这就是典籍经常把楚国称为“荆国”的由来。秦朝官府甚至专门颁布了律令,要求名字中带有敏感词的百姓改名字,《岳麓秦简》就有这样一枚简:
令曰:黔首徒隶名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赀二甲。(第二个“有”应该是衍字,也就是多余的字)
大概意思是,律令规定:百姓们名字中带有“秦”字的,必须要改掉,敢有不改的,罚两套铠甲(的钱)。注意“黔首”这个词是灭六国后才出现的,所以这条律令显然是统一后颁布的。禁止用“秦”字的名字也不难理解,先秦礼制就有“不以本国为名”等规定。
不过《史记》对秦代的避讳并不严格,太史公是汉代人,没必要遵循前朝规定,与此恰成对照,他在写到本朝皇帝时明显谨慎了许多,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五任皇帝个个都需要避讳:
汉高祖名邦,《史记》但凡用“邦”字的地方,都改用“国”字,比如“相国”本来应该是“相邦”,还有观点认为,《诗经》里的《国风》本该是《邦风》。
汉惠帝名盈,《史记》一般用“满”字代替。
汉文帝名恒,用“常”字代替,比如常山本来应该是恒山,人们熟悉的“嫦娥”本来应该是“姮娥”,也是为了避同音的讳。
汉景帝名启,多以“开”字或“间”字代替,比如商纣王的叔叔微子启,在《周本纪》《宋微子世家》里都成了“微子开”。开封也本来应该是“启封”。
汉武帝名彻,所有“彻”字都被改成了“通”,秦末有个说客蒯彻,《史记》称其为蒯通,后来的《汉书》就注解,“蒯通, 范阳人也, 本与武帝同讳。”爵位“彻侯”也成了“通侯”。
再往后,汉昭帝名弗陵,“弗”被“不”取代;汉宣帝名询,汉明帝名庄,荀子、庄子因此连名字都被改了,称孙卿、严周;为了避讳汉光武帝刘秀,秀才被改为茂才,直到《阿Q正传》的时代依旧保持着这一称呼。
后面的朝代,类似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西晋建立,司马昭被追封晋文帝,几百年前的王昭君就被改了名,称王明君或明妃,比如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当时就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
唐太宗名李世民,“世”字经常被略去,王世充、徐世绩就分别被写成王充、徐绩;“民”字也都用“人”字取代,柳宗元《捕蛇者说》里有一句,“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这里的“人风”其实就是“民风”。还有三省六部制中的“户部”,之前其实是“民部”。
宋仁宗名赵祯,蒸馒头的“蒸”因此都要改为“炊”,这就是武大郎卖的炊饼的由来。
雍正帝名“胤祯”,为此他把宋朝皇帝“赵匡胤”改名为“赵匡允”,把明朝皇帝“崇祯”改为“崇正”,所以才会有《阿Q正传》里那些“白盔白甲的革命党”,“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
长辈的名字同样要避讳。众所周知,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他提到父亲时,常常称其为太史公、父、先人等,写《史记》时遇到“谈”这个字,也统一用“同”来代替,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世说新语》里也有一个小故事:桓玄有一次和王忱喝酒,酒变凉了,王忱要求手下温酒,桓玄忽然痛哭流涕起来,原因是“犯我家讳”,他的父亲是大司马桓温。最倒霉的是唐代诗人李贺,他考进士的时候,竞争者告了他黑状,说父亲叫李晋肃,“晋”和“进”同音,为避讳就不能考进士。韩愈为此特意写了《讳辩》一文为李贺说话,“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但李贺最终还是没能参加考试。
孔圣人也在避讳之列,他老人家名丘,北宋朝廷就曾下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音,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规定,凡是天下姓丘的,都要改姓“邱”,还得读成“七”。
还有一种避讳很特殊,不是为表尊敬,而是因为厌恶。安史之乱后,继位的唐肃宗对安禄山恨之入骨,把天下所有带“安”字的地名全都改了,安康改为汉阴,同安改为桐城,绥安改为广德,宝安改为东莞,安昌改为义昌等。东莞、桐城等地名因此沿用至今。
这些避讳自然给民间带来了极大不便,百姓们一不小心,动辄得咎,《唐律疏议》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写错字的代价着实不小;更糟的是,到了清代文字狱最盛行的康雍乾三朝,这种敏感词的判定已经没有章法可循,完全看皇帝的心情,著名的“清风不识字”案正是如此。雍正八年,翰林院学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雍正帝马上将其革职抄家,后来又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等诗句,雍正把“明”“清”都认定成敏感词,认为这是存心诽谤,徐骏因此以大不敬罪被判斩立决。
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文人们个个如履薄冰,只好尽量先自我审查,其心理类似于“我们自己割了吧,省得朝廷动手”。雍正后来给内阁写了一份手谕,说自己看本朝人写的书,一遇到胡、虏、夷、狄这些字,要么空着,要么用“彝”、“卤”等字来代替,他“殊不可解”,以为这是“避之以明其敬慎”。这里的“四爷”颇有些“何不食肉糜”之感,天知道他是不是在装傻白甜。
长达2000年的古典社会,已很难统计共有多少汉字在避讳之列,而且敏感词库还在不断补充增加,每一位新皇帝继位,都意味着又多了一批不能写的字。假如它们全部累积下来,汉语势必会像《1984》中的“新话”那样,词汇量越来越少,直到一个字都不能用。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些敏感词大多带有时效性,一俟前朝覆灭,曾经的避讳很快就又能恢复正常了,民间有一个关于袁世凯的传说。洪宪复辟时,袁世凯嫌元宵与“袁消”同音,下令改元宵为汤圆,没过多久复辟失败、袁世凯下台,一纸禁令自然也成了过眼云烟,等到下一个元宵节,北京各大商家重新大张旗鼓卖起了元宵。
故事是假的,“汤圆”“元宵”在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就已提到,“自初九日之后,即有软灯市,买灯吃元宵,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为果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小,即江南所称‘汤圆’也。”不过百姓们的心情,百年之后的今人仍能感同身受。
相关阅读:
中国数字空间|十九届三中全会
中国数字空间|文革
中国数字空间|昨日重现
中国数字空间|颂歌新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