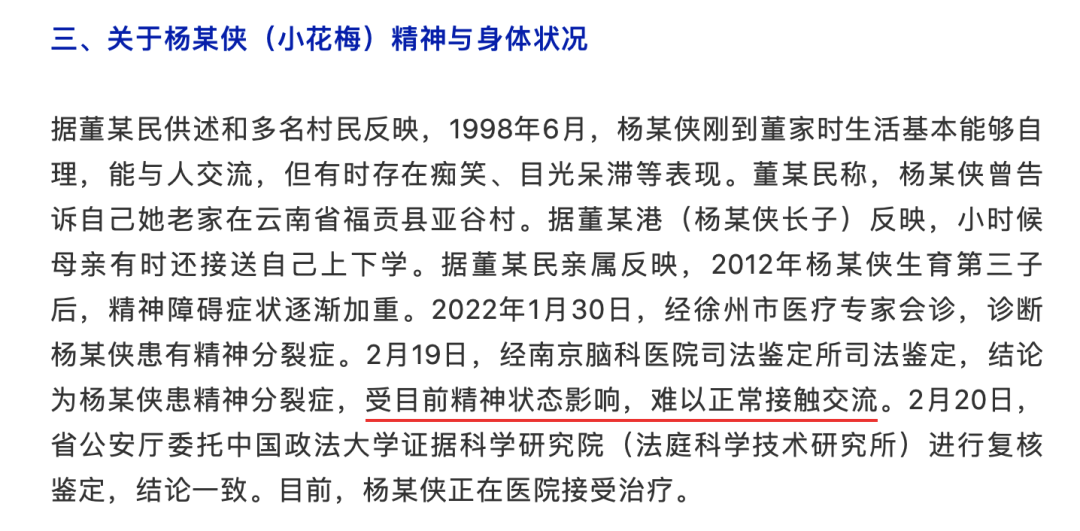作者:刘思瑶
“ 2022年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八孩事件’事件调查处理结果,遗憾的是杨某侠的声音依然缺位,文章借此契机探讨精神障碍者的话语与自主权,以期杨某侠的主体权利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与重视。”
在徐州政府四次通报都没有记载杨某侠本人的意思表达后,笔者曾期待新调查组会倾听杨某侠的声音,然而遗憾的是,新调查组仍以杨某侠“受目前精神状态影响,难以正常接触交流”为由剥夺了她的话语权。
杨某侠话语被剥夺的后果是:
第一,本次事件的调查手段仍存在不足,调查结果难免会引来争议;
第二,官方既然已认定杨某侠是被拐卖来的,那么董某民在收买过程中是否存在对杨某侠实施故意伤害、强奸等行为,需要收集杨某侠的陈述,仅单纯依靠嫌疑人的供述,很有可能会放纵犯罪。要知道,虐待罪最高量刑仅为两年有期徒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最高量刑是三年有期徒刑,而如果董某民存在多次强奸杨某侠并致使其精神障碍症状加重的,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值得追问的是,即使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她就不具备正常的沟通与表达能力吗?为此,笔者采访了从2006年以来就持续关注和推动精神障碍人群权益保护与发展的黄雪涛律师,并与其就精障有关的其他法律权益进行了探讨交流。
问:黄律师,官方表示杨某侠难以正常接触交流,但我们却在网友视频里看到杨某侠曾多次表达“这个世界不要俺了”、“屋里头都不是人”之类的话语,关于精障人士的沟通能力,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黄雪涛:我们可以感觉到杨某侠并不完全失去语言。我认为大部分受家暴的女性都有心理创伤,都不容易去表达自己的很多事情以及描述痛苦的经历,因此在沟通过程中特别需要在友好与信任的环境下进行对话。如果存在沟通障碍,那可能是因为有很多元素参合在里面,除了生理原因之外,还有比如方言的障碍、专业术语的障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翻译或者理解精障人士的人去搭起沟通的桥梁。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有没有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的时候,我们要退一步去评估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跟她沟通,有没有能力去读懂她的意思。
问:即使杨某侠具有表达能力,但由于她存在精神疾病,是否她的话就不具有可信力呢?
黄雪涛:精障人士的话语是否具有可信力取决于周围人的态度。首先是我们要给她创造表达的机会,其次是移除表达的障碍,再次是尝试聆听。很多时候她的表达并不一定要用准确的语言,即使是没有语言的人比如哑巴、婴儿,他也有自己表达的方式,只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聆听、去解读。所以我相信杨某侠是一定有意思表达的,至于说她的话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其实不取决于她的表达能力,而取决于周围人的态度,如果照顾她的人是一种认可的态度,那么就会尊重杨某侠的表达。
问:官方显示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是否意味着是一个好的开始?
黄雪涛:虽然杨某侠在精神病院里面能获得照顾,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杨某侠在精神病院里面的状态可能相较于在小黑屋里饥寒交迫的处境而言,会有一些改善,但是被医疗化管控的状态也可能是禁闭、禁锢、丧失人身自由和尊严的另一种开始。我本人之所以走进精障议题,正是因为在早些年参与解救“被精神病”人的工作。
问:虽然官方的调查工作看起来已告一段落,但杨某侠的未来发展仍值得关注,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进一步保障杨某侠的权益呢?
黄雪涛:像杨某侠这种长期在家庭环境里面受到暴力对待的女性,首先她需要离开这个暴力的环境,有个地方可以为她提供庇护,这个庇护不仅仅是提供一个住的地方,还应该包括一些心理、医疗、法律和重建她生活的经济支持,比如关于她未来的就业、和孩子的关系、丈夫的关系以及原来家庭的关系,很多复杂的生活关系都需要社会给予支持性的服务。此外在精神障碍医疗方面她也需要一些决策性的支持,比如是否需要继续接受治疗、在哪里治疗等问题方面,她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支持下作出决策,如果没有社会支持的话,她个人很难作出决策。
【笔者注:据了解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且是由其大儿子进行陪护。笔者认为由于目前不确定杨某侠的大儿子是否有参与暴力行为,以及杨某侠对其大儿子是否呈接纳态度,因此建议由家庭之外的人进行陪护,以免影响她离开暴力环境后的精神康复。】
问:目前官方认定杨某侠在到徐州前就出现言语行为异常,后被他人以看病为由拐卖,我在检索拐卖妇女罪的相关判例中,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例中被害人是精障者,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该如何预防?
黄雪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精障者成为被拐卖的对象,反映了精障社群权利的脆弱性,它比普通女性的权利更脆弱,所以对他们的保护力度应该更大,这个社会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去支持这个人群的权利保障,包括教育、医疗和生活上的支持,但是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是很不均衡的,我们将有限的资源大部分投去了精神医学界,社区的资源投入非常少,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住院治疗,你根本享受不到国家对精障领域的支持,这也导致精障人士长期不能离开精神病医院,好多人住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其实应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区里面,支持精障人群在社区里面的正常生活,我认识很多有精神障碍病史的人,他们照样结婚生孩子,和普通人一样成家立业。只要给到精障人群一些有用和良好的支持,他们就可以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问:在丰县事件中,董某民以拘禁方式对待精神病妇女,存在哪些问题?
黄雪涛:在20年前,很多家里有精神分裂的人都是这样被锁住的,因为政府认为这是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公权力基本不介入。直到2004年,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开展了“解锁行动”,让精神科医生把关在家里的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目前国家已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和资源去排查各地的精神障碍人群,那么在文明的社会或者在中国现有的政策之下,其实是不应该再发生这种精障人群还要被锁在家里的情况。
问: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精神障碍者的权益?
黄雪涛:早在2013年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就重申精神障碍者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人身自由的权利。不管是中国的宪法、民法还是刑法,都没有规定说人身自由应该以没有精神病作为前期条件,只是因为公众的歧视或刻板印象,导致长期以来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受到侵犯后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需要强调的是,精神障碍者是权利的主体,而不是人道主义保护的对象,2006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也明确提出不能因为残疾人有生理上的缺陷或疾病而导致残疾人权利的削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第一款: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第五条第二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
问:在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网友们普遍认为精障人士是不可能跟人结婚的,对此我们应如何正确看待杨某侠与董某民之间的婚姻关系?
黄雪涛:网友们这些救助性的言论是让人感动的,但其实大家还是用旧时的法律观念去质疑个案,认为精神病人的结婚行为是无效的、跟精神病女性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在中国加入残疾人权利公约之前,我们确实存在歧视性的法律规定,比如1980年代严打时期,曾有司法解释规定只要与严重的精神障碍者发生性行为,不论什么形式,一律按强奸论处。但现在国家已经废止这些法律条文了,我们也应该更新法律观点,承认精障人士也享有性自主权。在丰县事件中,如果整个中国网民还是带着歧视性的偏见和基于旧时的法律视角去讨论个案,其实是不利于精障社群发展的。
【笔者注:在认定杨某侠与董某民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判断董某民是否存在强奸行为时,应首先承认精神障碍人群与普通人一样享有婚姻自主权、性自主权,因此倾听杨某侠的陈述尤为重要,如确认杨某侠是受胁迫的,则可认定婚姻无效、董某民存在强奸行为。】
问:官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许多网友呼吁继续彻查其他类似违法事件,在您看来,如果再遇到他人对精神障碍者施暴,该如何有效处理?
黄雪涛:其实用普通的法律视角去处理就好,面对暴力的发生,我们首先要终止暴力,其次是将施暴者与受害者进行暂时隔离分开,去避免暴力的持续发生。不管是警察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当我们看到周围有人在施暴,都要去制止。当然,民众的观念取决于态度,就好比有人看到妈妈在打小孩,如果围观者认为体罚孩子很正常,那就会认为体罚是一种教育而不是暴力。在丰县事件中,锁链就是一种暴力,我们不能拿家庭关系或者精神障碍作为挡箭牌,现场看到这种情况就应该终止、隔离、分开。
问:近几年来,随着反家暴法的颁布与推广,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应该受到干预的暴力事件。那么,针对精障人群的暴力事件,是否仍会被忽视和淡化处理呢?
黄雪涛: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公权力对于家暴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但是对于精障领域的观念转变却滞后很多。对于暴力我们是一定要制止的,制止暴力无关医学话题,该追究责任的依法追究。
问:最后,您认为丰县事件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的?
黄雪涛: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主流社会看到底层存在很多的人权陷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离婚案件也是触目惊心的,很多法官明知女方是被拐卖的都不判离婚,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救济系统的缺失。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此次事件不仅仅是妇联不作为,残联也不作为,有很多问题都需要社会全方位去审视和讨论。
结语:尽管官方的调查已出,但我们的焦点不应止于确认“八孩母亲”的身份,还应将目光投向此次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更广阔、更边缘的社会议题,后续杨某侠能否得到有效的康复治疗、董某民及相关人员是否受到应有的惩罚也需要我们持续关注。正义从来不是在蓝天里自由翱翔,而是在黑夜斗争中悄然抬头。
—-完—–
作者 | 刘思瑶,深圳执业律师,主攻刑事辩护,曾成功辩护多起无罪案件,热衷研究创作,长期关注公益议题。
受访者 | 黄雪涛,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公益组织衡平机构发起人,“被精神病”公益律师,先后代理了“深圳邹宜均”、“十堰彭宝泉”等“被精神病”诉讼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