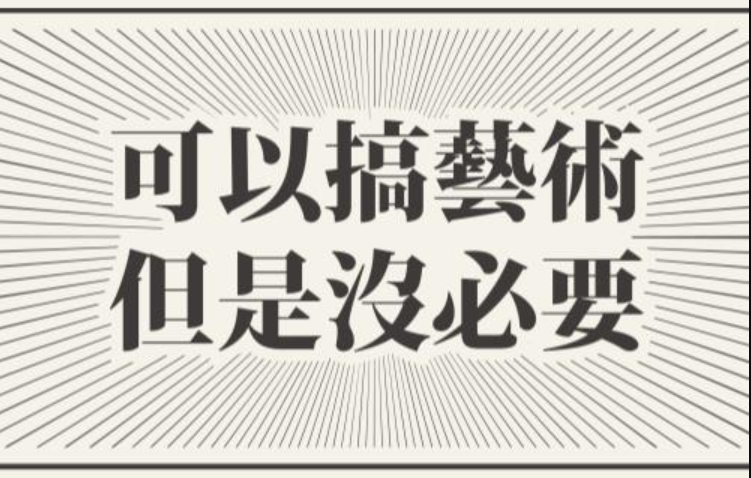日前,因举报、攻击作家莫言而一举成名的网民毛星火,得到正式答复:他对莫言的公益诉讼,将不被受理。他说,尊重相关部门的决定,但会继续起诉莫言。
不少人将他视为一个小丑,但是当然,他自我标榜为一个“说真话”并因此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并不奇怪,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一:加害者往往自视为受害者,因为这样才能占据更多道德资源。
在这件事上,值得重视的当然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莫言的沉默。这位当代著名作家,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曾被官媒盛赞“以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魄走向世界”,时隔不过十年,就被无数网民指控“通过写作抹黑中国”,近一年来甚至有很多人制作视频、写文章专门分析为什么他是汉奸,而对此,他一直保持了不同寻常的沉默。
固然,但凡了解一点当下的舆论环境就可知,沉默可能是他最恰当的回应了,毕竟在这个问题就像泥淖,做任何挣扎都注定凶险无比。不过,沉默有时是最高的不屑,有时却是无力的象征,他这样又算是什么呢?大概是“为了避免更多麻烦的忍让”?
这和自由批评是不一样的。当你的权利有足够坚实保障时,对这些喧嚣确实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因为那威胁不到你。
1931年2月9日,福克纳发表《圣殿》。评论家们摆出一副恼怒、憎恶、惊愕的姿态,对写作技巧一笔带过,大评特评福克纳对暴力和性变态的迷恋。不出几周,买《圣殿》的人比《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加在一起的人数还要多。4月底,销售量超过福克纳以前所有小说的总和。
在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下,这种批评的效果堪比广告。1960年代,美国庸俗色情小说家Jacqueline Susan经常受到严厉抨击,舆论呼吁禁止她的书出版。其丈夫(也是她的代理人)说:“每次有评论员或批评家说这是一部黄书,我们便注意到其销量大增。”当《时代》杂志谴责其黄色小说《玩偶谷》时,他说:“我们鞠躬作揖,偷偷说:多谢了!……他们唯一能伤害我们的办法就是对我们不理不睬。”
显然,在我们这里没办法这么轻松。去年6月,莫言新作《鳄鱼》出版后,遭受了大量抨击,而这些大多不是从文学性和审美的角度出发,只是挥舞着政治正确的大棒——一个不懂文学的家伙也能大言不惭地抨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想必让他们感觉良好,不仅如此,那位名人还没法还手,这就不仅可笑,甚至恐怖了。
也因此,像毛星火这样的批评者最容易遭受的质疑就是其道德真诚:有的是人嘲骂他只是借此出名,反正这样鸡蛋里挑骨头没有任何风险,左右都是赢——莫言不回应,他固然赢;如果竟然忍不住多看他一眼,那更是赚到了。
确实,这位原本籍籍无名的网民,这次算是一战成名,迅速积累了20万粉丝,推出了年费500元的VIP粉丝服务,当然还不可避免地带货了。微信群里转发这个消息时,人们都揶揄着,那意思是:“早知道这货会这样!”
这思路无非是说“你到头来还是有私心,要是你不图钱,我还敬你是条汉子”,然而,一个没有私心的毛星火才是更可怕的,试想一下,一个人出于“真诚的无知”,不图什么,就是为了口诛笔伐打倒知名作家——实际上,他那20万粉丝里,大部分恐怕就是如此,更别提网上还有大量人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
必须正视,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信念,并且正是出于这些坚定的信念在严词抨击。不仅如此,他们的攻击性常常倒是一种防御性反应,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原有的价值支柱正在摇摇欲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攻击时还会自视为受害者。
仅仅嘲讽他们有私心、愚蠢是不足以消除这一现象的,这其实源于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信念:只有那些正确、真实的信息才能被允许发布,并且由权威来发布。问题是,他们自认为是在维护心中那个清朗、干净的秩序,却没有意识到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所有人都只能闭嘴了。
我们这个社会在运作过程中,像这种浸润在传统价值观的普通人对权力是无条件信任的,而且对权力之外的其他东西都保持高度的不信任,比如文学,比如艺术,比如资本,比如宗教,甚至科技,所以才有那句得意洋洋的蠢话:“可以搞艺术,但是没必要。”
《偏见的本质》一书认为,政治性价值观就意味着对权力的兴趣,这意味着人们习惯于从等级、控制、支配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不容许有任何偏离,最狂热、偏见最强的群体将“政治性”价值观排最高,审美排最低,而最宽容的那群人则相反:
审美(aesthetic)价值观(在宽容群体中得分最高,在偏见群体中得分最低)代表着对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兴趣。它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日落、花园、交响乐或者是一种人格——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审美的态度不是分类的,每一种体验都作为独立的经验而具有内在价值。持有审美价值观的个体是个人化的。当他遇见某人时,他会将其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进行评价。由于偏见群体很少持有这一价值观,而宽容群体则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该价值,这个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说对莫言的攻击是可悲的,因为这种攻击本身证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习惯了挥舞政治性价值观的大棒来敲打文艺作品。可想而知,这样一种心态如果足够普遍,那就很难说是宽容的。
对这些狭隘的心灵来说,少几个好作家、好作品是无所谓的,当然更不会为此痛心,也不承认文艺的独立价值,因为他们是在用文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的好坏——当然,这样的声音向来不少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忍受这些人为我们选定能看什么?
艺术策展人祝羽捷前两年有段话说得很好:
我们总说审美多元,可你明显感觉到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固执的评判标准,有人觉得工业很美,有的人觉得工业无比丑陋只想躲进自然里。每个人的审美太感性了,但这个标准一定是受到当时文化、习俗、政治、社会的影响。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吕燕的照片,心里也是超级困惑,后来不断在媒体看到她的照片逐渐接受了这种美,这是与我小时候在主流媒体上接触的不一样的个性,不用靠近主流审美(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而是放大了自身的特点。
美丑都是相对的,审美的主观性也不排除身份的认同感,有些人觉得丑,并非是视觉范畴,是因为感受到了“异己”,如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文化歧视。美丑一线间,没有必须要说服别人去认同。
文学的道理亦同,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哈姆雷特》”,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但用外在于文学的政治标尺来敲打作品和作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势必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贫瘠化。
我们不应容忍这样的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