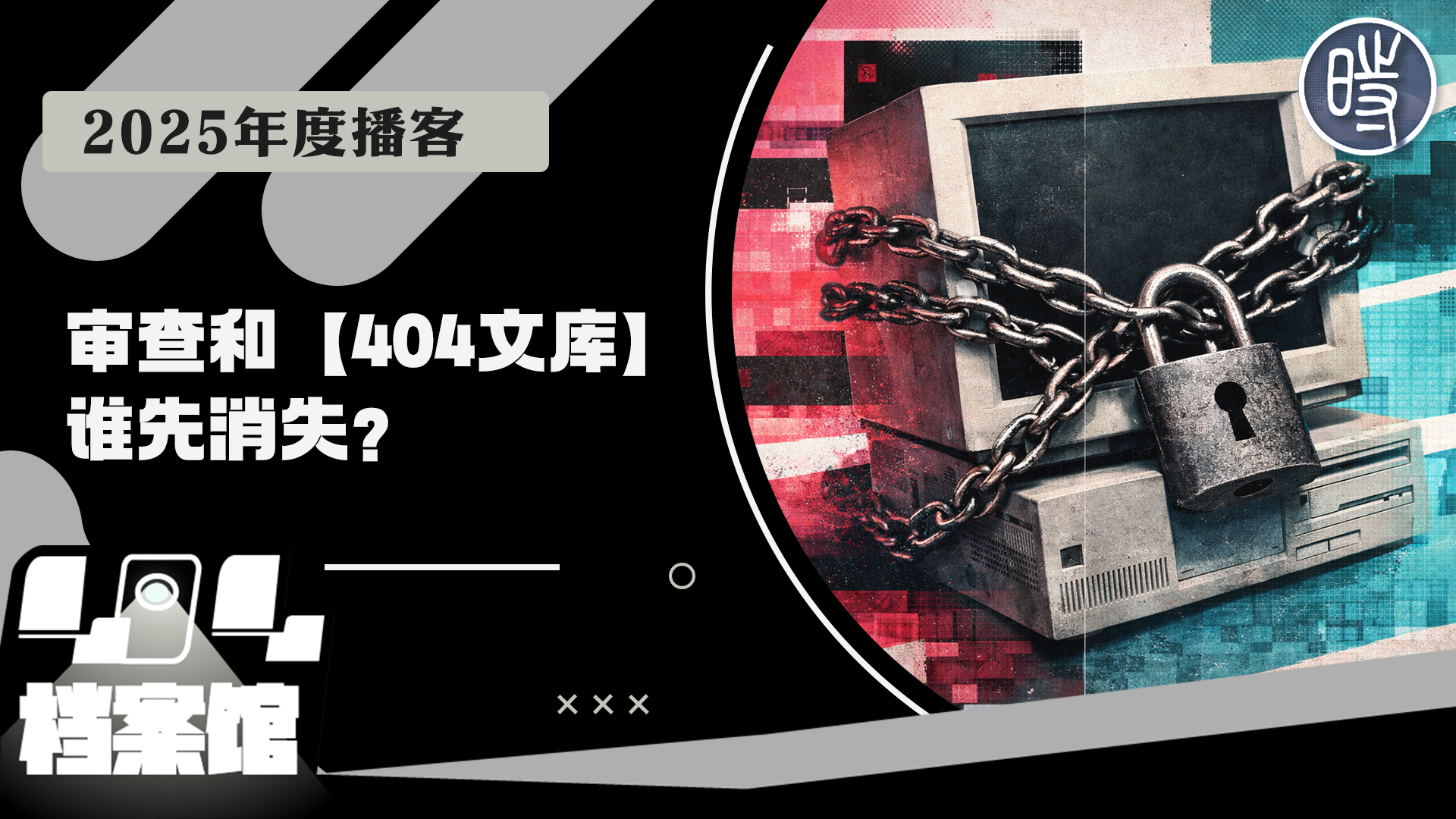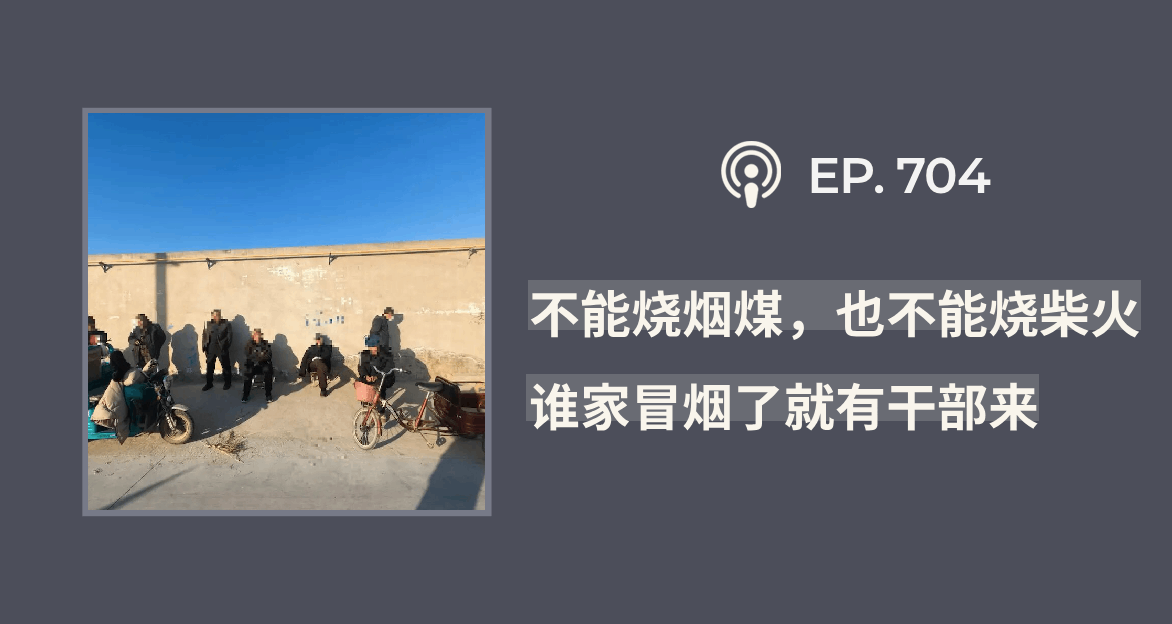昨天看到一篇名为《主要省市,“体制内强度”指数》的文章,作者在三年前提出了“体制内强度”这一指数,以此考察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活跃度。
这个指数其实很简单,即一个地方体制内人员(包含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缴存公积金人数占当地全部缴存人数的比重。作者认为,比重越高,这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就越高,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就越不适合创新和创业,也不适合投资买房。一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低于33%,是比较合理的。
作者举了几个省为例,从数据来看,也基本符合人们日常的直观印象。
比如广东,指数的两极化特征与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经济巨大差距的状态相吻合。东莞、深圳和佛山的指数均低于20%,珠海、广州、惠州、中山均未超过27%,珠三角边缘城市江门与肇庆都没有超过50%。但非珠三角的揭阳、茂名等城市,这一指数非常高,与东北地区城市接近。
江苏也符合人们的日常印象,最富庶的苏锡常地区,“体制内强度指数”最低,苏北地区则明显高于苏南,最高的徐州呈现典型的北方城市特征。
在山东,仅有青岛和威海两个城市低于30%,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鲁南的枣庄、菏泽和济宁都超过了66%,是典型的北方化城市。
辽宁最开放的大连,体制内强度指数也最低,但其他绝大多数城市都超过了70%,“要不就进入体制内,要不就离开东北”成为年轻人仅有的两个选择。
但“东北化”这个标签,并不意味着东北经济缺乏活力的情况最严重,西北才是更典型地区。作者提供了甘肃的数据,所有城市的指数都超过了70%,四个城市甚至超过了90%。
作者慨叹了一句:“超过90%意味着什么?基本上体制之外无世界了”。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体制内工作是唯一稳定和靠谱的选择,体制外当然有生存空间,但没有发展空间。
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嘉峪关选调女生”事件。主流声音批评她,也有人认为基于权利的个人选择不应苛求,而且当事人已经自行离职。我倒不否认“个人权利”的说法,也认为大众越是容易被冒犯,越是在正常认知的反面。但我并不同意这个女生表达不满是在抗争什么,因为她对嘉峪关的反感,并不是真正基于“人往高处走”,不是基于对地方政务、经济和观念的更高追求,不是“恨铁不成钢”。因为她最初意向中的兰州,在省会城市这个层面,观念同样相对滞后。她的期待仅仅是因为那是她的家乡,一切更为方便,她更期待的是稳定。
小地方更看重人情世故,体制内更加板结化,政务清明度相对更低,人情社会严重,个人生活更为压抑(找不到可以聊天的人,体制内女性很难找到看得上眼的配偶),这都是一直以来的事实。这个女生有不满其实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如果她所期望的是从“这里的体制内”跳到“另一个地方的体制内”,那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对于当地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说别无选择。
很多一心“上岸”的人,其实并不知道“上岸”意味着什么。其实上岸者的情绪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即使这个社会对整齐划一有着变态般的迷恋),有人会在喜悦中有憧憬,有人会有过于天真的期待,有人则会觉得人生从此定型。
那些过于天真的期待,会在现实中幻灭。前些年,有个上岸者发过一段牢骚。他说,在自己身处的小县城里,老一辈永远关心你为什么大学毕业了还不拍拖,二十五岁了怎么还不结婚,结婚都一年了怎么还不生孩子。即使是年轻人,也往往早早老去,坐下来就跟你谈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经,见到育儿和养生讲座就像打了鸡血。许多同龄人,有着高学历和小城里相对最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可家里没有一本书……但他只能选择妥协和懦弱。这样的年轻人,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确实别无选择,除了考公考编。
但所有对“上岸”的长远判断,其实都是很可笑的。因为“体制内强度”指数越高,就意味着体制外生存空间越狭窄,也意味着当地的经济活力越低。而经济活力低的地方,能够为“上岸者”提供的财税来源只会越来越少。这些地方的人们会越来越依赖于体制内,但反过来体制内又无法承载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员,只能涸泽而渔,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
即使是那些“体制内强度”指数低的地方也一样,因为众所周知的转移支付等原因,相对发达地区其实比欠发达地区更早体会到了寒意。
退一步说,哪怕现有模式可以持续,“上岸者”可以一直得到保障,拿到自己最期待的退休金,那又如何呢?如果一个人辛苦几十年,每日忙于各种机械且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退休金,那还有活着的必要吗?如果这样的生存已经是一个社会的最好选择(目前来说,考公考编确实是相对最稳妥的选择),那又意味着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前些日子还有个热搜——“调研表明东北体制内联姻已成不成文规定”。我开了个玩笑,说中国上一次“跨体制通婚障碍”,还是两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制度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赵丹在刊载于《中国青年研究》的文章《体制分割与青年的婚恋行为和就业选择分析——以东北青年为例》中指出,无论形式如何,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社会规范,这条规范对东北单身青年择偶行为的形塑与约束,不仅体现于个体的婚恋行动中,而且表现在有组织的相亲活动中。
该文提到,体制对东北青年婚恋的影响力,或许超越了收入、学历、户籍、毕业院校、个人能力、样貌,甚至包括爱情在内等诸多常见因素。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尽管拥有收入来源、高学历、房子和车子等优越条件,也难获得与体制内单身青年发展一段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一对青年在偶然的情境下产生了情愫,若得知一方在体制内就职,另一方暂无体制内的职业,则有可能导致这段感情无果。甚至,处于体制内的一方还可能产生被对方“占便宜”或被“高攀”的顾虑。也正是这种状态,让许多年轻人选择用脚投票,逃离东北。
赵丹分析,对于东北地区的大部分青年而言,先“立‘体制内’的业”,可为“成家”推波助澜。获得体制内的一席之地,或与同为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不但是社会个体的理想,而且是重要他人乃至社会的共同期望。这种集体共识甚至成为一种具有潜在强制性的婚恋行为规范。一旦没能获得编制,东北青年的婚恋过程也将受阻,社会个体及其家庭都可能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缔结婚姻的潜在社会规范,既排斥了体制外的单身青年,又加剧了体制内单身女性的婚恋难度。
东北并非唯一,中国社会一直有此倾向,只是程度不一。但从近年来“考公考编”几乎成为唯一选择的情况来看,未来肯定会加剧这一现象。之前有个段子,说东北才提前反映了社会现实,比如更早走向考公之路。这话其实也没错,毕竟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
当“体制内强度”越来越高,“跨体制通婚”成为障碍,那么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前面的路都只会越来越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