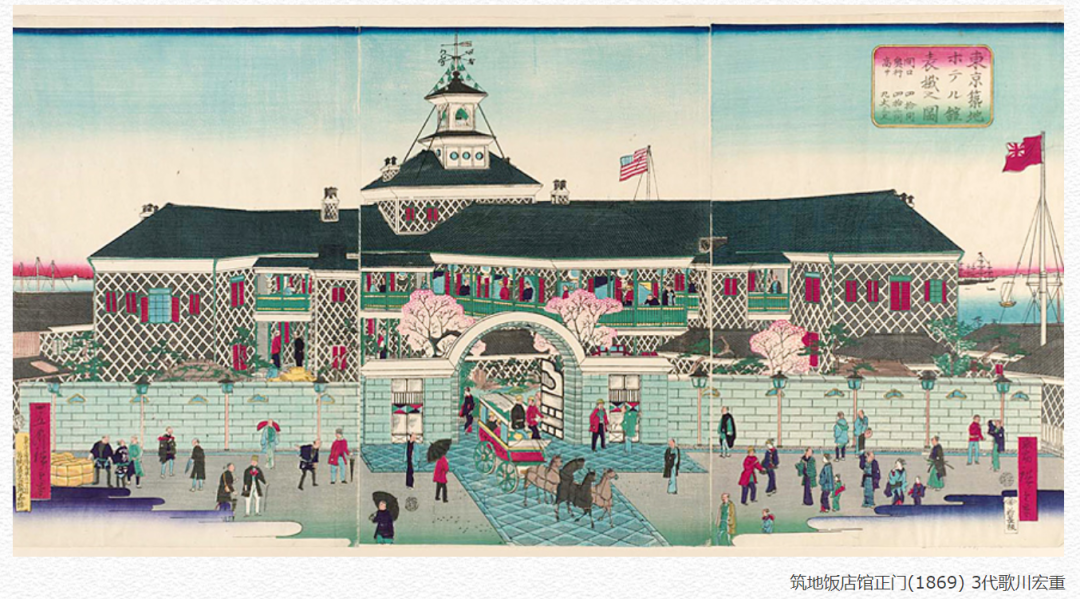「与其说日本人渴望吃白米饭,不如说他们渴望一个吃白米饭的民族。」
文|S.P
1872 年 2 月 18 日,一群身穿白衣的日本僧人强闯东京皇居,意图向明治天皇请愿,要求收回解禁吃肉的决定。闯宫自然失败,四人当场被射杀,一人重伤,五人被擒。
一个月前,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肉食解禁令》,将牛肉和羊肉纳入了日本人的日常餐食。而在更早为天皇祝寿的外交宴请上,已出现了「马德拉酒烤牛肉」、「小牛肉佐胡椒酒醋酱」和「烤羊腿」等菜品。
在这群请愿的日本僧人看来,天皇「立于万民之上,祭拜稻米、禁止肉食」,一定是迫于外国势力才解禁食肉。食肉将会造成身份阶级混乱,神明丧失居所,社会陷入混乱,乃是亡国灭种的大事。
日本人是应该坚持大和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白米饭,还是要学习欧美,改吃肉食面包?日本人民为此纠结了近一个世纪。
白米饭上的民族
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有多爱吃白米饭?
从 1873 年征兵命令的口粮标准就可见一斑。按照规定,每个士兵每天的口粮有六合(约 840 克)白米,加上六钱六厘的其他食物。这个标准已足以让全日本的农家青年兴奋地投军。
对当时的日本普通人而言,白米饭就是最好的食物,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访问日本的英国炮兵军官亨利·诺利如此记述日本兵的饭量和菜式:
日本兵是如此的满足于极大碗、作为主食的雪白米饭,和只有少许几片腌渍物的配菜。
然而,虽然饭量很大,日本兵的营养程度却让他看不下去:
在体力方面,他们在攻击时就像侏儒。对他们的武器来说,他们实在太矮小了。也难怪,他们的平均身高几乎没有超过 5 英尺(约 1.5 米)……在我所谓的肌肉精实度上,他们也不及格……比一般军人要好对付得多。
今天掌握现代营养知识的人们很容易看出,日本人传统的饮食结构很有问题:白米饭提供的精制碳水占了绝大比例,剩下的是营养很少的咸菜,蛋白质、脂肪等严重不足。要改善营养与健康状况,日本人急需多吃肉,少吃米。
然而在当年的日本,白米饭是神圣的,肉类是不洁的。用肉食取代白米饭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米饭的神圣性源于日本神道教。公元 7 世纪开始编纂的日本古史《日本书纪》写道,天照大神将高天原上栽培的稻穗交给他的子孙(历代天皇)饲育臣民,于是,天皇、稻米和日本民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直至今日,日本天皇每年秋收后都要用今年收上的新米祭祀天地(新尝祭)。新天皇即位时,还要举办同样性质但更为隆重的大尝祭。
相形之下,肉类的地位就卑贱多了。
公元 675 年,天武天皇颁布「杀生禁断令」,类似的禁令此后数个世纪络绎不绝。不过据学者考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禁令执行并不严格,普通人还可以吃野鸟、野兽的肉。
17 世纪德川幕府时代为了保护畜力,才真正禁止了食用家养禽畜。同时随着人口增殖,森林野地逐渐被开辟为田地,野生动物也越来越罕见,禁食肉类才成为普遍习惯。
到了 17 世纪末,吃肉在整个日本社会已成为一大禁忌。吃肉的唯一正当理由是治病,病人捏着鼻子吃完后,要向神佛致意道歉。万一在家里煮食,还需要将佛坛的窗眼糊住。
无论是 17 世纪访问日本的传教士,还是 19 世纪造访的西洋商人、军人,都在抱怨日本买不到肉、奶、面包,甚至只能从中国上海转运。
随着日本人睁眼看世界,日本人极不健康的传统饮食结构,很快引起了启蒙思想家的注意。最早也是最激烈主张吃肉的,是头像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
作为幕末兰学家,福泽谕吉很早就效仿荷兰人,在上不得台面的半黑店里大吃特吃又腥又硬的病死耕牛肉。
明治维新后,他在自己主编的《时事新报》上连篇累牍的推广肉食。
他认为,欧美人食用对于人类滋补最为有利的兽肉,而日本人却不吃肉,喜欢吃养分较低的草根菜叶。由此养成的身体和心灵都是脆弱贫乏的,在国际竞争中难免居于弱势。
福泽谕吉甚至激进的提出「废水田、强畜牧」。理由是:一、日本国土耕地狭小,不宜以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二、稻米作为热带植物,并非日本最适宜栽种的植物,三、可以输入取代自行生产,四、重视肉食才是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
不过,尽管有明治天皇的亲自推广和福泽谕吉等人的大肆鼓吹,但对于早已经将吃肉视为禁忌的日本人而言,这并不是一项容易接受的事。
当得知天皇陛下亲自带头吃肉时,整个社会受到了极大冲击,因而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1881 年,杉木钺子在自传《武士的女儿》中写到她家第一次吃肉的场景:
八岁的时候,某一天从学校回来,发现了奇特的事情,女性家属们不晓得为何用著和纸,仔细糊在佛堂闪耀着金色光芒的佛堂的门窗上。仔细一问,祖母表示:「你父亲说要在家里吃牛肉哟,从学习外国医学的医生那儿所获赠的肉说是可以强健你父亲的身体,也能让你成为像外国人般强健且聪明的小孩,因为牛肉即将送来,现在正着糊窗」。(按:在家煮肉需要将佛坛的窗眼糊住,以免玷污神佛。)
祖母叹了口气,表示世界转变如此巨大,连这样奇怪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家,最后未出席当天的用餐,而尽管杉木跟姐姐在用餐时悄悄讨论肉的美味,但却无法跟任何人提起这话题。
「食面包亡国论」
肉食禁令虽然解除,牛肉虽然一举跃升为代表文明、健康、现代、西化的食材,但日本人的基本饮食结构却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答案很简单:虽然舆论都说肉食好,可国内畜牧业刚刚起步,供给有限,无论普通人还是大头兵,都实在是吃不起。
不过,米饭的主食地位还是遭到了猛烈的冲击,挑战者是来自西方的面包和小麦。
1882 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首次向海外派遣舰队,与丁汝昌所率北洋水师在朝鲜外海对峙。
不过比起北洋舰队,更让日本海军将领担忧的是脚气病的迅速蔓延。日本主力装甲舰扶桑号上,约一半的士兵都得了脚气病,让这艘战舰几乎丧失战斗力。
「脚气」并非一般所说的「脚癣」(俗称香港脚)。患者一开始两脚麻木,行动不便,渐渐发展到上肢,或者突发心脏症状而死亡。直到 20 世纪初,人们才发现这是由于身体缺乏硫氨素(即维生素 B1)导致的全身性疾病,可以通过摄入粗粮和肉类等来补充。
18 世纪以后,脚气在主食精米的日本大城市愈发流行。在明治初年光吃白米的日本军队里,脚气更加严重。日本军医都筑甚之助将脚气病视为日本的「国敌」。
当时的日本医学界,普遍按照西方流行理论,认为脚气病是一种传染病。包括陆军军医部门的石黑中汇及森鸥外等,主张病原体是真菌或细菌类,做好卫生通风就可以了。
而毕业于英国圣托马斯医学院的海军军医高木兼宽,却在军舰筑波号的日志中发现:
该舰远航出现了大量脚气病患者,唯独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靠港期间一个都没有。水兵回忆当时场景:「大家都很高兴,唯有面包令人甚不习惯。」高木很快意识到,问题就在大米上。
高木兼宽发现,脚气病是一种典型的亚洲病,西洋人很少得。他因此假设,这是因为日本兵吃大米过多,缺乏蛋白质所致,应当学习洋人的食谱,多吃面包、饼干、肉类和蔬菜。
虽然高木对于病因的解释是错误的,却歪打正着找到了症结。
1883 年,「龙骧号」前往新西兰和南美洲训练演习,367 名船员中有 169 名患脚气病,死亡 23 人。
次年,高木让另一艘军舰「筑波号」采用与「龙骧号」完全相同的航线,用高木亲自设计的模仿西洋食谱做实验。结果,此行一共只有十五名脚气患者,其中 8 人没有按规定吃肉,四人未饮用炼乳。
高木兼宽的实验对日本海军的饮食影响深远。在他的后半生里,高木一直呼吁少吃米饭,多吃面食,「吾家自明治十八年以来,从不以米待客」云云,获得了「面饭男爵」的绰号。
此后,海军大幅提高士兵的饮食标准,其中增加的部分,正是高木反复强调的面包、肉类、大麦等,水兵体质的提高,确保了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
然而,海军的转变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对大米的崇拜,甚至就在高木研究的同时,日本陆军的同行便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后来成为日本陆军首席军医的森鸥外,在 1886 年前往德国学习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日本士兵样式补给之通论》的文章。
他认为,西方人的身材之所以比日本人高大,并不是西洋饮食营养更好,而是人种有别,消化系统存在差异。他盛赞大米的营养价值,并相信日本人的饮食毫不逊色于西方饮食。
1888 年 12 月,他发表了《非日本食论将失其根据》,认为日本人应该把大米作为饮食的核心。他通过计算得出,如果把肉类和面包大规模引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势必迫使国家过度依赖进口,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1891 年起,日本陆军的许多部队开始用混合稻米和大麦的法子,试图解决脚气病问题。但森鸥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 1907 被任命为陆军军医总监之后,就立即停止在陆军的米饭中加入大麦,还严厉批评海军的政策。
这种明显缺乏科学性的做法,得到了大部分日本士兵的欢迎。因为当时的新兵大多来自农村,对于满满一碗白米饭充满了向往——对于底层人民,白米饭是只有特殊的日子才能享受的稀罕物,怎么能轻易放弃并让位于西方餐食?
最终,日俄战争的胜利成为了白米饭反攻倒算的催化剂。
随着欧陆强国俄国的战败,日本民族主义高度膨胀,从煤油灯到菜谱,这些日本曾经挨个向西方学习的事物,此时又被挨个被国民质疑了一遍。
饮食方面,吃米饭的日本人在战场上击溃吃面包牛肉的俄国人,一举证明了福泽谕吉的肉食强国论纯属伪科学,本国饮食传统至少更符合国情。
食养会成员、陆军骑兵大佐西端学提出:「吃本土食品身体健康,吃外来食物身体则会变差」。
西端学还从佛教里学来了「身土不二」这个意味不明的名词,并很快现学现用,用来代指他的这套理论。
1906 年 11 月,奇书《吃面包亡国论》在食养新闻社出版。作者菟道春千代高屋建瓴的指出:
日本人吃了两千多年的白米,把脚气病栽到白米上是栽赃陷害,面粉的营养比白米差,不适合日本人消化吸收,以面包为主食会导致体质下降,这是肉体上的亡国;
放弃本民族优秀传统白米不吃,一味追求西化、模仿洋人吃面包,崇洋媚外,这是精神上的亡国;
如果都要吃肉和面包,日本就要依赖进口,在食品上浪费大量外汇,这就是经济上的亡国。
1909 年,日本陆军部成立预防脚气的调查团,由森鸥外担任主席,隔年,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的铃木梅太郎发现维生素 B 与脚气之间的联系。
然而,直到 1927 年,以七比三混合的稻米才成为日军标准主食。
混合稻米的成功,也并不意味着科学营养观的胜利:大米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昭和时期远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在昭和时期,所有明治时期关于饮食、文明和吃肉与否的争论,很快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军国主义宣传。
民族主义者赞美日本饮食,视之为日本人民过人健康体魄的源泉,是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每个日本人都要吃米饭,喝味增汤,坚决防止西方错误营养观入侵大和民族的餐桌。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日本式饮食的优越性得到有力证明:两位朝鲜选手代表日本取得了马拉松冠军和季军。
吹鼓手们认为,两位运动员的成功源自以大米为主食,这种饮食方式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补充血糖,维持身体长时间的能量消耗。
战争爆发后,日军起初也完全依赖本土或殖民地送来的物资,对搜集战场当地食品并不热心。1937 年 12 月,京津地区日军把掳获的中国大米主要用于抚恤、赈济地方百姓。只有在战争深入,日军后勤难以支撑之后,「鬼子进村」才成为常态。
太平洋战争中后期,大米在日本本土的地位再创新高。
在美军空袭和海上封锁下,日本本土物资供应愈发紧张,米饭优越论也随之愈演愈烈。1943 年,陆军主计少将川岛四郎在《决战下的日本粮食》一书中说:「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问题」,「米饭必须成为我们饮食的核心」,「酒应该留到我们赢得战争胜利之后再来享用」。
其实到此时,除了咸菜配米饭(如果不是更差的番薯、芋头的话),日本国民如果要调整饮食结构,基本也只能改走猎奇路线了。
战争最后时刻,川岛曾经通过国内广播建议全国百姓,应该吃掉鸡蛋壳,以获取食物能给予的全部营养。宫内省总厨师长秋山德藏也曾经联系川岛,认为战况日下,日本皇室可能要吃草,他想知道川岛对于天皇一家有没有什么营养建议。
战后,日本曾经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而一旦又能吃饱,他们便重新开始痛快地大口吃米饭,大米消费量在 1962 年达到了战后顶峰,每人每年能吃掉 117 公斤。
直到西餐风潮到来,日本人的吃米热情才持续下跌。战后经济奇迹中终于富起来的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提高了饮食结构中肉类和脂肪比重。
1955 年,日本平均每人一年消耗 110.7 公斤大米,1.1 公斤的牛肉,0.8 公斤猪肉和 3.4 公斤的鸡蛋;到了 1978 年,白米消耗量减少到人均 81 公斤,但仅仅是猪肉的消耗量就达到了 8.7 公斤。而人均鸡蛋消耗量是 14.9 公斤,一个鸡蛋大约 50 克,约合人均一年 300 枚鸡蛋。
那一百多年里,日本先是在封闭状态下遭遇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落后的科技水平给民族主义以藏身之所,后来又在历史狂潮的歧路中,将陈旧错误的饮食观念奉上神坛。
今天,西方式的饮食结构是否健康,是否值得东方人参考实践,似乎已经不应再成为争论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拉面 食物里的日本史》,顾若鹏著,夏小倩译。[2]《饮食、权力与国族认同 当代日本料理的形成》,Katarzyna J. Cwiertka著,陳玉箴译。
[3]《从吃牛肉看文明开化时期的理想身体打造》,黄靖岚。
[4]《面饭男爵 高木兼宽》,廖育群。
[5]《日本明治社会疾病意义之考察》 ,王梅。
[6]《在帝国医学与殖民医学的夹缝之中,日志时期台湾人脚气问题病研究》,范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