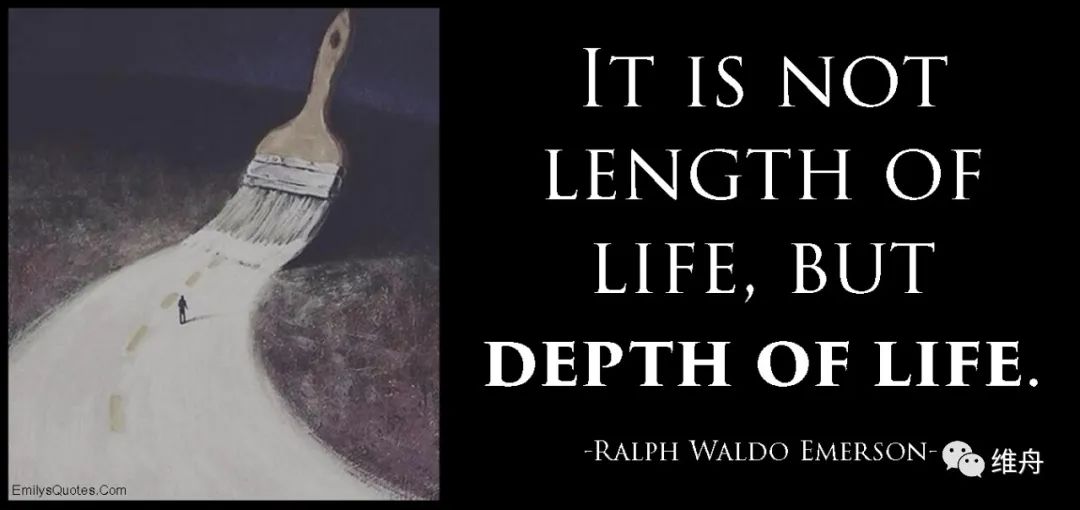1
前些年,高晓松曾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这看起来带着某种“小资”的情怀,有些人被打动,有些人则嘲讽这只是鸡汤,随后被人倒过来戏仿:“这个世界不只有诗与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这也算是常态:对一个刚刚吃饱饭没多少年的民族来说,“诗与远方”这种精神追求,看起来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是不知民间疾苦,甚至是一种特权。
这一心态相当普遍,最能印证其存在的,就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之后,中国人普遍觉得“日子过得好了”,但与此同时,哪怕是月薪两三万的人,也都坚称自己属于底层的“老百姓”而拒绝“中产”的标签。这不仅仅是谦虚或站在多数一边的安全需求,因为从他们的心理需求层次来看,确实也与最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不同。
社会学者何国良、梁世荣曾基于1993-1995年的社会指标调查研究发现,香港社会当时虽然已持续繁荣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却并未像西方社会那样,随着社会日趋富裕而逐渐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香港人的心灵中,物质主义根深蒂固。即使社会及经济环境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但也不易改转过来。”
这并不只是因为香港人是“经济动物”,至少文化同根,在这方面大陆人即便和香港有所不同,也最多只是量的差异。事实上,像香港人这样的现象,在沿海城市已经出现,那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即便现在暂时活得不错,但还是要紧紧抓住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以免有一天连这些都统统失去。
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更高精神层面的需求是谈不上的,甚至一萌生就会被掐灭。这就像我父母那一辈,年轻时的匮乏记忆深入骨髓,我还在上初中时,她就单位发的被褥、脸盆都整齐收拾好,说留着给我将来结婚时用。她以前嘲讽我外婆总是把好东西留到快变质、发黄才怕坏掉而拿出来用,到现在却自己也重蹈覆辙。即便日子宽裕了,但她还是不习惯享受,相比起来,过紧巴巴的苦日子让她感到自在得多。
英国社会经济学家R.H. Tawney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一书中写到1931年的中国农村时,曾有一句名言:“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他当时这么说,是鉴于当时的农民手头拮据,抗风险能力极低,但现在近一百年过去了,很多中国人(也许是大部分)的心态,仍然像是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哪怕他们已经上岸了。
2
在一场争论中,我看到有人扔下一句:“一小众精英阶层的‘高级’权利,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比起来,屁都不是。”
这位也读过不少书,平日发言尚属严谨,连他也这么说,不由让我认真想了下,为何我们社会中这么多人把“生存权是最基本人|权”这个论断俨然看作是不可动摇的铁律——有些人甚至断言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一个相对普世的解释性框架”,这么说的人,可也是逻辑思维能力挺强的一位。
在新冠疫情之下,这一对生存权的强调更达到了新的高度。4月初,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便嘲讽了欧美对出行自由的强调:“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Human Right or Human Left。”
这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其实是在非此即彼的对立框架下混淆了基础性与重要性——吃饭是人生活中最基本的,但它是最重要的吗?否则为什么要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呢?
这个逻辑陷阱的问题,就在于非要把不同层面的事物,按优先等级分出个先后与轻重。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后,往往对其树状结构的政治平衡感到困惑不解,会问:“三权分立,那国会议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和总统,究竟哪个最大?”林达《在边缘看世界》中就此答道:“不同分支的权力、功能和官员的地位,也就是不可比的,就像猫和狗不可比一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究其根源,恐怕在于我们根深蒂固的一元化思维——在权威、评判标准都单一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强行分出清晰的等级先后的。李维汉曾回忆当年在陕甘宁边区,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在此三权是“政权的三种职能”,背后仍是一元而非彼此制衡的三元。连这尚且可以中国化改造,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在社会结构尚属简单的时代,这不失为一种高效的垂直化组织结构,但当社会高度复杂之后,这就不免削足适履了。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活动都有自身的逻辑,只有在其单独的逻辑内部,才能进行判断,而在逻辑之间则难以分出先后,只能制衡。
这就出现了相声《五官争功》中的那种场面:多元的事物已经不可比了,就像比赛尝味道,五官都不如舌头;而如果比赛听力,也都不如耳朵。然而,中国人在这样的场面中看到的是争论不休的混乱,最终不是和事佬式地调和,就是重归一元化的秩序,而不是走向合作与制衡。
3
确实,脱离现实奢谈空中楼阁,不免让人感觉好高骛远,但始终紧抓着基本面不放,那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那就是整个群体的心灵始终在低层次徘徊——而对这一点,中国社会却好像普遍缺乏应有的警惕。
我将之称为“心灵的内卷化”。所谓“内卷化”(involution),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达到一种精致而固化的形态后,便倾向于不断自我维系、自我保持和自我复制,无法实现突破,转化为另一种高级形态,从而呈现出长期停滞不前的态势。有时这也被称为“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Frank Hahn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即人们一旦“达致这一状态,就不会给我们留下这一状态会发生改变的任何合理理由”。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指出,一个广泛存在“内卷化”的社会完全可以呈现出与一个典型的奴隶/农奴社会类似的诸多经济特征:劳动极度密集的技术的使用、非常小的外购生活消费品市场、对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极端缺乏兴趣。简言之,这是一个忙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无法实现自我突破的社会。这乍看起来像是另一种“停滞的中国”说,但其实是历史上各大文明的常态,能自发实现现代化变革只有西方文明。
4
这种思维定势的问题在哪里?
在我看来,它建构了一种虚假对立:很多事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也没有先后可言。即便两者在特定情形下只能二选一,那么,如果说欧洲人为了更高的权利意识放弃了生存,中国人也一样,只不过相反,是为了生存而放弃了更高的层次。这不过是不同的选择侧重,而重要性的排序,乍看是“事实”,其实是价值观的折射,如何排优先级,涉及多维度的评估和权重设定。
但更重要的一个误区是:它暗示了,“劳苦大众”在吃饱饭之前,谈不上精神需求。近些年女权意识兴起,最常见的反驳之一,便是“在一个连基本人|权都还没有保障的地方,谈何女权?”这同样构建了一种虚假的优先秩序,仿佛这两者是矛盾的,必须分个先后。
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很多追求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也不见得有什么固定的先后秩序。就像农业无疑是最基础的产业,但如果要说它是否就是最重要的,那在小农时代或许还成立,当下则不得不打个问号。过多把注意力分配在这些最基本层面的事物上,势必带来的一个危险就是陷入内卷化而难以迈进更高的层次。这就像是有人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去好好读书。”——但如果他这么想,也许就永远也等不来这一天。
讽刺的是,在一个经常嚷嚷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恨不能一步登天的社会里,在这些方面却顽强地遵循着“循序渐进”的步调。这看似不无道理,但看看我们周围就能发现,这样的排序其实是虚假的:一个清贫的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那些早就实现温饱乃至富裕的人,也没有因为因此就转向精神追求,却有可能比常人更贪婪地还想占有更多的物质。事实上,中国社会不时可见的是反例:真正有精神追求、将之珍视为人生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人,往往倒挣扎在生存边缘。
在这一点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能也在无意中误导了人,让人误以为在这个金字塔中,需求层次的满足是逐步递进的,这又与中国文化中“仓廪足则知礼仪”的说法一拍即合;但问题在于:究竟多少才算满足、更高层次的追求有多重要,这些判断都是因人而异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认真地对我说,他觉得要实现财务自由享受人生,得先赚够1个亿——而他所说的“享受人生”,恐怕也不见得是精神层次的追求。
毫无疑问,正是对生活的不满足感,驱使着我们前行。很多人并不是缺乏这种不满足感,只不过这仅仅指向物质层面——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病态的一面:对物质的不懈追求,会广受赞誉;而对精神性事物的追求,则被看作“不务正业”。换言之,后者被看作是非生产性的、消耗性的(“败家”),是令人不安的“折腾”,而不顾正是这种不安分,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丰富。
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在其自传《追寻事实》中感叹,人生是一场充满意外的旅程:“在如此多元化的时代,在如此多样化的人群中,进行如此不确定的追寻,我们不会有很多确定无疑或封闭的感受,甚至可能连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都不太清楚。但这却是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本就值得活得更好,很多时候,并不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像力,而是想像力的限制导致了你人生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