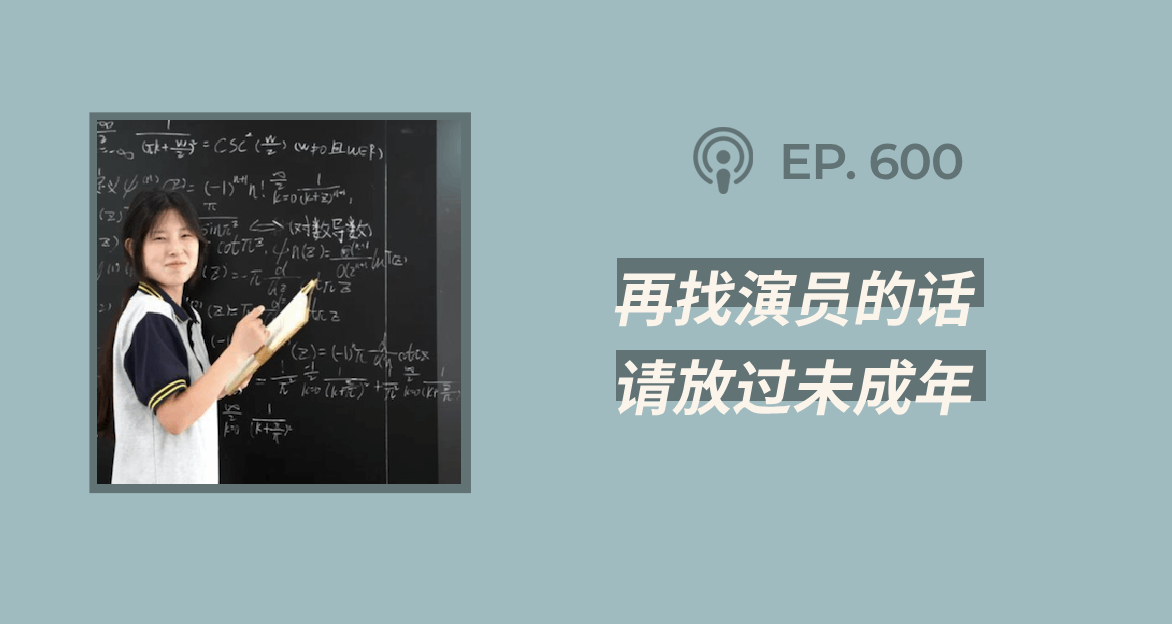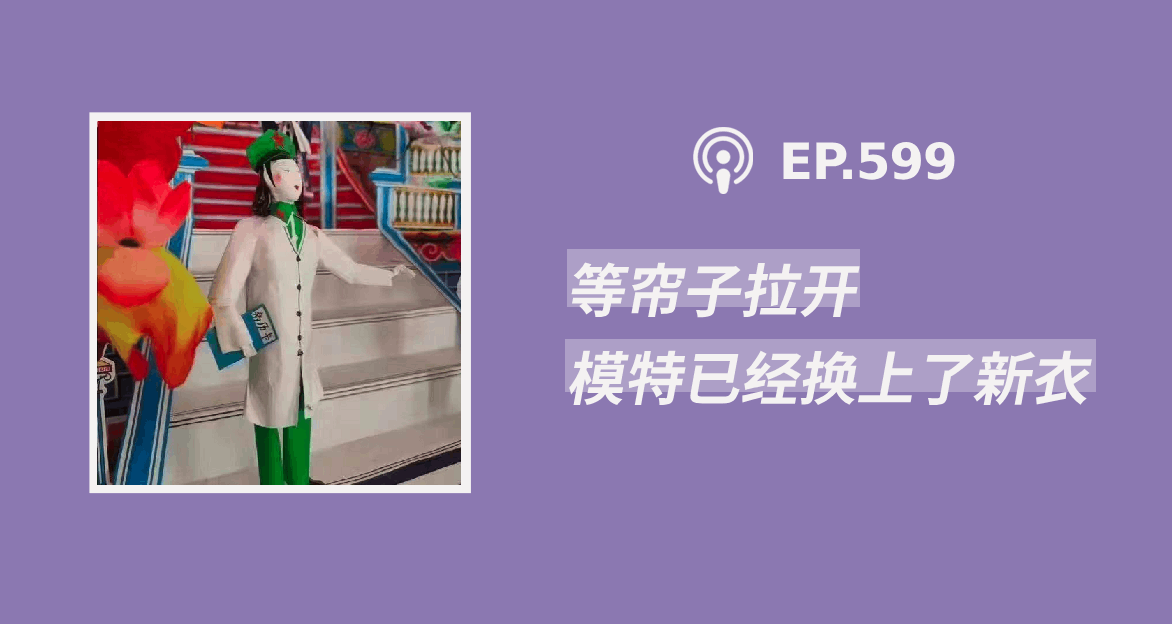樊纲:中国户籍与土地制度阻碍城市化进程
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城市贫民窟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城市严重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用城市居民数量占人口百分比来衡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按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是48%。考虑到30年前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8%,这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进步虽大,但仍不能让人满意。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时候,城市化速度都快于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却落后于工业化,用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百分比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目前约为70%。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民工入城。但我们现在城里的户籍人口是贵族,给他提供东西远远高于农民能够得到的东西。所以它里面的价差非常高。农民工市民化,这个是大趋势。要在资源配置基础上做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是怎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讲公共品供给。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个显著差别:中国城市不论大小都看不到任何重大城市贫困人口或贫民窟的迹象。人们往往把这现象归因于中国的户口制度。中国人一出生就被户口制度区分为城市特权和农村贫困两类。然而,这一制度虽然让农村人口享受不到一些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比如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和失业保险等,但却从不阻止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事实上,政府一直在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这就是为何在过去30年,超过40%的中国劳动力,即约3亿人脱离农业进入日渐向城市集中的工业和服务领域。结果,在中国城市中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总数量已经超过了持城市户口的工人。 如果防止贫民窟在中国城市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是什么呢?我认为,防止严重城市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发轫于将生产土地租给农民家庭的所谓“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意味着在改革初期,集体生产方式便已土崩瓦解,由私人取而代之。 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虽然仍归“集体”所有,但家庭可以获得土地产出的所有“剩余价值”,这就给了农民有效利用土地的诱因。如果家庭成员在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还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别的农民。 家庭可以在承包期内保留转包的权利,但他们并不拥有土地权。如果农民工出现财务困境,他们可以更努力地寻找新工作或向政府求助,但土地却绝不能被出售或抵押,土地的用途也不能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转作其他商业用途。 这一特殊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如果农民工失去了城市的工作,他们还可以从地租中获得一些收入,也可以回到农村重新靠承包土地生活。在家庭承包制度下,农村家庭获配的一小片土地虽然不能致富,却可以发挥作为最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土地制度造成城市化滞后且不稳定。 这就有力地解释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独一无二的土地所有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似乎不可能复制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储备留在农村,而不是留在城市贫民窟。 这安排虽然让城市化得以较平稳推进,但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性而非永久性制度。农民工仍然感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为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是由其农村户口决定。事实上,由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分隔,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社会差距。 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中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让中国的城市化极度不稳定。要实现“永久城市化”,中国必须引入新的社会安全网。宣布废除户口制度或许并非难事,但若没有可以缓冲农民工在城市所面对风险的制度,这样做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让农民工也能享有公共服务,如教育和正式的社会安全网,这才是城市化进程成功的关键,即使囿于资源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农民工就会争相变成城市居民。从获得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也会变得更平等。 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或许将较有效的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为建立全国性、普遍性及可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努力。“十二五”规划也可能规定城市政府增加提供给不持户口的长住居民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最低工资保护。试点工作已在重庆和成都等城市展开。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和犹豫之后,高层决策者显然已经做好了采取新方法,迈入城市化新阶段的准备。 城市化的主要挑战并非基础结构和城市设施,不管它们有多重要。成功的关键,是让农村移民在城市里成为平等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公共服务。这个目标需逐步实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