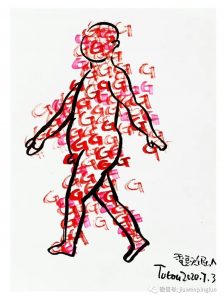作者:宋志标
在山东方面表示彻查苟晶被冒名顶替一事后,7月4日下午,几个省级部门联手的调查组发布了调查通报。有必要提醒的是,调查组在之前赶赴湖州接触了苟晶,而她在微博上表示过受到了许多压力。通报一出,它就成了全部,没人再去关注苟晶的心路历程。
回到通报的内容上。它确认了苟晶1997年高考被冒名顶替的事实,通报后半部分给予政纪党纪处分的十来个官场小吏,联合起来,让班主任邱印林的盗窃计划成真,苟晶的身份、档案、身份证在这一年被邱小慧冒用。这是通报的核心结论,证实了苟晶的主要指控。
再一个,苟晶1998年高考被调查组定性为“正常录取”,尽管所用的档案是邱印林偷偷制作的一套。相对于苟晶这些年在心底里推演的谜团,这个调查结论可以解释了邱印林“狸猫换太子”的持续动作,也可以呼应舆论关于“苟晶第二次高考录取是如何实现”的质疑。
从调查组披露的成绩看,苟晶高考成绩与她的摸底考试等有差距,97年低于录取线,98年略高于录取线。对90年代高考有基本了解的都知道,模拟考与高考成绩有落差,是常见的情况。整个90年代的高考录取比例很低,竞争残酷,不独山东才有。
在这个通报出来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理性、客观、中立的类型,俗称为理中客的,像是吹响了集结号,开始淡化苟晶被冒名顶替的恶劣影响;二是直接责骂苟晶,认为她“人设”崩溃,之前言辞夸大,没遵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常。
在我看来,这些理中客的依据是不成立的,是一种小人之心。而从通报出发,无视它的核心结论,反过来责骂苟晶“并非学霸”,“未受冒名顶替的影响”,都是唇红齿白的无稽之谈。即使不去推断这些论断的动机,但它们已产生很恶劣的效果。
有人认为,通报与苟晶所指控的不完全吻合,所以她就是怎样怎样。苟晶是一个个体,一个有直接证据(邱印林的所谓忏悔信)能推导出自己被冒名顶替的人,她没有权力和能力调查整个事。调查事实是官家的责任,公权的义务,不能本末倒置。
认为苟晶没有反映全部的事实,或者事实理解有偏差,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将本属于学校、教育局、纪委监委的调查任务强加给苟晶——或者任何卷入类似处境的个人——往轻里说,是苛责;往重里讲,这就是善待公权、恶猜个人的无能之举。
像冒名顶替这样的操作,很多时候不见得是掌握多大权的人所为,更多是县域关系网络中低阶官员就可以完成的。从山东通报的冒名顶替个案看,提档、伪造档案、重新制作身份证,都是县官不如现管,这是县域“纸牌屋”的无声默契作业,外人无法洞穿。
在这种情况下,苟晶从自己的经历、经验出发,推测自己在班主任、学校等方面遇到了不好的对待,这是很正常的表现,她即使无法准确地、完整地还全部事实,但苟晶又不是诬告诬陷,调查组甄别、补充、核验相关事实即可,苟晶没有任何义务要为“事实不准确”负责。
除了拿“事实不准”来打苟晶,还有一个很有迷惑性的攻击角度,说她没有受到冒名顶替的“实质”影响,所以她叫苦喊冤就是“矫情”。在这种责骂苟晶的模式下,隐藏着至少三种立场:一是常见的厌女症,二是追求完美受害人角色,三是混淆视听。
以被冒名顶替者受害程度不大,来否认他们的愤怒、控诉、主张——总的来说是否认他们的存在感——这首先是一种失焦的行为。因为在所有冒名顶替个案中,最该关注的是这一恶行本身,是谁通过什么关系用了什么手段掠夺他人身份,如何侵害无辜人的人格权。
山东调查组确认了苟晶被冒名顶替的事实,至于她受了多少伤,有没有真的被“偷走人生”,命运有没有因此逆转,都不是责骂苟晶的理由。责骂苟晶不够惨,所以她不算是冒名顶替受害人,再推导出她的人品问题,这一套言辞是很下作的。
之所以说这套修辞是下作的,证据来自于使用者本人,是自证的。因为,这些人比较了陈春秀与苟晶,认为陈春秀够惨,她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被冒名顶替者,所以陈春秀值得同情,而苟晶不值得同情。正是这种看似有理的列举法,暴露了论者的短见或龌龊。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陈春秀,还是苟晶,都是同一套冒名顶替术的受害者,在她俩背后,闪现着相同部门职能的作奸犯科者,他们不管是在聊城,还是在济宁,县域“纸牌屋”采用的是同一种手法。不管是更多地怜悯陈春秀,还是更少地同情苟晶,这套作恶手法不多不少、不增不减。
在如此雷同的冒名顶替手法下,说陈春秀因为伤得更完美、苟晶伤得不够完美,所以苟晶就是“居心叵测”的家伙,这种错乱的逻辑要如何自圆其说呢?只能雄辩地证明,这种比较下,所谓对陈春秀的同情是假同情真虚伪,对苟晶的苛责是真小人假君子。
通过追求一个完美受害人角色,苛责苟晶之种种,实际效果是掩盖了苟晶被冒名顶替的模式,淡化了那套联合作业的幕后罪责。当然,理中客会辩解说,他们也抨击冒名顶替的黑箱操作,但要看后果云云。可这套操作在制造陈春秀们、苟晶们的时候,也会如此“体贴”吗?
陈春秀和苟晶都是冒名顶替的受害者,陈春秀的执着与苟晶的坚定是一致的,都是寻求被冒名顶替的真相。她们都出身寒门,都做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梦,却是为别人苦读。她们是同一个刀锋的受害者,数着苟晶的伤说不够数,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出口的。
陈春秀与苟晶也不是不能比较,但不该比较谁的伤更完美,而是比较她俩受伤的形式。陈春秀受的伤是大学梦的破灭,苟晶受的伤是不再信任家长的同学、师长等关系,她痛恨那片是非不分的土地。这种决心要做故乡陌生人的伤痛,在苟晶的讲述中充分展现。
冒名顶替带给苟晶的深刻的精神创伤,它没法量化,无法显性地通过具体诉求来弥补;因为这种伤特别个人化,无法被真正地感同身受,所以也无法博取很多共情。在同样经历下,苟晶面对那些心知肚明却沉默的同学,面对所谓练达实质是背叛的人情,这种痛感更深。
但对那些责骂苟晶的人来说,她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过得好,所以造成一个微妙的局面:对陈春秀可以轻易释放的同情心,是对低到尘埃里的人的同情,它很容易释放,并让同情者获得道德的虚荣心。而这套自上而下的廉价的同情机制,在苟晶这里会失效。
有一种观察也许不那么全面,在社媒大行其道的认知世界里,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他们要么看重从成功者那里映射生而为人的未来幻象,要么从被欺负被侮辱的人那里映射高人一等的道德感。对那些中间的毅行者,反而是诋毁大于尊重,泼污胜过体面。
依据比惨,来分配社会同情,这是非常不堪的人间景象。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有稳固的是非标准,很难有稳定遵守的原则。这样的不稳定,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粉碎的状态,也让一些舆论引导有了“抓手”,有了可以着力的点,不是徐图而是快速地催化舆论成果。
与上述讨论无关的一点是,我们谈论了许多被冒名顶替的个案,也不得不接受调查结果的有限指向,但我们似乎不善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即使不被冒名顶推,不曾经受这些,陈春秀们、苟晶们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吗?当然这是假设性问题,没标准答案。
这有点扯远了,不再是时政的范畴,进入文学的空间了。但还是好奇,当人们在谴责陈春秀被“偷走了一段人生”时,究竟是指什么?现有的冒名顶替者都有公职,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可是,陈春秀他们即使没被冒名顶替、哪怕上完大学也不一定能拿到。
所以,在冒名顶替事件中,什么才是那称得上是“希望”的部分?(没人会天真到把调查视作希望吧)寒门苦学,冒名顶替,十多年后惊觉……都很打击人。真正励志的部分也许闪现在苟晶身上,断然告别,不懈打拼,借时代浪潮超越厚黑学盛行的地域。
回到主题上,即使以最大善意来理解那些责骂苟晶的人,哪怕他们仅仅发自内心,也不能以“失去某种人生的可能性”来增减受害者权重。这配合的是议题失焦,是狗苟蝇营,是苟且之辈的做法——因为它是新的污染,新的伤害,灌注到恶之花的土壤中,变成恶的一部分。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