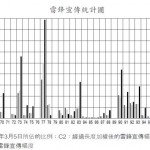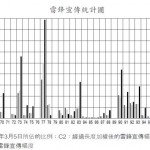(这是十年前我的毕业论文,至今看来,历史还真是一面镜子啊。)
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号)
柴子文(吴海刚)
在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中,英雄人物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刘胡兰、董存瑞等成为战斗的号角,1949年之后,雷锋、王杰、焦裕禄等又被塑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通过号召全民学习英雄事迹来凝聚和团结群众,无疑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尽管英雄人物在各自的年代里发挥过不同的功用,但是,他们应时而生,也应时而灭。然而,雷锋却是一个例外。时间的推移非但没有让人遗忘他,相反,学习雷锋在各个时期都成为紧扣时代主题的社会运动,并且呈现出多样的主题和要求。雷锋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模型。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人民日报》对雷锋的宣传,分析雷锋这一道德模型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过程。
一
据官方的传记记载,雷锋1940年生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不满七岁就成了孤儿:父亲遭日寇毒打致死,哥哥做童工,由于劳累过度得肺病而死,母亲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悬梁自尽。之后雷锋被亲戚收养。1949年以后,雷锋有机会接受免费的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先后做过通信员、县委公务员、工人,1959年12月参军,并随军迁至辽宁省营口市,1960年11月入党。因为在1960年抗洪抢险中的积极表现,雷锋的事迹通过题为〈苦孩子好战士〉的文章在报刊发表而得到了传播。此后,雷锋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1961年9月被推举为抚顺市人大代表。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
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认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题词,全国性的学雷锋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毛泽东的题词,第二版则刊登了罗瑞卿的文章。罗当时在党政军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的题词和罗瑞卿的文章都是从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中转载过来的。罗文强调「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覆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为一个已故的烈士相继题词,这在建国后并不多见。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单纯的号召向模范学习的运动,它跟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有着密切联系。1958-61年,中国发生了二十世纪以来破坏性最大的饥荒,这大大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一方面,面对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务实派着手整顿经济,在各个经济领域公布通过调查研究制订的政策性文件。随着鼓励农业、工业和教育单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自政策的职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降低了;更重要的是,某些人开始对大跃进、撤消彭德怀的职务、毛泽东的政治领导,甚至毛泽东的能力和个性提出批评。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显得日益不安。毛大力支持由林彪提出的、旨在突出毛个人权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作为对刘少奇「右倾」的一种反击。随之,从军内到军外,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造神运动被全面推开。
学雷锋运动是造神运动的典型产物。跟当时很多其它英雄模范一样,雷锋来自于军队。自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发起军队政治化的运动后,人民解放军的地位急剧提升。军队的作用甚至进一步伸延至其它领域,军队的政治部制度开始在党和政府结构中推广,1963年起,中央各部委都设立了政治部。通过有选择地安置退伍军人和设置新的政治部,解放军已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建立了政治影响的网络。毛泽东在为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寻求办法的过程中,把军队视为最重要的后盾。而主要由农村新兵构成的人民解放军,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经过简单化和教条化的思想,也更利于造神运动全面而有效地展开。
学雷锋运动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印记。学雷锋只是一种形式,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是要学习毛主席。然而,这一点却使雷锋能够逐步转变成为一种维护政治权威的道德模型。因为从政权继承性上讲,不管实行的政策倾向如何,政权最终的合法性始终是来自于革命,而谁也不能否认的是,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也因此,作为造神运动产物的「雷锋」,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仅没有像文化大革命中其它造神运动的产物那样受到严厉的批判,反而成了一项缩小改革前后政治合法性鸿沟的最现成也是最有效的政治遗产。
二
在学雷锋活动中,「发扬雷锋精神」是一个被不断强调的主题。所谓「雷锋精神」,就是在学雷锋活动中某种能够有效地推动、强化政治和社会动员的思想和品质。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内(1963-99年),雷锋精神随着时代的变革一直在不停变换主题。共有五个宣传高潮:1973年、1977年、1983年、1990年、1993年。以这五次高潮为分界点,可以将雷锋宣传分为六个阶段:1973年以前为第一期,1973-76为第二期,1977-82为第三期,1983-89年为第四期,1990-93为第五期,1993年以后为第六期。第二、第六期的宣传是无序的,其它各期则呈现出曲线的分布。第二、五期的宣传在两个高潮之间呈下降趋势,第三、四期的宣传则在两个高潮之间呈上升趋势。本文将这六个时期作为分析雷锋精神的基本框架。
雷锋宣传的第一个时期(1973年以前)属于文革初期,学雷锋的主要立足点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中「爱」的层面。第一期的雷锋宣传在《人民日报》的幅度并不大,但是却体现了最重要的政治信息。雷锋是忠于毛泽东的典范,作为个人的雷锋,其所有的成绩和贡献来源于毛主席的思想。
第二期的雷锋宣传(1973-76年)的重点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中「憎」的一面。这一转变主要是由党的历史上一起严重政治事故造成的。1971年9月,突然有报导说林彪在外蒙古的一次坠机事件中身亡,事实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林彪密谋篡权,甚至暗杀毛泽东,而当他卑怯的阴谋败露时又试图逃跑。
1973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全面概括雷锋精神的文章,在署名为「雷锋生前所在连队党支部」的通讯中,雷锋值得学习的地方被总结为三个方面:「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第二期雷锋宣传中,「钉子」精神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的宣传中出现。「钉子」精神的实质被阐释为一种刻苦而认真的态度,被用来鼓励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这在1973年和1975年的宣传中都有所表现。
雷锋精神在第三期的雷锋宣传(1977-82年)中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1977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中,雷锋宣传第一次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社论中,周恩来的题词成为对雷锋精神的「精辟概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当时的情形下,学雷锋体现的最主要的方面依然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这篇社论号召:「我们学雷锋,就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大破大立……就要永远怀念和崇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就要仇恨代表着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利益的『四人帮』」。
到了1980年,雷锋精神的定位出现了转变。《人民日报》转摘《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指出「新长征需要有雷锋那样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精神,也需要有雷锋那样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钉子」精神得到了新的阐发,被定义为「勤奋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的精神。而取代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成为学雷锋又一主要内容的是「维护社会公德,培养文明行为,注意品德修养」。这些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即将逐步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期的雷锋宣传(1983-89年)中,改革的需要被进一步融入雷锋精神,「傻子」精神和「螺丝钉」精神被概括出来。1985年,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精简整编中,《人民日报》号召学习和发扬雷锋先人后己的「傻子」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另外一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党把他拧到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的「螺丝钉」精神被认为是在面对「是听从党的安排,还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考验时,需要学习的榜样。
第五期和第六期的雷锋宣传中,雷锋精神在经过新一轮的道德整合之后,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继1977年关于雷锋的社论在《人民日报》3月5日的宣传中第一次出现之后,1990年再次出现。雷锋精神被定义为:概括地说,就是一种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合,其核心是共产主义精神。1991年《人民日报》刊登江泽民会见「雷锋团」的讲话,强调指出「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由此而出现了学雷锋活动指导思想上的变化,「要求今后学雷锋活动要在坚持开展好公益服务活动的同时,把活动的重点转向立足本职工作,在岗位上体现出奉献精神」,「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成为学雷锋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1993年纪念为雷锋题词三十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的讲话再一次全面总结雷锋精神在新形势下所要求的表现形式。「钉子」精神被概括为「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螺丝钉」精神被提炼为「立足本职,忠于职守」;雷锋精神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精神中所包含的传统美德,被总结为爱国主义精神,它在新形式下的要求就是「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三
由上分析,随着时代的变革,雷锋精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雷锋因此而成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模型。其主要的功能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运动的风向标;第二,构建或者维护政治权威的工具;第三,社会风气的调节杠杆。
在雷锋宣传的早期阶段,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被突出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学雷锋活动跟批判阶级敌人紧密结合起来。刘少奇被称为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他的罪状之一便是「肆意歪曲雷锋同志的高大形象,把雷锋同志说成是『和平时期』的典型,抽调其阶级斗争的灵魂」,其目的被解释为「妄图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号召要「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满怀无产阶级义愤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而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雷锋又同样被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四人帮」的罪行之一就是「污蔑学雷锋是不分阶级、不讲路线、不抓大事」、「竭力破坏毛主席倡导的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甚至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公然砍掉周总理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学雷锋活动能够跟中国的政治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雷锋的阶级出身。雷锋是旧社会的孤儿,是共产党的贫民政策使他「翻身」成了「主人」,这种感恩情结凝聚成为一种坚定的忠诚。因此,雷锋精神很容易就被强化为对毛泽东和以他为灵魂的共产党的一种不容置疑的忠诚。毛泽东时代的各项政治运动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或者极力支持的,只要从阶级感情的立场出发,一切的支持都应该是无条件和高热情的。同时,在后毛时代只要牵涉到党的合法性问题,同样的理由,就可以从雷锋精神中提炼出一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来增加道德砝码。
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同时也起到了构建或者维护政治权威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雷锋宣传的高潮年份。1973年、1983年、1993年是毛泽东题词发表逢十周年,这三次都试图通过雷锋宣传来巩固和维护现存政治权威。1973年通过强调「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批判反对毛泽东的修正主义者,重新确立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而维护和修复因为「九.一三」林彪事件和经济混乱而严重受损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原有的绝对政治权威。1983年的情况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掌权之后,试图通过雷锋宣传对其领导的经济改革进行道德合法性的补充和确认。雷锋成为从革命政府继承下来一项有力的政治遗产。1993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二年,经济改革在中国掀起了新的高潮,而改革的各种弊端也开始显现,经济过热和道德滑坡同样需要用传统革命资源来整合民间道德和价值观,使之在最大程度上为政治权威提供支持。
1977年和1990年的雷锋宣传则带有明显的构建新政治权威的倾向。1977年的社论总结道:雷锋的一生是坚持反修防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一生。社论宣称,「我们学习雷锋,……就要永远怀念和崇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1990年的雷锋宣传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信念」,这一年的社论指出:雷锋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在1989年以后的几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再次成为焦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阻力,就需要有新的价值和道德支持来弥补「精神文明」的真空,雷锋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的道德符号获得了空前的宣传。而这种改革合法性的重塑跟树立新的政治领导权威是紧密结合一起的。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日益广泛流行,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又被作为调节社会风气的杠杆。在《人民日报》报导学雷锋事迹的消息中,有几则报导的标题非常形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群众来信表明)群众需要雷锋精神,雷锋活在人民心中」(1987年)、「改革开放年代仍需发扬雷锋精神」(1988年)、「雷锋又回到了群众中间」(1990年)。「需要」、「仍需」、「又回到」这些关键词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介入。雷锋精神中帮助他人、立足本职、服务社会的思想,成为克服经济建设带来的种种不良现象的手段。90年代初开始的「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活动除了鼓励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还达到了鼓励积极生产的目的。
概言之,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在塑造雷锋这个道德模型的毛泽东时代,雷锋更多地是像它的塑造者所希望的那样,担当着乌托邦运动的形象设计师的角色,学雷锋实际上意味着紧跟频繁而严酷的政治运动的风向标。文革结束以后,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具有了更广阔的扩展空间。首先,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政治遗产,雷锋被毛泽东的继承者用作证明其合法性的补充工具。其次,除了强烈的阶级性之外,雷锋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品质被开发出来,具有了普遍学习的意义和价值,雷锋精神因此有了一种道德整合的力量。并且,随着时代的变革,在政治符号和道德符号之间,雷锋的价值逐渐偏向后者,但是,只要需要,雷锋作为政治符号的力量随时可以复苏起来。
*
本文部分内容承蒙高华、张凤阳、李永刚、安替、王强诸位师友的共同讨论,多有启发,在此谨致谢意。不过,若有错误之处,仍由笔者负责。另外,也要感谢丘城晓、张也雷、谌程明等诸位学友在资料整理和程序设计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
本文部分内容承蒙高华、张凤阳、李永刚、安替、王强诸位师友的共同讨论,多有启发,在此谨致谢意。不过,若有错误之处,仍由笔者负责。另外,也要感谢丘城晓、张也雷、谌程明等诸位学友在资料整理和程序设计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
吴海刚 1979年生,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四年级学生。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