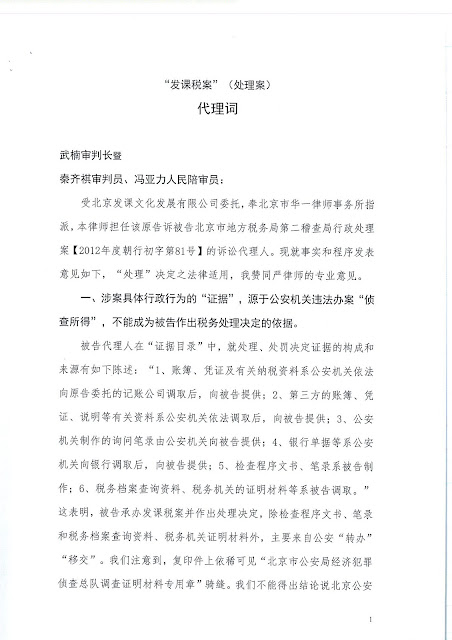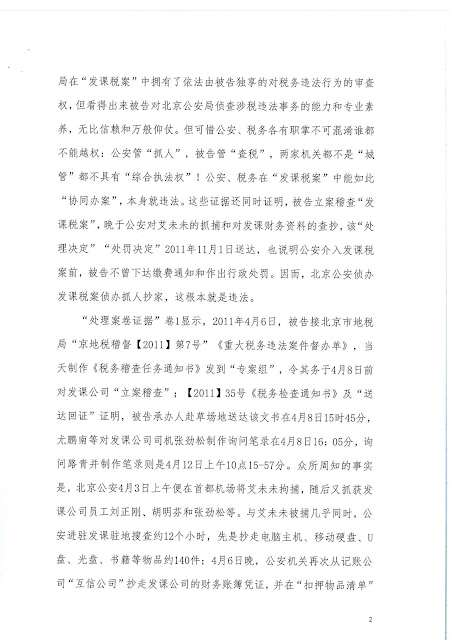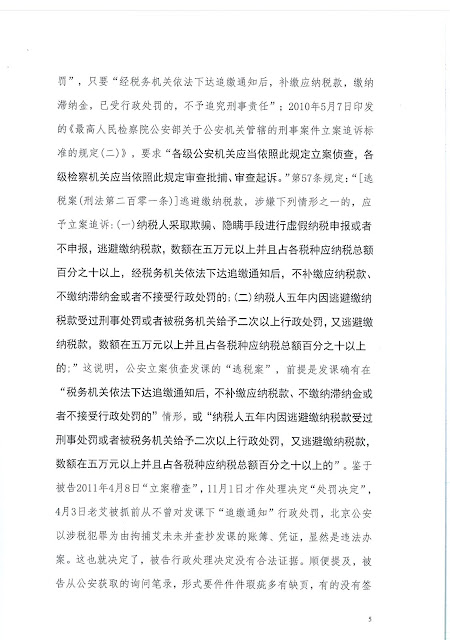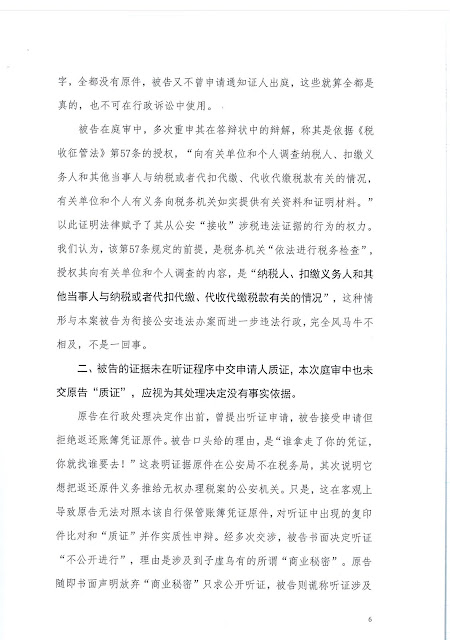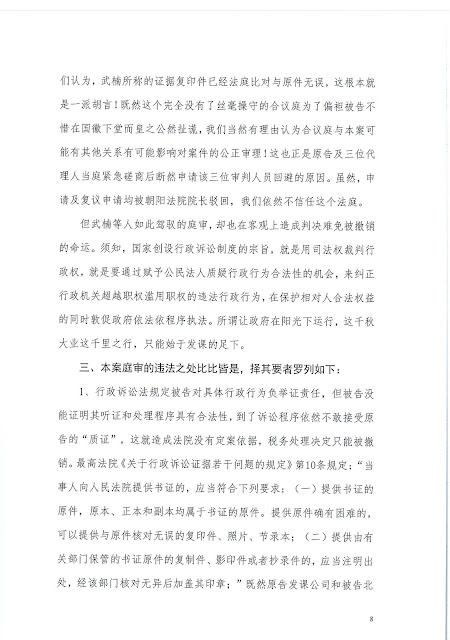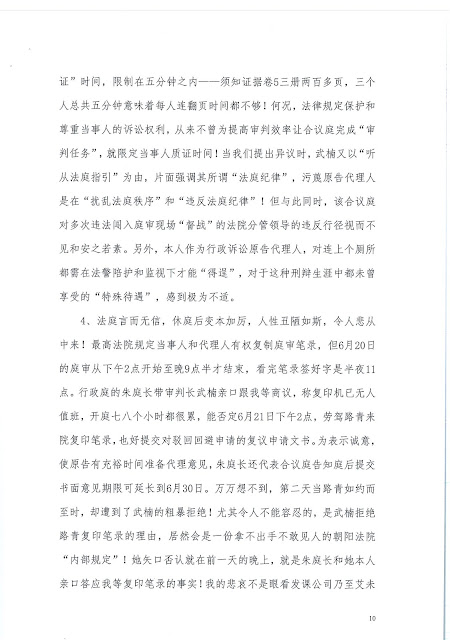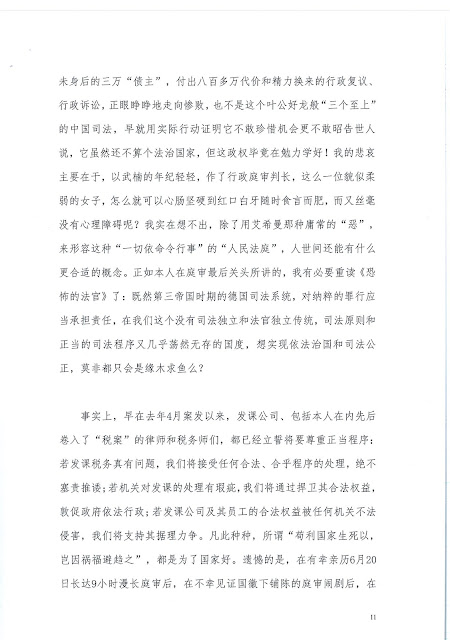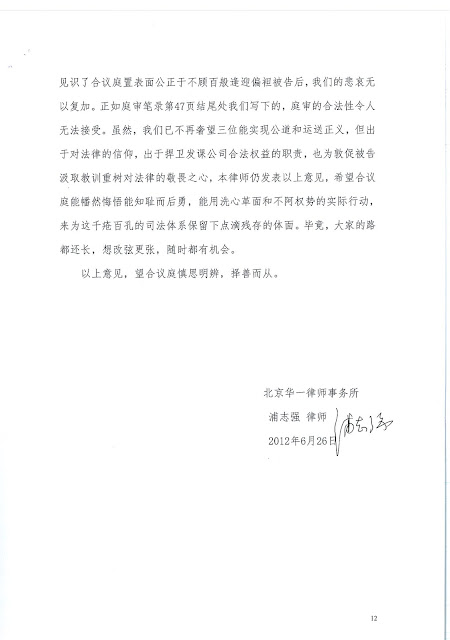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诉 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 代理词(二)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律师提交合议庭:
“发课税案”(处理案)
代理词
武楠审判长暨
秦齐祺审判员、冯亚力人民陪审员:
受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奉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担任该原告诉被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行政处理案【2012年度朝行初字第81号】的诉讼代理人。现就事实和程序发表意见如下,“处理”决定之法律适用,我赞同严律师的专业意见。
一、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源于公安机关违法办案“侦查所得”,不能成为被告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的依据。
被告代理人在“证据目录”中,就处理、处罚决定证据的构成和来源有如下陈述:“1、账簿、凭证及有关纳税资料系公安机关依法向原告委托的记账公司调取后,向被告提供;2、第三方的账簿、凭证、说明等有关资料系公安机关依法调取后,向被告提供;3、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由公安机关向被告提供;4、银行单据等系公安机关向银行调取后,向被告提供;5、检查程序文书、笔录系被告制作;6、税务档案查询资料、税务机关的证明材料等系被告调取。”这表明,被告承办发课税案并作出处理决定,除检查程序文书、笔录和税务档案查询资料、税务机关证明材料外,主要来自公安“转办”“移交”。我们注意到,复印件上依稀可见“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调查证明材料专用章”骑缝。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北京公安局在“发课税案”中拥有了依法由被告独享的对税务违法行为的审查权,但看得出来被告对北京公安局侦查涉税违法事务的能力和专业素养,无比信赖和万般仰仗。但可惜公安、税务各有职掌不可混淆谁都不能越权:公安管“抓人”,被告管“查税”,两家机关都不是“城管”都不具有“综合执法权”!公安、税务在“发课税案”中能如此“协同办案”,本身就违法。这些证据还同时证明,被告立案稽查“发课税案”,晚于公安对艾未未的抓捕和对发课财务资料的查抄,该“处理决定”“处罚决定”2011年11月1日送达,也说明公安介入发课税案前,被告不曾下达缴费通知和作出行政处罚。因而,北京公安侦办发课税案侦办抓人抄家,这根本就是违法。
“处理案卷证据”卷1显示,2011年4月6日,被告接北京市地税局“京地税稽督【2011】第7号”《重大税务违法案件督办单》,当天制作《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发到“专案组”,令其务于4月8日前对发课公司“立案稽查”;【2011】35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承办人赴草场地送达该文书在4月8日15时45分,尤鹏南等对发课公司司机张劲松制作询问笔录在4月8日16:05分,询问路青并制作笔录则是4月12日上午10点15-57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京公安4月3日上午便在首都机场将艾未未拘捕,随后又抓获发课公司员工刘正刚、胡明芬和张劲松等。与艾未未被捕几乎同时,公安进驻发课驻地搜查约12个小时,先是抄走电脑主机、移动硬盘、U盘、光盘、书籍等物品约140件;4月6日晚,公安机关再次从记账公司“互信公司”抄走发课公司的财务账簿凭证,并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名。这说明,被告对发课“立案稽查”是基于北京公安“转办”,发课税案“案源”不是“上级交办”。常识告诉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并不是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的上级。
处理证据卷1收录《涉税事实认定意见书》复印件,上有艾未未6月22日签下的“同意审核意见”字样,但没有艾某代签文书的公司授权;卷8首页,是路青6月22日手书《说明》,她称“公司的主要活动是由艾未未先生和刘正刚先生来负责。本公司的一切事宜由艾未未先生和刘正刚先生来处理。”夫妻俩的上述签字和“说明”,不能赋予被告的“行政处理”以合法性,反说明被告是在联合公安违法办案。
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另一事实,是2011年6月22日艾未未“获释”了!此前他被“监视居住”81天,没任何人任何机关通知他妻子、老母、兄弟、姐姐,没人告知他为什么、犯什么罪、被关在什么地方。这两份文件恰恰在他“获释”前签署——艾氏夫妇称公安威胁他们说,不签字就不放艾未未回家!问题是影响送达效力的破绽,是草率送达属送达错误或曰错误送达:送达对象是纳税人发课公司,不是设计师艾未未!被告派员“勇闯”公安办案点,不为“劫狱”就为把这份与艾未未无关的文书交他,可惜除非他拿得出书面授权,否则对发课公司不产生“送达”的效力,事实上是他没得到过授权!路青手写的“说明”,仅能证明发课公司“主要活动”是由艾未未和刘正刚“负责”,至多证明发课公司经营中“一切事宜”由艾未未和刘正刚“处理”,但这不能证明艾有权替发课接待税务承办人,不能证明他有权“签收法律文书”!退一步讲,即使艾某真有这权限,他不是法定代表人,签收文书对公司生效的前提都只能是取得授权。路青已申明,当天她没有授权艾未未签收这份文件,她不知道公安逼她写下这“说明”是为了干什么,究竟是意味着什么。
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源自公安的“提供”,不说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合法的事实依据:公安机关违法办案,侵犯发课公司乃至艾未未等人合法权益,按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第57条,这些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查该等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包括“(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及“(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尚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上院”项目中诸多证据来自香港,公安“取证”时未向公安部申请,也没提交法定的证明程序对证据真实性加以见证!这些非法取得的证据既然在刑事程序中应被依法排除,当然也就不可能因加盖了“经侦总队”的骑缝章,并“移交”和“提供”给了税务机关,就摇身一变成了合法有效的证据,以此为据作行政处理决定当然会滑天下之大稽!姑且不论艾未未是否犯其他罪行,也无须多虑对艾未未“捉、放”的背景是繁是简,至少公安在税务“动手”前“贸然”对发课税案“霸王硬上弓”,违反了《刑法》和公安部、最高检的禁止性规定,搬起石头砸中了自己的脚。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想抵赖完全没用。
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纳税人真犯“逃税罪”,除非“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只要“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2010年5月7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此规定立案侦查,各级检察机关应当依照此规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第57条规定:“逃税案(刑法第二百零一条)逃避缴纳税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二)纳税人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这说明,公安立案侦查发课的“逃税案”,前提是发课确有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情形,或“纳税人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鉴于被告2011年4月8日“立案稽查”,11月1日才作处理决定“处罚决定”,4月3日艾未未被抓前从不曾对发课下“追缴通知”行政处罚,北京公安以涉税犯罪为由拘捕艾未未并查抄发课的账簿、凭证,显然是违法办案。这也就决定了,被告行政处理决定没有合法证据。顺便提及,被告从公安获取的询问笔录,形式要件件件瑕疵多有缺页,有的没有签字,全都没有原件,被告又不曾申请通知证人出庭,这些就算全都是真的,也不可在行政诉讼中使用。
被告在庭审中,多次重申其在答辩状中的辩解,称其是依据《税收征管法》第57条的授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证明材料。”以此证明法律赋予了其从公安“接收”涉税违法证据的行为的权力。我们认为,该第57条规定的前提,是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授权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的内容,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这种情形与本案被告为衔接公安违法办案而进一步违法行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不是一回事。
二、被告的证据未在听证程序中交申请人质证,本次庭审中也未交原告“质证”,应视为其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
原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作出前,曾提出听证申请,被告接受申请但拒绝返还账簿凭证原件。被告口头给的理由,是“谁拿走了你的凭证,你就找谁要去!”这表明证据原件在公安局不在税务局,其次说明它想把返还原件义务推给无权办理税案的公安机关。只是,这在客观上导致原告无法对照本该自行保管账簿凭证原件,对听证中出现的复印件比对和“质证”并作实质性申辩。经多次交涉,被告书面决定听证“不公开进行”,理由是涉及到子虚乌有的所谓“商业秘密”。原告随即书面声明放弃“商业秘密”只求公开听证,被告则谎称听证涉及第三人“商业秘密”,但又无法给出“第三人”姓甚名谁。2011年7月14日,被告违法举行不公开“听证”,11月1日违法作出涉案“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据悉,被告听证中出示的证据复印件与本案庭审前提交的应诉证据复印件大体相同。但因当时没提供原件“比对”,发课听证代理人夏霖律师和杜延林税务师曾明确表达无法对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严正立场。2011年7月19日,被告电告路青可次日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十八里店派出所“核对”证据原件,因这一“通知”过于不严肃,在“听证”结束后才通知,且派出所并非保管企业财务资料的合法场所,发课拒绝了税务机关的这番“安排”。考虑到现有诉讼证据复印件盖有经侦总队的“调查证明材料专用章”,我们认为被告“调取”的证据仅是复印件,不曾真占有过发课公司账簿、凭证的原件,所有原件至今仍被公安机关非法占有着。因而,未经公开听证程序又未经原告“质证”的复印件,决定了被告的涉案“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和违反法定程序。该处理决定依法应被法院判决撤销。
但在本案庭审中,针对原告质证原件的诉求,武楠审判长和秦齐祺审判员百般阻挠,其违法行径令人齿冷、令人发指。武楠越俎代庖迫不及待地声称:“被告的证据复印件,庭前已经法庭核对,均与证据原件相符。”她多次敲击法槌训斥原告及代理人,称“关于证据原件的问题,法庭已经做出决定,这个问题不许再说了!”这无疑非法剥夺了原告质证原件的诉讼权利。基于上文分析,考虑到诉讼案卷中从不曾出现过公安机关派员到庭提供“原件”供“比对”的记载,我们认为,武楠所称的证据复印件已经法庭比对与原件无误,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既然这个完全没有了丝毫操守的合议庭为了偏袒被告不惜在国徽下堂而皇之公然扯谎,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合议庭与本案可能有其他关系有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这也正是原告及三位代理人当庭紧急磋商后断然申请该三位审判人员回避的原因。虽然,申请及复议申请均被朝阳法院院长驳回,我们依然不信任这个法庭。
但武楠等人如此驾驭的庭审,却也在客观上造成判决难免被撤销的命运。须知,国家创设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就是用司法权裁判行政权,就是要通过赋予公民法人质疑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机会,来纠正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在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敦促政府依法依程序执法。所谓让政府在阳光下运行,这千秋大业这千里之行,只能始于发课的足下。
三、本案庭审的违法之处比比皆是,择其要者罗列如下:
1、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但被告没能证明其听证和处理程序具有合法性,到了诉讼程序依然不敢接受原告的“质证”,这就造成法院没有定案依据,税务处理决定只能被撤销。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二)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既然原告发课公司和被告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局都是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双方举证都应秉承司法解释规定;既然被告不肯提供原件,原告又不曾授权武楠代为“核对”原件与复印件是否相符,而北京公安经侦总队不是法定的保管档案原件的档案馆、资料室等专业机构,它恰恰是违法侦办发课税案的机关,其出具的公文印鉴不能当然确保证据合法和真实。按照该证据规则第35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而,本案被告的“处理决定”,依法应当被撤销。
2、原告曾于法定期限内申请调取证据,法院从未书面通知原告“不予调取”,按证据规则第25条应被理解为申请已被接受。但合议庭却并未以任何方式告知当事人何以未曾调取到任何证据,这显然是对原告诉讼权利的漠视。更有甚者,原告庭前申请通知包括尤鹏南在内的证人出庭,但开庭却意外发现尤鹏南作为被告代理人端坐被告席,我们立即提醒法庭最好让其先行退庭,以免届时需要作证时,他因出席了庭审而丧失作证的资格。岂料,武楠审判长竟以申请尤鹏南作证的理由,须经庭审调查并经合议庭评议后,才能确定是否成立和应否通知证人,循环论证得出荒谬结论即此人可先出庭,至于是否需作证,等休庭后再说!问题是待证事项需要尤某退庭,以此确保原告申请证人的权利在必要时能实现!本案法庭的庸劣,可见一斑。
3、庭审中,武楠合议庭不仅屡次无礼打断原告代理人的发言,还无理限制原告代理人发言时间。她不断喝止我等要求质证原件的诉求,无视每组证据厚薄多寡不同,执意将原告对每组证据复印件的“质证”时间,限制在五分钟之内——须知证据卷5三册九百多页,三个人总共五分钟意味着每人连翻页时间都不够!何况,法律规定保护和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来不曾为提高审判效率让合议庭完成“审判任务”,就限定当事人质证时间!当我们提出异议时,武楠又以“听从法庭指引”为由,片面强调其所谓“法庭纪律”,污蔑原告代理人是在“扰乱法庭秩序”和“违反法庭纪律”!但与此同时,该合议庭对多次违法闯入庭审现场“督战”的法院分管领导的违反行径视而不见和安之若素。另外,本人作为行政诉讼原告代理人,对连上个厕所都需在法警陪护和监视下才能“得逞”,对于这种刑辩生涯中都未曾享受的“特殊待遇”,感到极为不适。
4、法庭言而无信,休庭后变本加厉,人性丑陋如斯,令人悲从中来!最高法院规定当事人和代理人有权复制庭审笔录,但6月20日的庭审从下午2点开始至晚9点半才结束,看完笔录签好字是半夜11点。行政庭的朱军巍庭长带审判长武楠亲口跟我等商议,称复印机已无人值班,开庭七八个小时都很累,能否定6月21日下午2点,劳驾路青来院复印笔录,也好提交对驳回回避申请的复议申请文书。为表示诚意,使原告有充裕时间准备代理意见,朱庭长还代表合议庭告知庭后提交书面意见期限可延长到6月30日。万万想不到,第二天当路青如约而至时,却遭到了武楠的粗暴拒绝!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武楠拒绝路青复印笔录的理由,居然会是一份拿不出手不敢见人的朝阳法院“内部规定”!她矢口否认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就是朱庭长和她本人亲口答应我等复印笔录的事实!我的悲哀不是眼看发课公司乃至艾未未身后的三万“债主”,付出八百多万代价和精力换来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正眼睁睁地走向惨败,也不是这个叶公好龙般“三个至上”的中国司法,早就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不敢珍惜机会更不敢昭告世人说,它虽然还不算个法治国家,但这政权毕竟在勉力学好!我的悲哀主要在于,以武楠的年纪轻轻,作了行政庭审判长,这么一位貌似柔弱的女子,怎么就可以心肠坚硬到红口白牙随时食言而肥,而又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呢?我实在想不出,除了用艾希曼那种庸常的“恶”,来形容这种“一切依命令行事”的“人民法庭”,人世间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概念。正如本人在庭审最后关头所讲的,我有必要重读《恐怖的法官》了:既然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司法系统,对纳粹的罪行应当承担责任,在我们这个没有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传统,司法原则和正当的司法程序又几乎荡然无存的国度,想实现依法治国和司法公正,莫非都只会是缘木求鱼么?
事实上,早在去年4月案发以来,发课公司、包括本人在内先后卷入了“税案”的律师和税务师们,都已经立誓将要尊重正当程序:若发课税务真有问题,我们将接受任何合法、合乎程序的处理,绝不塞责推诿;若机关对发课的处理有瑕疵,我们将通过捍卫其合法权益,敦促政府依法行政;若发课公司及其员工的合法权益被任何机关不法侵害,我们将支持其据理力争。凡此种种,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为了国家好。遗憾的是,在有幸亲历6月20日长达9小时漫长庭审后,在不幸见证国徽下铺陈的庭审闹剧后,在见识了合议庭置表面公正于不顾百般逢迎偏袒被告后,我们的悲哀无以复加。正如庭审笔录第47页结尾处我们写下的,庭审的合法性令人无法接受。虽然,我们已不再奢望三位能实现公道和运送正义,但出于对法律的信仰,出于捍卫发课公司合法权益的职责,也为敦促被告汲取教训重树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本律师仍发表以上意见,希望合议庭能幡然悔悟能知耻而后勇,能用洗心革面和不阿权势的实际行动,来为这千疮百孔的司法体系保留下点滴残存的体面。毕竟,大家的路都还长,想改弦更张,随时都有机会。
以上意见,望合议庭慎思明辨,择善而从。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
浦志强 律师
2012年6月26日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