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洲(绘)
陈洲(绘)我来讲一个三年前的事儿吧。
2015年,我是益行去北京的徒步活动的队员,在徒步的尾声,也就是7月29日的这一天,遭遇了雷闯的性侵(非自愿性关系)。
要回想具体过程非常费劲,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三年,我这三年所有的努力都是忘记这件事,所以要把记忆全封不动的找回来很困难。所以,请大家原谅我记忆的不连续,我尽量负责任的把细节写清楚。
日子是2015年7月28日,我刚刚过二十岁的生日,对于徒步这件事,一直都很期待,觉得如果能完成这件事,一直都很期待,觉得如果能完成这件事,那我迎接2字开头的人生也会有更多勇气。当时我一个人坐了二十几小时的硬座和徒步队伍在内蒙古汇合,那天我发现自己是队伍当中最小的队员,作为一个面子很薄并且在陌生人面前很紧张的人,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照顾,但是其中最热情也是最让我觉得困惑的,就是雷闯。(雷闯中途离开过一次,接触比较多的就是雷闯重新和队伍汇合之后)
在徒步之前,因为朋友的关系,我对雷闯大致有一个印象,是一个很棒的人,他做了很棒的事情,他很被大家认可,而且也一直作为公益界的领袖被看待。所以我一直对于雷闯的照顾,比如买冰淇淋之类的,邀请去单独去景区玩一直觉得很感激,甚至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认可。
现在仔细回想过来,我觉得雷闯在路上的有很多不必要的身体接触,比如他会在我们有单独相处时间的时候搭我的肩,要求我挽他的手,还会要求在我的房间里午休(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雷闯和其他队员一直说,认为我像他的小妹妹,所以要像照顾小妹妹一样照顾我。
在徒步的尾声,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接到了只能三人进入北京市区的要求(这部分由雷闯转述,据队友回忆,本身并没有要求大家不能住在一起,只是要分拨进入北京),当时在挑选谁和雷闯完成最后的行程时,雷闯找到我,他说他认为我是一个背景比较单纯的大学生,并且体力较好,其他人如果继续行走会比较吃力,所以想让我和他一起走到北京。
具体事情的发声就是徒步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因为在路上雷闯和龙飞一直完成预定酒店的工作,出于对他的信任,我丝毫没有担心住宿的问题,以为会和徒步的路上一样,男女分开住。到了那天晚上,我们走到目的地时候,雷闯没有让我在前台登记(说是为了安全),而是等他办好入住手续之后,再进入酒店房间,当我进到房间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对,因为这个房间是一个大床房,只有一张床。我当时跟雷闯说,我觉得这样一张床不合适。但是雷闯的解释是,
“做公益的人都很穷的,大家都是这样混着开房一起睡的”
“你不放心我可以睡地上”(对不起我不记得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有说过)
我很不想和雷闯翻脸,也不知道要怎么表示拒绝,就勉强接受了这样一种挤一挤过一晚的要求。到了晚上的时候,我洗完澡坐到床上(不好意思床睡衣,一直穿着白天穿的臭衣服),雷闯开始抱住我,我当时完全傻眼,用一些很不强硬的口气请求他放开,不停岔开话题,他没有停下,我最后到一个请求是,没有安全措施,不能这样。但是我没想到,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避孕套,最后的结果是我以非常痛苦的方式,和雷闯发生了关系。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性经验,几乎是忍受撕裂感和疼痛,一个人清醒地读过了一夜。
当时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一时没有办法消化这件事,也不知道要怎么告诉其他人,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全是我单独跟雷闯一起徒步的后果,我自己要为这件事负责任。雷闯是个好人,那肯定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女孩子,这种事情才会发生到我身上。最后,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受害人”,也没有办法接受雷闯是“性侵犯”的我,选择和雷闯保持一种关系,让这件事合理化,变得可以忍受。
但是我必须说,我和雷闯的每一秒,都非常痛苦,很难生存。我心里明白,这不是正常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本质是自我欺骗和麻木。但是我毫无办法,哪怕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三年,我依旧认为,我有错。
在2016年的三月份,我和当时徒步路上的另外一个朋友w见面,她开玩笑的告诉我她知道一个雷闯的秘密。我当时心里发凉,我猜测肯定是我类似的事情。果不其然,她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我第一次知道确有其他受害者存在。直到知道了还有其他人,我才终于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我不是雷闯唯一一个秘密。当时我的应对方法是,想要通过写匿名公开信的方式,举报雷闯的所作所为,但是在我准备做的时候。W与雷闯电话沟通,告诉他不要“杀熟”,不要继续犯不成熟的错误。因为W已经和雷闯以私下沟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没有继续再继续通过公开匿名的方式做些什么,而是主动切断了与雷闯的联系,并且愿意相信W的做法是有效的。
今年的暑假,也就是2018年的七月。
我又得知还有其他的受害者,是雷闯机构的实习生/志愿者,虽然她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公开。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这是我完全无法忍受的事情。
坦白来说,我知道实名公开这件事困难重重,我写这段文字之前,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我知道一旦公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风险,也许在雷闯收手之前,我个人的信用就会破产,因为比起相信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学生的自述,更多的人肯定会更倾向于相信一直有道德光环的雷闯。
第二个我很担心的事情是,我无法像举报信优秀范文一样,拿出所谓实锤(比如聊天记录、录音)来证明我的非自愿到底是怎么一个非自愿法,我无法通过文字来陈述这件事对我的伤害,我确实无法为我自己辩护,对于这类的质疑,我只能沉默。
第三个问题是,公开这件事,对我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是为可知的,为了让自己好起来,这三年我能想的办法都去做了,我去打坐、看心理医生、还在乡下呆了一年,这些让我的生活好不容易有些起色,而我又重新回到这件事的漩涡,必须重新去接受心理治疗,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我怕我很难再好起来。
我一直在想,公开这件事这么难,我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很清醒的知道,不管雷闯对我个人做什么弥补性的行为,对我来说,都是很虚弱的补偿。我甚至连公开道歉这种操作,都没有想到过,他的道歉对我个人还有其他受害者,毫无意义,时间不会倒流,我回不去三年前了。
公开这件事的唯一诉求,是希望他真的能住手,或者有一个比他自己更有约束力的团队或者机制能约束他,让他不要伤害热爱公益一心追求公平正义的年轻女性,他不会知道,我们要修复自己,重新开始,有多么难。
我知道我的朋友圈很多都是雷闯的朋友,不管你们信不信,至少,别再推荐自己的女性朋友去徒步或者是实习了,我也是今年才知道,仅仅是2015年的那一次徒步,雷闯套路过的女性,就不止我一个……
2018年7月23日凌晨于北京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录入)




这两天徒步下来,我遇到的最大的苦恼不是炎热,不是劳累,也不是月经,而是做反歧视运动的同伴的性别歧视。两天前我还天真的相信,作为某一种弱势群体的一员可以有同理心体谅别的弱势群体。但这种想法显然是错的,性别歧视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性别意识也是需要学习的。贵机构是一个反歧视的机构,难道不应该先在机构内做好性别平等的知识普及么?像雷闯这样的公益名人性别意识都这么差,在他反乙肝歧视的倡导过程中,却传播着性别歧视,实在太让人心寒。这也让我相信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责怪雷闯,而是觉得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希望机构可以予以重视。
2013.8.19


(雷闯 发送至我 嗯,谢谢来信,谢谢你指出的看法,很感谢。因为在周围不会有人提出,及时提出也不会写长文。 你可以把此文发在益人平邮件组,如果可以的话,可否将部分修改,发到我的博客? 发自我的小米手机)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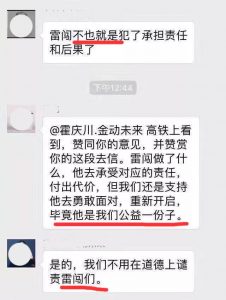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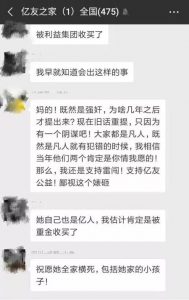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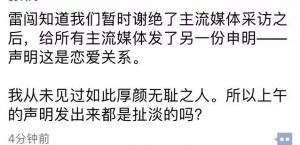
 欢迎扫码加我的个人微信
欢迎扫码加我的个人微信相关阅读: 北京青年报 | 知名公益人雷闯涉性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