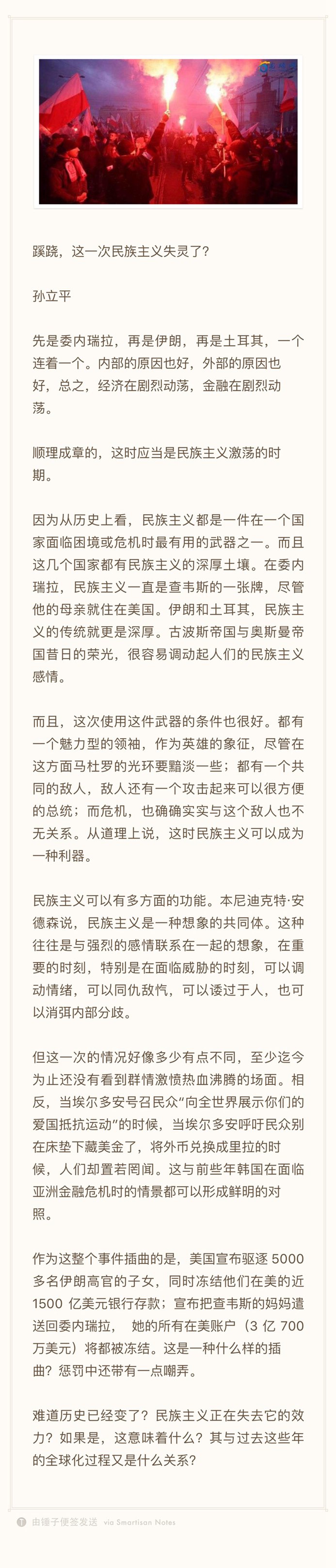先是委内瑞拉,再是伊朗,再是土耳其,一个连着一个。内部的原因也好,外部的原因也好,总之,经济在剧烈动荡,金融在剧烈动荡。
顺理成章的,这时应当是民族主义激荡的时期。
因为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都是一件在一个国家面临困境或危机时最有用的武器之一。而且这几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在委内瑞拉,民族主义一直是查韦斯的一张牌,尽管他的母亲就住在美国。伊朗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传统就更是深厚。古波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荣光,很容易调动起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
而且,这次使用这件武器的条件也很好。都有一个魅力型的领袖,作为英雄的象征,尽管在这方面马杜罗的光环要黯淡一些;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敌人还有一个攻击起来可以很方便的总统;而危机,也确确实实与这个敌人也不无关系。从道理上说,这时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利器。
民族主义可以有多方面的功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往往是与强烈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想象,在重要的时刻,特别是在面临威胁的时刻,可以调动情绪,可以同仇敌忾,可以透过于人,也可以消弭内部分歧。
但这一次的情况好像多少有点不同,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群情激愤热血沸腾的场面。相反,当埃尔多安号召民众“向全世界展示你们的爱国抵抗运动”的时候,当埃尔多安呼吁民众别在床垫下藏美金了,将外币兑换成里拉的时候,人们却置若罔闻。这与前些年韩国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景都可以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为这整个事件插曲的是,美国宣布驱逐5000多名伊朗高官的子女,同时冻结他们在美的近1500亿美元银行存款;宣布把查韦斯的妈妈遣送回委内瑞拉,她的所有在美账户(3亿700万美元)将都被冻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插曲?惩罚中还带有一点嘲弄。
难道历史已经变了?民族主义正在失去它的效力?如果是,这意味着什么?其与过去这些年的全球化过程又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