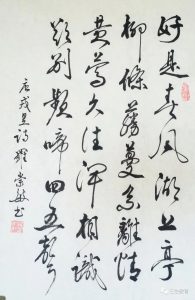作者:郭于华
1、我们健忘是因为有人不让我们记住
我在这里要谈几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记忆与忘却,这个话题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我们常常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对过去无论是经验教训还是荣耀,无论是成功的,还是苦难的东西,把它们都忘掉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悲催”的,也很可耻。
我们不说那么远,我们说五十年的历史,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都不清楚了,都发生扭曲了,或者被遗忘了。再说得近一点,四十年前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今天的人们怎样看待“文革”?怎么样评价它?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真正地进行彻底了解、彻底反思,以至于很多人说要回到“文革”那个时候,而且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迹象,回到“文革”那个时候的迹象,或者是对“文革”的一些美化。
中国人是很骄傲于自己民族有久远的历史的,但是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人否认,说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时候都说中国人民是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独独我们就健忘吗?我们就是一个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不是。我们健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让我们健忘,我们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些具体的案例。
2、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有这么几个事例,前几年官方媒体都有报道,当时我看到以后有非常大的震动,是一种很难以言表的心痛。
河北保定的一个农民叫李红旗,这个哥们儿喜欢收藏,还挣了点儿钱,没事到古董市场去转悠,在古董市场淘东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张烈士证书,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证书,在古董市场里,他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他老婆还埋怨他,说你花钱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他当时买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到时候能卖更多的钱。后来他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他们的家庭,没有送达他们的亲属,却反而出现在旧货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他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以后就开始做一件事,自己往里搭钱,花了十年的时间,按照证书的姓名、大概的地点去寻找,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他找到了四个,当时央视报道的时候他找到了三个,报道了以后又有很多人关注,通过连锁的帮忙,后来找到了第四个,把这四位烈士的证书都送给了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在拿到烈士证书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生是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烈属的话会有很多政策的照顾,会有优待,可有些人没有享受到,所以家里人拿到这个烈士证书的时候真是痛哭号啕,把李红旗视作上苍派来的使者,让他们的亲人终于魂归故里了。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看过电影《集结号》。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检察官,山西人,他在废品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大本,里面有八十四份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是1949年解放太原牺牲战士通知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千辛万苦、散尽家财地去帮这些人送达通知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不只是经济上的困难–因为都很远,散布在全国各地,到一个地方需要当地部门的配合帮助,比如他到民政部门去,或者到哪些部门去了,这些部门的官员说这些东西早失效了。他非常不容易地为其中二十六位烈士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第三个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个老警察,他的家乡那儿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着很多人,他也是用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去要“身份”。
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会引起很多的联想。首先,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送达?这些通知书,这些烈士证为什么没有送达?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无法送达,找不到,难找。它们送达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部门,在什么档案馆里面存档?没有。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流入了废品收购站?他们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是千千万万死去的人中的一个,如果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可能这些人微不足道,因为死的人很多。可是从每一个家庭,从他们亲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家庭的唯一。那么我们就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时–当然都是作为好人好事报道的,是不是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了,我们也会想到,这些人,包括我们大家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民,还要追问普通人的历史命运是什么。难道就像这些人一样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我们在现实中会感觉到我们的命运确实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人应该是历史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仅仅作为数字存在,应该作为主体来存在,这是我们很核心的命题。其实当今社会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社会建设的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性的存在、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是非,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这实际上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我们天天都在说今天的好生活是前人牺牲、奉献换来的,但是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连他们做过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们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记住,这实际上是一种忘恩负义。更为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是,记忆是什么?记忆实际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记忆历史来明辨是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个社会记忆的话,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就会中断,当然也谈不上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没有记忆的话,就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比较,不会有记忆中的历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记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记忆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的作用。这一点大家不难理解。我们有时会谈论,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历史研究方面书籍的出版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书遇到的阻力还大,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去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去了解一段历史、去揭示历史逻辑的写作非常困难。我总是说历史具有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种制约,这让他们产生恐惧。
3、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涂尔干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知历史,来写历史,也是这样,今天对历史有一个重新建构。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已经现成的东西在那里待着,等着我们大家去了解它、去熟悉它,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
我们说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什么?依靠人们的记忆,但是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就像奥威尔在《1984》当中说过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未来。第二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当中以一种近乎天才式的预言,描绘了这种集权主义所能够达到的,对于思想,对于心理,包括对于记忆的控制的极致。而对于记忆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具体方式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奥威尔描述了在这样的国度中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的销毁的,那就是真理部。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种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这样的话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治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历史被修改了,而这种修改的痕迹又全被遮盖掉了,所以人们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权力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4、宏大叙事的历史结构把记忆扭曲了
在历史和权力的关系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遗忘怎么会发生。用大家常常说的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钱看。实际上这是有意识地让人们遗忘。还有一个说法叫不争论,什么事都搁置,实际上就是不去讨论、不去思考,那么这个遗忘是必然发生的。搁在那里,没有人去想,没有人去思考,能不遗忘吗?还有一种说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历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这样一代人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经过;今天大家在探讨知青话题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概念,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听到这个“青春无悔”就来火。知道吗?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要只把眼睛放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为领导人,当了大官,或者成为很成功的商人,成为很成功的学者,那是凤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难,有很多人的生命历程完全是混乱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到农村去了;该成家的时候赶快补读书、补文凭,或者说去工作;到了年富力强的年龄,四十多岁,正是成为家庭的栋梁,也应该是国家栋梁的时候,下岗了。整个生命历程都被打乱了,这样的一代人岂止是一句轻飘飘的“青春无悔”就可以概括的?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如果苦难不被讲述,如果苦难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说法都需要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反思。
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记忆,有些人说“文革”没有那么差,很多人也很开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乐趣。实际上这要从更大的宏观的结构来看,很多记忆发生扭曲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个体与社会。我们的话题是一个关于社会记忆的话题,或者叫集体记忆。我们说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关于自己的,或者关于其家庭的、其先人的历史,这个东西怎么跟一个更大的历史,跟一个宏观的历史发生关联?这就涉及个体和社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莫里斯·哈布瓦赫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实际上他是在谈个体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会涉及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说一种思路。
布迪厄是法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不限于社会学家,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他作过很多的研究。布迪厄说: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很具体的东西来理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关系。
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叫赖特·米尔斯,他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开篇其实就在谈普通人,谈在一个具体的情景当中个体的遭遇、个体的烦恼,是怎么跟一个公共议题上的更大的、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发生联系的。他所提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把具体情景中的个人烦恼和公共议题当中的社会结构打通、贯穿–这样的一种能力,将其概括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具体来说,比如说在一个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衰败,或者说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转型的时候–大家今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大的转折、剧变,那么失业这件事就不是个人能够去化解的问题。我们身边的例子,比如说企业转制,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转型、企业转制的时候出现了大批的失业下岗的工人。尤其是重工业地区,比如说东北,大家都失业下岗了,买断工龄了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能把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吗?说一个人下岗了,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是因为他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是,是因为整个产业都转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当战争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乃至于全球化体系当中的一个内在属性、一个内在的基本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引起的困扰,个人面对它时是无能为力的。
5、制度如何影响了个人生活和记忆
所以我们说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样跟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结构发生关联,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它们进行贯穿。文明本来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说某种文明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怎样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怎样把文明落实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加以理解?其实也不难,可以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上一代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里每个人都要生活在一个人民公社当中,在农村你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城市当中你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一方面有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这样的制约,另一方面有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把人限定了,跟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要吃饭,得有粮票、米票、面票,没有这些票就买不到粮食。买豆腐得有票;买油得有票;布,甚至肥皂、火柴,这些东西都是按票来供应的。这样的一套制度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人是活不了的。你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不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方面就受到限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生存,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这种生活方式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这样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既有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唯有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琐碎的一些经历,那样一些记忆,才会成为非凡的记忆,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