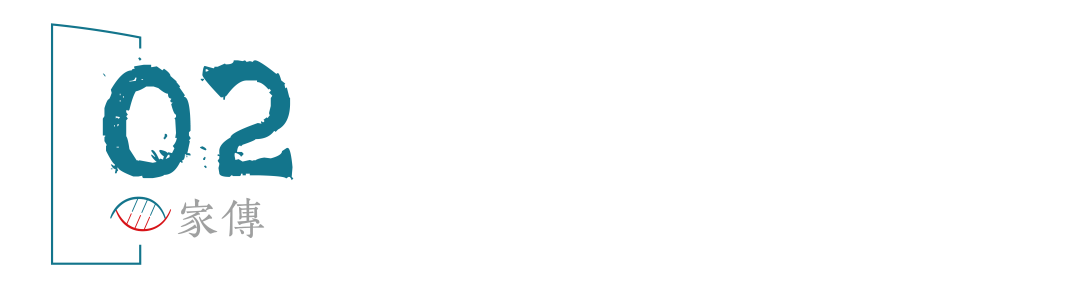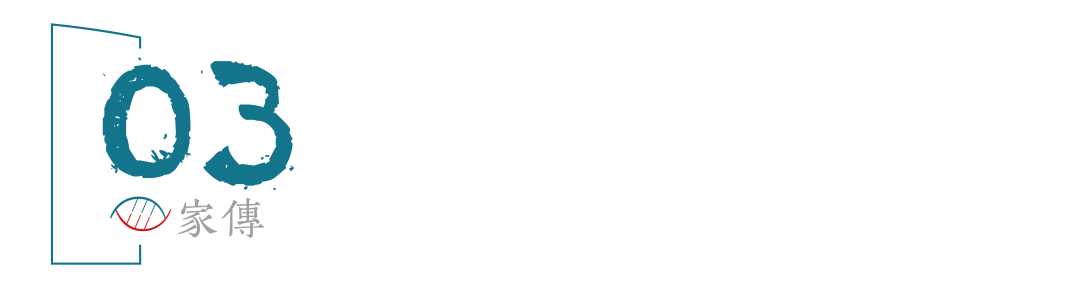如今要活得松快,一位朋友总结了「三巴论」:闭紧嘴巴、夹起尾巴、管牢J巴。
我那就夹起沟子,前段时间去了趟。
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可以搜一下戈壁滩上的古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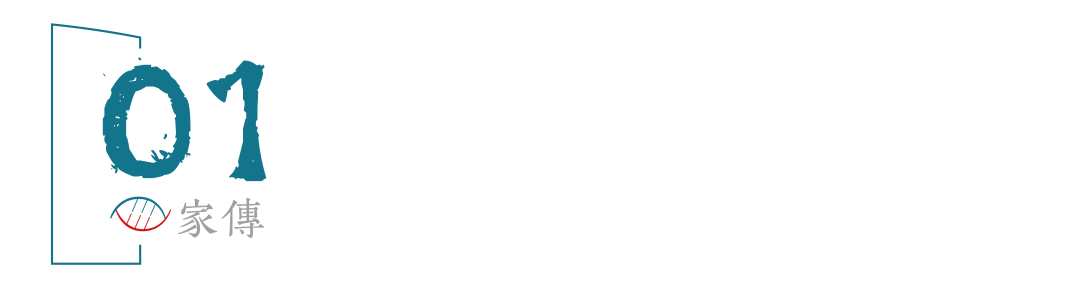
「再不去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
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
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搜到一篇2020年的文章,标题叫《那年清明,我去了夹沟子》。
文章说,一进入林场,迎面驶来一辆摩托,直接横在车前拦住去路,查问来意,作者说只是来看看。
「跟你说吧,你想看什么我知道,我也告诉你,早没了。你赶紧出去。」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再不去看,就算还在,也不让看了。
有年顺道去看赵滑县的故居,也是同等待遇。
但作者还是先前在附近的村里问到了一些东西,恰如我猜想的,正在有计划地抹掉。
一位村民告诉他,村西边那片林子后头沙丘那,有些破房子、土窑子,也都是他们的。前几年倒是还有些,最近有人专门过来,都拆光了。
我去看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幢小房子,看起来近些年还有人用过。
地上还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印,感觉不久前还有人开车进来过。
至于以前荒沙丘上常见的尸骨,都清差不多了。前些日子,还有人专门过来清。
「以前有人过来拍电影,后来还有人过来,说是亲属,捡尸骨说建坟,还要立碑,现在又都没了。」
白骨露于野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午,远处天际,能看到祁连雪山。
有了水利设施,一路都像是青纱账。
近些年西北气候剧变,戈壁滩上也开始长草了。
1957年,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被关进这处成立三年的劳改农场,让他们接受「劳动教养」净化灵魂,同时阻止土地沙化造福社会。
制度设计上,不能让他们继续剥削人民,因此必须自给自足。
从空中看去,是这样的:
被发配这里的,有正式戴帽的,也有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
1958年最高峰时,正式人数为3074人。但因有人死、有人逃,不断补充,因此累积人数不止这个。
当然,也有「才华」被发现而死里逃生的。
美学哲学家高氏尔泰,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发配这里。
但领导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画主席像时,想起他可以「废物利用」,便将他调了回来,从而躲过一劫。
但他这样的人,命运不会就此停止转动。后来他又被金庸他们通过一场小鸟行动,弄到香港去了。
而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按约定接到电话,精神病复发去世了。
这段过往,在他的回忆录体散文集《寻找家园》里详细描述。
我是因为难过读不下去,隔了两年才读完的。
我没拍到居住的窑洞,这是媒体人刘桂明拍摄的:
这里不是戈壁就是盐碱地,根本不可能种庄稼。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死过半。
死了也不得安宁,被活着的夜里偷挖出来吃掉。
到1961年解散时,有人说,3000人只剩下三四百人。
一进去,航拍中的平面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遍地都是坟堆。无名无牌,不知道是谁堆起来的。
我在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下,可能都有尸骨,这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以免惊扰这里的亡灵。
天快要下雨了,电线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电到。加上太阳能播放器在播放佛音,猛一听还以为是坟墓里传来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村民对2020年那位来访者说,早些时候,林子北头的沙窝里,大风一过,就露出尸骨,上了岁数的村民都见过。
但我没看到,只有这些酒瓶之类,应该是祭奠后扔在这里的。
碑下无坟茔
我找到了几块墓碑。
郭淮清应该是名医学专业人士,1897-1957年4月,遗孀张郭氏逝于1973年4月。
2011年4月,后人在这里立碑,应该是合葬。
可见郭淮清之死,对于家族的痛,绵延半个世纪而不能解。
难解处在于,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而郭淮清则在当年4月份即已去世?
不知是否家属未能查清。
赵登魁,1898-1957,遗孀陈秀珍逝于1996年,碑立于2006年。
想来,死在这里的赵登魁连骨头都找不到,无法「回家」,于是后人只好将墓碑树在这处荒原上,见证风沙猎猎。
其他冤魂,则无陵无碑,消失在这茫茫戈壁,从此再也无人提起。
像哈佛博士海归、上海人董坚毅,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到了这。
还有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被二哥傅作义劝回国,1957年到这里挖排碱沟。
……
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将心照明月?
奈何。
细看之下,墓地的朝向都不一样,我猜是不是都朝着家乡的方向。
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在努力寻找归处。
我们在努力不遗忘。
毕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这也是我写家传、抢救家庭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