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来自曾在中国常住了近 10 年的记者 Poppy。她是中国高速发展的见证者,好的坏的,她都记录了下来,直到不便再作记录。回忆在中国的生活经历,Poppy 用了“触碰”这个词。“触碰”,既是她和中国的关系,也是她眼里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农耕生活习惯、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延续,人与人的交往法则、模糊的阶级差异等等,都通过“触碰”这一行为体现了出来。而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像处于资本主义晚期的地方那样,“触碰”在中国也逐渐消逝。当人们将中西方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立起来时,Poppy 的文章让人五味杂陈。这种区隔,也成了“触碰”消失的一部分。文化差异、利益冲突固然存在,但 Poppy 的叙述提醒我们,从肉体到精神,人与人之间的“触碰”是可能的、可爱的、重要的。就像生命诞生起就需要肢体触碰来获得快乐,我们总会突破区隔,在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中,更好地活下去。
本文获得作者授权,在《单读》独家发布。
触碰
撰文 Poppy Sebag-Montefiore
译者 牛雪琛
1999 年至 2007 年间,我时常住在中国。我曾在 BBC 北京分部担任记者,最初我并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来到中国的,但是这份工作让我在中国住了很久。还记得我报道的第一则新闻,是关于中国发射首架载人航天飞船的。我们播报了宇航员杨立伟从太空传回的消息,当时他正在独自环绕地球轨道,他的声音带着电波的滋滋声,他说:“一切都好。”好的方面可能已经被描述了很多遍了,但当时是 2003 年,中国正在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全球超级大国。我们的新闻焦点从激动人心的发展和希望,转向高速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后果:污染;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获得平等的权利;土地被地方官员非法没收并出售的人们,向国家要求赔偿却遭到殴打。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但低谷部分令人感伤。当我在中国的任期快结束时,我已采访过许多处于恐惧状态中的人,以至于自己也受到了影响。被拘留了几次之后,我变得有些妄想症似的,回到家后还会检查一下窗帘的后面。
在变成这种状态之前,我深深地热爱着中国。每天醒来我都像婴儿观察世界一样地学习新鲜事物:中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每天我都受到感动,很多时候这些感动来自朋友,陌生人,打扫我家旁边街道的女士,卖水的小贩,餐馆老板,下棋的老人,很多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大多数人我都没有机会再次遇到了。我被拽着,推着,拉着,靠着,我的手被握着。正是通过这些微小的、亲密的、姿态性的时刻,我开始渐渐看到宏观变化是如何烙印在人们的关系和内心生活中的。
人与人之间的触碰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其中的规则与我故乡的规则正好相反。北京的街头,人与人之间有无数的触碰。如果人们在街上经过时手臂互相撞到或蹭到,无需道歉,甚至无需躲开;排队的时候陌生人有可能会整个地靠在别人身上。似乎每个人都可以以某种方式接触其他人的身体。买家和小贩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会握着彼此的手臂;人们打牌的时候会挤在一起;到了晚上,女人们会在舞厅手挽着手,像跳华尔兹一样相拥着穿过街角。
公共场合中陌生人之间的触碰像一首有着丰富曲调的小曲,曲调中既不包含性,也不涉及暴力,但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没错,有时候由于空间不足,你可能会被人靠着,或是被踩几脚。不过还有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想靠着的人,或者被他人选择。再比如,当你拿着大蒜讨价还价后准备离开时,你可能会感到有人抓住了你,你也会抓住对方的手臂。触碰是一种非常细致的交流工具,你可以通过触碰来表达你对他人一些行为的感谢,比如他们微笑时眼中闪烁的亮光,协商时的直率,还有他们展现出的善意。
这种触碰使我既振奋又不安。有时我觉得自己像弹力球一样,在不同人之间弹来弹去,跳来跳去。被城市中不同的手臂推着,拉着。如果说这个国家像一个过分严格的父亲,那么这个民族、社会或街上的人就是安抚人心的母亲。人们对待彼此的方式给人感觉就像一个温柔的摇篮。有时候太多人的触碰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压迫感,但是大多数时候触碰就像一种润滑剂,可以缓解城市中的各种日常活动带来的压力,使人感到温暖。
我想记录下这种无意识的触碰,把它保留下来,我感觉陌生人之间这种轻松的身体状态可能无法在高速运转的城市中幸存下来。这种触碰非常可见,非常显著,我将相机从固定机位的采访拍摄中解放出来,带着它走到街头。
几周前,我发现了一卷标记着“触碰 I ”的录像带,它是我 2005 至 2006 年间在北京拍的。斜斜的阳光照在人们的脸上,反射出粉金色的光。市中心附近的服装店开着门,门口放着电子音乐,音乐在门外宽阔的步行街上飘扬。顾客在门口排成长队,我的相机对准了这条长队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
我尤其注意到两个男人,一个年长些,可能六十多岁,身着军装式的外套,戴着灰色的羊毛帽子。他前面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淡紫色的外套,外套上散布着小小的黄色油漆斑点。这两个人互相靠着,但都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然后穿着卡其色衣服的人转身看了一下他身后排队的人有没有变多,每次他这么做的时候都会撞到他身后的人。
他们越来越靠近队列的前面。我也和他们一起行动,音乐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的心脏也跟着跳动,就像这音乐是从人体内放大到街道上一样。穿淡紫色外套的男人开始扭动身体。随着咚咚的音乐他左右摆动着。他站在队列旁边,一边跳舞一边努力保暖,每次踩准鼓点的时候,他的右臂都会随着音乐节奏不断地撞到穿卡其色外套男人的肚子上。穿卡其色外套的男人并没有躲开,他完全没注意到,他很自在。现在在我看来,这两个人完全不认识这件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按理说应该关系非常亲密才行,比如是朋友,同事,或者家人,最有可能的关系是父子。然后我快进磁带,跳到下一幕。这两个人被放大了,我带着相机走到他们两个身边,他们俩的面孔占满了镜头。我问道:“你从哪里来?”
“河北,”淡紫色外套的男人说。
“湖北,”卡其色外套的男子说。
河北位于黄河以北,湖北地处洞庭湖以北。这两个省份相距约六百英里。
我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他们俩同时回答了我:
卡其色外套的男人说:“我们不认识。”
“不认识。”另一个人也说道。
伦敦的莎特博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上坐落着一家名为幸运小屋迷你市场(Lucky House Mini Market)的小店,沿着这家店旁一个昏暗破旧的楼梯往上走,就能看到一家传统中医诊所。范医生六十来岁,大约三十年前离开中国。我回伦敦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所描述的是一种乡土式的相处之道:农民之间的触碰。我一直在努力让北京的人们思考这种触碰,因为这种触碰对他们来说太过显而易见,以至于几乎难以察觉 。但是范医生在给我做足底推拿的时候告诉我,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常常保持着相互尊重的距离,他们之间比较拘谨。我住在中国的那段时期,正值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高峰期,当时的北京是一个由很多村庄组成的城市,这些村庄彼此叠置,相互环绕。范医生说,在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确实靠得更近,同性别之间尤其明显,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毛泽东将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向农民学习。可能正因如此,所有人都更了解彼此的工作,也更熟识彼此。
触摸是中国传统医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会通过感受病人手腕上的六种不同的脉象来做出诊断。按摩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皮肤上的穴位与特定的内脏有关,触摸这些穴位可以释放毒素,减轻炎症。有一次我从上海前往东海的一个小岛,需要坐十一个小时的船。途中我痛经很严重,住我下铺的一位陌生的女士握住我的手,找到了手上与子宫相对应的穴位。她为我按压那个穴位,然后疼痛就这样逐渐消失了。
在中文里“养生”的意思是“养育生命”。它是指人们通过按摩、运动和饮食等医学手段来积极追求健康。这种健康观不只意味着健身房会员和注射螺旋藻,更是一种通过积蓄身体能量来提高健康水平和康健感受的古老观念。这种健康观中还杂糅着一种人们由于缺乏医保福利而产生的担忧——有必要在年老后不成为自己唯一的孩子太大的经济负担。当我住在北京时,养生并没有在城市里的老年人中变得太过商业化。养生是一种身体智慧,是人对身体需要的满足:有时需要人细致谋划,有时又需要人们借助根深蒂固的本能去行动。正是因此,人们才会晚上聚集在舞厅跳舞,早上又一起在公园锻炼身体。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大家一起聚在街头满足身体需求的活动,像一种对国家的抵抗,是人们之间的密谋。尽管这种团结一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社会主义的熏陶和鼓励,但它还是掌握在人们自己手中的,像是一种个人自治的形式。在这个审查严格的地方,出版和媒体上的话不一定可信,这种活动就像一种感官的公共空间,它使人们能感受到彼此。这样聚在一起也可以使人们从彼此身上获得快乐和活力,而无需再从他人那里索取任何东西。这是一种互惠、开放、关注个人需求的活动。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抛弃界线,接受陌生人自信、自然的碰触的时候。当时我在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那座位于黄灰色山脉间的拉卜楞寺里,和其他人一同观看藏传佛教的节日活动。这时一个大概八十来岁的男人从我身后走过来,搂住了我的腰。我转过身去,一开始感到羞愤,后来变得困惑。因为他甚至都没看我一眼,只是把脖子搭在我的肩上,望向演出的方向。他紧紧地抓着我,对他来说,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在站着看表演的同时不摔倒。他像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借用了我的身体。我估摸着他这么做是不是别有用心,然后发现他并没有其他目的,我记得我当时忍不住为这个男人靠着我而感到高兴。几乎有点欣喜若狂。一个老人可以用我的身体来帮助自己站着看演出,这很棒。我让我的朋友从后面和前面给我们拍了照片。照片中我的脸神采奕奕。这种感觉可以比拟站在自己喜欢的画前所获得的精神振奋。但这种触碰更为强大:它随时都可以发生,往往是在人最不经意的时候,而且它是一种亲身体验,它的媒介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种触碰能带给你一种弗洛伊德所形容的“海洋般的感觉”(oceanic feeling)——当婴儿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轮廓,在自我还没有形成之前,当个人与其他一切合为一体时——才会有的那种感觉。
我有时会疑惑,触碰会不会有其阴暗的一面。如果这种接触他人身体的权利被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滥用的话,这会不会就是地方官员雇佣暴徒殴打上访者,以此阻止他们向“上级”投诉的部分原因呢?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和随意是否助长了官员之间的腐败,使他们更容易巴结其他领导?
当时在中国,各个年龄段的异性朋友和同僚之间的接触都很克制,几乎是禁忌。如果我在分别时拥抱或亲吻我的男性朋友,他们会感到尴尬和局促。但是同性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年轻人之间,肢体接触非常普遍。女人们常常挽着胳膊走路。男人们会互相揽着肩膀走路。建筑工地上的人会坐在彼此的腿上。
柏拉图式的触碰有自己的情欲表达。它让你能直接感受到友谊带给你的爱、活力和同志般的情谊。朋友之间的接触部分得到许可并变得尤为突出,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内部禁止性接触。性只限于婚姻,但即使在婚姻中,性也不应该分散人们对革命的热爱。
在这些观念下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夫妻,在公共场合对彼此的行为举止都一本正经。我曾经坐在北京后海的湖边和一些老人谈论他们在家里与配偶之间的触碰,他们显得非常实事求是。一位女士告诉我,性就是性,不包括接吻这部分。另一位老人告诉我,他和妻子的关系是“我给她搓背,她给我搓背”。
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最畅销的一篇短篇小说叫《我爱美元》(I Love Dollars),故事的叙述者朱文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当他的父亲来大城市看望他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能为父亲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帮他跟别人发生关系。朱文沉思道:“仔细想想,我意识到父亲是一个性欲很强的人,只是他生不逢时,在他那个时代,性欲不叫性欲,而叫理想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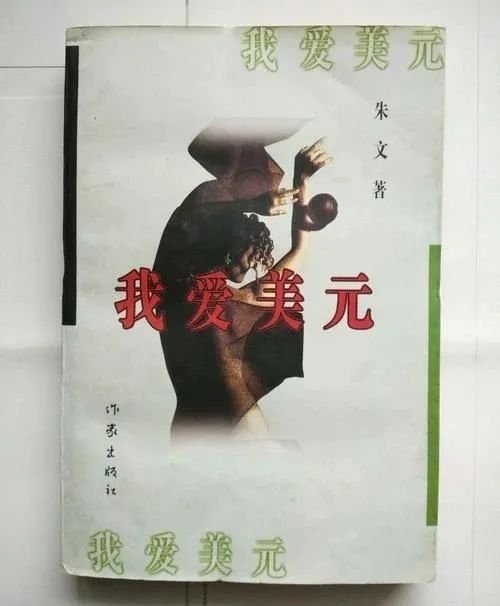
《我爱美元》
朱文 著
作家出版社 出版
我的感觉是,北京的老一代人对身体和亲密生活的体验,主要是在街上发生的。
搬回伦敦后,我每年都会回北京待几周。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我回了北京。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晚我也在北京。当时街头突然开始了自发的狂欢活动。人们把汽车丢在路中间。所有人都兴高采烈,中国终于被全世界接受了。七年后的 2008 年,北京人似乎一直在默默忍受着奥运。北京 2001 年的大部分城区都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精心筹备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被彻底清洗了一遍。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所有隐约有疑点的人都被撤职了。城市的“精神文明委员会”禁止了一些不文明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不文明排队,以及轻浮的肢体语言。政府给老年志愿者们发了红袖章和一个电话号码,发现问题可以打电话报告。这些志愿者们经常坐在人行道旁的长椅上,监视着自己的地盘。这座城市被束缚住了。我没有去看比赛,我拿出相机记录下了人们触碰彼此的方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那种古老的触碰方式了。沿着林荫大道,我的取景器里满是年轻夫妇和恋人紧握的双手和挽着的手臂。
触碰被从街头搬到家中,从公共场合转移到私人生活中。它正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越来越与性相关。如今的年轻一代在街上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解放后的性观念。他们互相给予对方温柔、关注和关怀,有时他们的姿态是一种全球化的、浪漫的、好莱坞式的方式。在《我爱美元》里,朱文的父亲在读了朱文的一些作品后,抱怨这些作品都是关于性的,他说:“作家应该带给人们一些积极的东西,一些值得尊敬的东西,理想,抱负,民主,自由,诸如此类。”朱文回答道:“爸爸,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于性之中。”对于朱文父亲这一代人来说,性被强行升华为理想主义,而对朱文来说,那些崭新的、可能难以实现的理想被升华为性。
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人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从别人身边挤过去,新的中产阶级有了一席之地。超市接管了街边的市场,易货交易消失了,买东西不需要太多的交流,事实上顾客们经常一边买东西一边跟别人打电话。现在有大量农民工居住在这个城市,但他们通常被隔离开了,他们睡在建筑工地的宿舍里,不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以前我几乎分不清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的差异惊人,从衣着、面孔、被围观的程度等方面都可以区分。城市居民会和农民工保持距离,人们越来越恐惧这些移工,担心他们可能想要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东西。人们开始把农民工描述成是肮脏、危险、需要远离的人。他们成了不可触碰者。
不知怎的,那种寡淡又老套的苏联风格的房间——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领导人的画像,墙漆可能蹭在你的衣服上——成为了身体被社会所控制的人们的背景墙。而晚期资本主义建筑、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私人拥有且专人巡逻的闪闪发光的商场、钢塔、地铁——成为了强调更多的公共规范、更好的行为、更多的自我意识,以及和陌生人保持更远距离的空间。
我曾在北京的一家诊所里接受按摩疗法的治疗,那家诊所是一家大型中医医院的分所,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按摩师戴上了扎人的塑料手套。他告诉我,现在城市里的人鱼龙混杂,这样做是为了卫生。
突然之间,按摩和针灸并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了。治疗心理疾病的谈话节目都上电视了。人们不再通过触碰来治疗疾病,而更倾向于坐在严格禁止身体接触的治疗师的房间。治疗师是一个崭新的职业,中国现在还缺少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心理治疗师,一些认为自己应该更多地了解自己内心生活的人开始受训成为治疗师和分析师。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的主要城市将会有 40 万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2007 年搬回伦敦后,我很想念那种公众场合的触碰。我经常在街上撞到别人,走在我身边的朋友们会很尴尬,帮我道歉,因为被我撞到的人很生气,但我却意识不到。不过很快,我又适应了伦敦的街道,对陌生人造成的喧嚣和拥挤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易怒。然后,我做了一件每个 21 世纪初的、有感觉系统的人都会做的事情:找一位神经科学家聊聊。
弗朗西斯·麦格龙(Francis McGlone)的工作,主要针对我们皮肤中一种被称为 C-触觉( C-tactile afferents)的神经感受器。它们最近才在人类身上被发现,存在于人体有毛发的皮肤里,尤其是背部、躯干、头皮、脸和前臂上。它们会对缓慢和轻柔的触碰做出反应。C-触觉不存在于生殖器里。每当受到抚摸的刺激时,C-触觉会让人产生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不是性快感,而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触碰所带来的那种感觉。神经学家称之为“社会触碰”。
这些神经纤维非常古老,它们诞生于生物生命的早期,早在语言之前,甚至在那些告诉我们移开手使其远离疼痛的感受器形成之前。这表明它们对保护生命和健康至关重要。在远古时期,我们需要周围有人帮助我们梳理毛发和清除寄生虫。和别人待在一起时,我们收获的是快乐。
麦格龙对现代性凌驾于进化过程之上的时刻很感兴趣。他认为,我们从出生起就需要 C- 触觉的刺激,这样才能使大脑的社交部分发育良好。我告诉他我在北京注意到的现象,他说可能穷人需要比富人更多地聚在一起,因为他们更依赖彼此生存。在他描述的科学世界里,每个人都在独自进行研究,完成各自的工作。他说,社交距离也有用,它让大脑得以处理其他事情。
但弗朗西斯·麦格龙将人们聚在了一起。他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成立了一个体感与情感神经研究小组(Somatosensory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Group),组内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 C-触觉与我们情感生活之间的关系。珍恩·莫顿(Jayne Morton)是柴郡警察局的按摩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她说我的描述让她想起了 20 世纪 70 年代她长大的地方威拉尔(Wirral),她的父母曾经在那里经营着一个社交俱乐部。男人们会在一个房间里一起躺着,而女人们会在另一个房间里手挽手地挤坐在一起。这些男人们服完了兵役,他们需要和有类似经历的人保持密切联系。而女人们,习惯了男人们不在家时和其他也在家带孩子的朋友们在一起。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大量的教堂关闭了,学校和俱乐部也关门了。大家都散了。晚上人们会和家人待在一起。后来,威拉尔变得更加多样,文化更加多元,但始终再没有大型聚会中心了。珍恩说,80 年代那会儿,由于离婚率提高,为学校家长组织活动变得更加困难,因为继父母和父母通常不愿意待在一个房间里。
这让我想到,当社区分裂后,夫妇们的关系是否也变得更加脆弱?我曾在北京街头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亲密方式是否都变成了个人的压力?在一个团体里,也许我们能够重温幼年时的一些亲密,比如母亲温柔的抚摸。我们现在仍旧渴望那种关怀,它让我们感觉很好,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和信任的人在一起——即使这种信任感只有一瞬间。
分开时弗朗西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触碰过对方,前一天晚饭后说再见时也没有。我们面对面地、非常专业地聊了好几个小时。但当他指引我沿着大学特建的走廊走出去时,他拍了拍我的背。这个行为让我觉得他认为我没事。这让我感觉很好。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令人震惊,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都在反思他们与时代“脱节”了。学者们称自己与时代脱节了,一位主持人承认 BBC 与时代脱节了,整个伦敦更是都被认为与外部脱节了。现在,语言几乎不可信。我们处于后接触、后真相的状态中。现在的社会还将如何沟通呢?
可能当人们感觉彼此之间遥不可及的时候,焦虑和恐惧都会激增。人们不光感受到和精英阶层之间的距离,还感受到和其他大多数人之间的距离。教堂、社区中心已经关闭;临时合同越来越多,人们社交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少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们挤在一起,互相分享,用双手创造世界。
这种原子化的分散状态也许会使一些人觉得受到移民群体的威胁,因为他们似乎拥有大多数人所没有的东西——发挥作用的“社区”。新移民通常会因为工作、信仰、饮食、母语,而彼此亲近,建立起移民内部的关系网。他们需要依赖彼此生存下去。触碰的意义在于它是可视的、可见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凝聚力,那么那些已经孤立的人,会进一步感到被排斥在移民社区那种可见的亲密感之外,也会感到被排斥在那些使我们团结和互惠互利的纽带之外。
生命中最紧急的时刻——出生和哀悼——都需要我们与最亲近的人保持越来越远的距离。我们与所爱之人以及和其他人之间的亲疏程度也受到宏观力量的影响:经济、意识形态、身份认同。这座大都市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生活的细节之中。我的实验表明,无论身在何处,我们不会这样困住自己。只需要在一个观念不同的世界待上几个月,我们的身体就会随之做出反应,适应环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再次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