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事”发生后的第十二年,何谦说起整个事件的经过,还是会泣不成声。
2018年的“米兔”浪潮中,她用化名半公开地书写自己曾遭遇过的一系列性骚扰和“未遂”事件,并在其中指认:前《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发起人邓飞,曾在她2009年实习期间对她实施性骚扰 (注:因为何谦不确定如何准确定义这一行为,此处说法与她的实名自述保持一致,具体见下文) 行为。这篇文章后来被她的朋友邹思聪发布在个人公众号,名为《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引起公众关注。
文章发布当天,邓飞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已向免费午餐基金等项目团队表明不再参与工作”,并同时退出所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同年11 月, 邹思聪被邓飞起诉名誉侵权,何谦则在参与庭前会议作证之后,被追加为第二被告。
2020年11月10 日,案件开庭前一天,何谦通过社交媒体公布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公开应诉。朋友们从远方赶到法院门口声援,大家都对胜诉怀抱希望。
然而,两个月后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她们输了。
如今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被告一方已经提起上诉。对何谦来说,这也意味着她的“ 任务”还没有终止:她要消化掉所有情绪,继续自己不被允许的讲述。
“为什么选中了我?”
何谦说,伤害发生的那一刻,她感到自己整个人被完全否定了。
“更准确地说,我觉得当时我就是一滩烂泥。”她在多年后看到李沧东的电影《诗》,用剧中的台词为当时那种难以言表的状态找到了复述的语言:“杏子掉在地上,摔烂或者被踩碎,准备来生。”她想起曾经自己也像是“摔烂在地上的烂泥”,恨不得渗透到地底,直接消失。
在自述文章中,她描述了当年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凤凰周刊》“首席老师” 邓飞约她见面聊选题,又以“人多不能谈话” 为由将她带到自己住的酒店。进入房间后,邓飞“瞬间变了一个人”,“ 扑过来,抱我,强吻,脱我的衣服,脱了自己的裤子“。
第二天,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偷偷丢掉了身上的衣服,一遍遍擦洗身体。那之后她没再和邓飞见过面,业务上也没有产生交集。一切看起来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但心理上的影响无法抹去。多年之后,那一幕还会在梦里重现。
当时何谦21岁,在她的视角里,邓飞是“ 铁肩担道义”的媒体人前辈,一个年长她许多的“中年人” ,网络账户头像还是和女儿的合影——这一切营造了安全的假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她想不明白,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而且为什么选中了我?”
自我厌恶涌上来,剥夺了她的价值感,逼迫她细数自己的“愚蠢” ,也促使她相信,自己只是经历了一次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导致的意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她的反抗,无论邓飞最初想要做什么,最后似乎都没有达成目的。这是一起“ 未遂”事件,她是幸运的。
直到9年后,她在一系列针对性骚扰的举报中再一次看见了邓飞的名字。
2018年7月,至少6 名网友通过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曝光邓飞对女性的性骚扰行为,包括言语挑逗、搭肩膀、拉手、搂腰、强吻、“壁咚”等。
彼时邓飞已从知名调查记者转身公益,成为“免费午餐”“ 儿童五防(防性侵、防拐、防校园暴力、防灾害、防意外)”等项目的发起人。一位当事人写道,她因“免费午餐 ”项目与邓飞产生合作,邓飞在饭局上多次试图搭她肩膀时,说了一句“你的眼睛好像我女儿啊” 。这句话让她一度自责自己过于敏感。然而之后,邓飞就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突然一把抱住了她。
微博用户@不要怕不要怂 针对邓飞的指控,当天她收到数则讲述被邓飞性骚扰经历的私信。
根据网友的叙述,这起事件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 壁咚”事件则是在2015年,均在何谦的遭遇之后。这两个数字刺痛了何谦。她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这个人换了行业,进入公益圈,还能继续这么做?
她的愤怒一部分指向邓飞,一部分却是指向自己——如果当初选择说出来,而不是保持沉默,是不是就能让对方没有机会再伤害其他人?
出于愧疚,同时是也希望表达支持,何谦联系上了两位当事女生。她说:“我有和你们相似的经历,我准备把它写出来。”
“我从一开始就是实名的”
如果有人回看何谦在2018年的自述,会发现它甚至不是一篇“控诉 ”,而是来自性暴力幸存者艰难的自我剖白。她回忆暴力发生的场景时措辞谨慎,却又直白地将自己的创伤暴露在公众面前。
在后来不止一次的梦里,我困在同一个场景大声尖叫。空间变形后破裂消失,我的身体消失,只有尖叫还在。
就像生了一场持久的慢性病,身体早有迹象和病症,对伤痛的感知却是后置的。延迟的。
——何谦(不再沉默的C)
除了邓飞,何谦也提到曾遭遇来自其他业内前辈的“未遂” 行为,最终让她感到对媒体行业的憧憬彻底坍塌。她意识到没有人可以逃脱这样的现状:她可以脱离实习生的身份,但对方依然在行业里掌握资源和人脉,只要**这种权力关系存在一天,她就势必会继续害怕他们**。
发生在职场的性暴力给她带来挥之不去的噩梦,她从噩梦中回溯到自己的童年,想起曾在公共场合被陌生成年男性猥亵的经历,也想起发生在不同场景之下,更多的“未遂 ”事件。这些经验在沉默中被长期掩藏,留下的是身为女性的耻感和对性、以及对异性的恐惧。她形容自己是“自相矛盾的病人” ,既怀疑自己在某一刻被迫变“脏”,又相信是自己的“ 不纯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但在近十年后,其他女性共同的经验让她明白:性本身就是权力关系,所谓的“纯洁” 更是危险的枷锁。为了承担这一共同的命运,她要把自己记得的一切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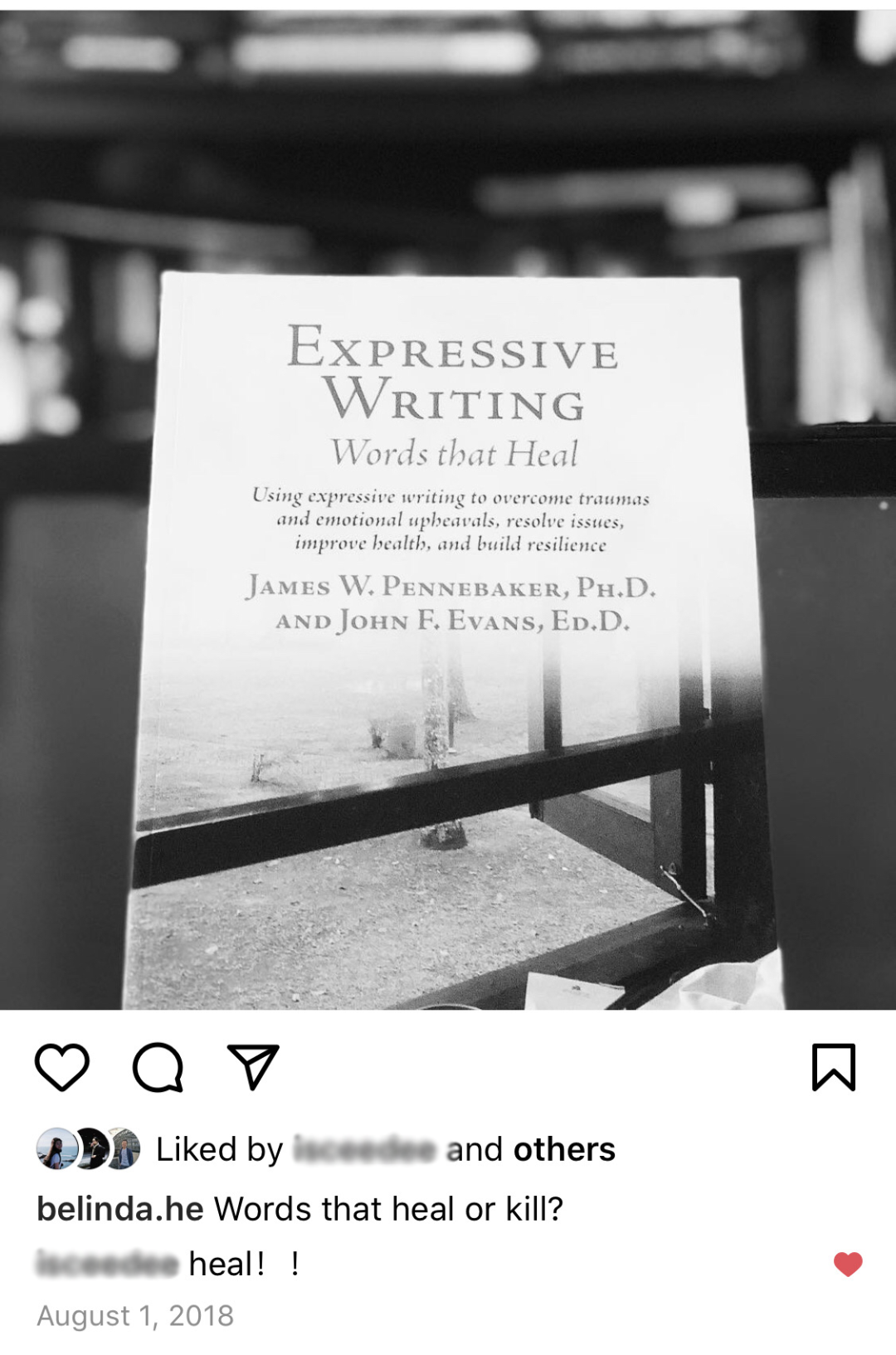
心理医生送给何谦的书。2018年8月1日,匿名发布自述后,何谦发布了这条Ins
最开始的自述写在锤子便签上,何谦将它选择性地发给了一些人,有过去曾听她倾诉相关经历的朋友——后来他们大部分都成为了案件的证人,也有一些在公益圈和媒体圈较为信任的前辈,其中包括邹思聪在内的几位伙伴主动提供平台帮助她传播。
在公开发布的文章里,她化名为“C”,但由于文章第一时间被转发至凤凰的编辑群,使得“圈内 ”许多人,包括她匿名指控的其他几名性骚扰者,也不可避免地迅速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在公众看来,我当时是匿名的,但其实对于这个圈子或者是我们之间有共同交集的这一部分人来讲,我从一开始就是实名的,他们都能知道我是谁。 ”
何谦受到了一些攻击,但支持的声音更多。她经历了一个短暂而放松的“黄金期” ,一部分是源于讲述带来的释放感,另一方面,她没想到书写自己的经历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像投出一颗小石子,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但意料之外的打击很快降临了。
2018年9月,何谦的文章发布一个月后,一位曾通过个人公众号实名支持她的前辈发了一篇新的推送《我杀死了邓飞》,称自己只是为了 “不辜负信任”才发文支持何谦,当晚即感到“ 焦灼不安”,觉得将这位“视自己为兄长 ”的人“判处了死刑” 。
这篇文章大部分的内容何谦都没有看进去,在哭到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她只记得文中结尾处的一句话:作者称自己梳理分析了从两边求证获得的信息,只能确定一个事实,“我不能判断对邓飞的指控就是真实的 ”。
她对“求证”的说法感到难以置信。她记得自己出于感激和信任向对方讲述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中还有一些她的个人信息,但作为当事人的她从未被对方明确征询“求证”。
之后这位“前辈”又来联系她,称她自述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可能存在记忆植入”,理由是曾在一些关于性侵的故事中看到和她的描述相似的反应,“从常理上来看,应当是邓飞实施并完成了强奸行为,(何谦)才会有这样的举动”。言下之意,因为何谦并没有遭遇“真实的强奸”,因此她所描述的感受和当下的反应是虚假的。
屏幕上的话语在何谦眼前爆炸开来。在此之前,她收到过别人的匿名攻击。她在美国读博,就有传言说她是富二代,在美国有房有别墅;她需要授课,有人就问“你的学生知道你在撒谎吗 ”;有人指责她与其他人合谋构陷邓飞,要“毁了他的前途”…… 但直到这一刻,来自信任之人的言语利刃才终于刺穿了她。
“前辈”后来还告诉何谦,自己对她和邓飞之间的关系存疑。这句话成为公开指控以来,何谦体验到最令人崩溃的“荡妇羞辱”:“我觉得他其实不是要杀死那个人,而是要杀死我。”
何谦和“前辈”的聊天记录最终被截取后作为邓飞一方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而在当时,她和朋友们已经意识到正在面临的法律风险,不仅是因为曾经的支持者立场骤变,也因为邹思聪和另一位发布文章的媒体人收到“中间人 ”传话,威胁不删帖就起诉。何谦担心自己私人账号发布的内容会变成带来更多攻击的靶子,她不敢再相信别人,改掉了自己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关闭了朋友圈,再也没有发新的内容。
“我就是那个女生C”
何谦再次“开口” 是在2021年的第一天,她发了两年来第一条朋友圈,向朋友们问好,感谢他们的支持。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她以为自己“有生之年都不会再发朋友圈了 ”。
一切都来自于2018年。在那个黑暗的冬天,何谦经历了背叛、指责,紧接着朋友又成为了被告,要忙于准备应诉事宜。在社交媒体上,她只想把自己整个人藏起来。而正是在那时,她认识了其他幸存者。
通过律师,她先是接触到“朱军案” 的当事人弦子,又以此为契机和更多经历相似的女性建立了联系。女生之间成立了幸存者互助小组,话题从相互鼓励、安慰,聊到猫猫狗狗和做饭,各种日常琐事。何谦觉得她们彼此“缘分都挺大” ,她找机会和好几位当事人在线下见了面,线上也一直保持联系。小组对她来说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供给”,她从中获取能量,也尽力为其他求助者提供支持,和她们一起面对外界的质疑乃至谩骂。
她也认识了日本第一位公开相貌和姓名指控性侵的女性、《黑箱》的作者伊藤诗织。2019年7 月,何谦回国参与庭前会议,恰逢伊藤诗织出席中国的新书发布宣传活动。她们在北京的分享会上见面,相互拥抱。随后何谦的律师牵线,邀请她做成都场活动的翻译。
何谦原本有一些顾虑,担心自己在现场会控制不住情绪,影响活动效果。但当时在场的朋友都很热情,律师也鼓励她参加,于是她答应了。事实上,她在翻译时确实哭了出来。这一幕后来被现场观众拍照发到了微博上:“翻译姐姐中途哽咽许多次,伊藤时不时摸摸她的背。 ”
伊藤诗织成都分享会结束后的观众记录。有朋友特意转给了何谦。
弦子身在北京,以连线的形式参与了分享。何谦听见她对自己喊话,让她不要哭,振作起来。
那场分享会的主题何谦印象很深,叫“黑暗中握紧的手” ,讲女性社群内部的共情。她还特地邀请妈妈一起参加。活动结束后,一向回避性侵话题的妈妈告诉何谦,她觉得伊藤诗织的分享特别好。
伊藤诗织、弦子、何谦和主办方在北京分享会上的合影
后来她们在美国再次见面,她听到了伊藤诗织曾经试图自杀的经历:当时伊藤诗织被不断的上诉折磨得精疲力竭,案子却还是看不到结果,突然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已经站出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决定终结自己的生命。所幸被及时抢救回来。
直到2019年底,伊藤诗织的案子胜诉,她在媒体面前公开了这段经历,在公众目睹之下,一位“ 受害者”的故事终于迎来了光明的结局。但在那个私人的讲述时刻,何谦说:“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抱着她一起哭。”
何谦自己曾在接受心理治疗途中数次被医生安排紧急救援和防自杀干预,并在2019 年被诊断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最严重的时候,她连走在街上都感到害怕,仅仅因为得知邓飞曾在某一时间去过她所在的城市。她不能想象自己和他身处同一个空间,甚至不能想象他曾经出现过。
2009年那一次经历之后,她曾无比庆幸自己和邓飞的工作再无交集,因此他们的名字也不用在报道中并列在一起。但她还是被迫在不同的场合看见或听见这个名字。在2018年一次朋友组织的聚会上,同席者突然提到自己和邓飞很熟,这件事几乎让何谦当场崩溃。她以为出国后已经远离那个名字、远离自己的经历很多年了,这一刻却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 “我就觉得那是个鸿门宴。”尽管他们对她是当事人一事可能并不知情。
网络上攻击何谦的人一直指责她在“暗处” ,而邓飞在“明处”。在何谦看来,原本是为了自我保护采取的匿名,却让她在某些时刻不得不沉默地忍受痛苦,也让她遭受了许多匿名攻击;而始终在“明处”的邓飞,顶着公益人物的光环,却可以继续收获朋友和同僚的公开支持。
于是开庭前一天,她通过微博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大家好,我是何谦,被邓飞起诉的那个‘女生C’。”

何谦和伊藤诗织在旧金山逛街时买了一对耳钉,图案是流泪的眼睛,一人分了一只。她们把那条街命名为“治愈街”。
实名站出来后,何谦和失联许久的同学、校友重新取得了联系,更幸运的是同期在《凤凰周刊》的其他实习生也辗转找到了她。
这一举动让她找回了自己的一部分能量:“原来我也可以像他(邓飞)那样。”小组的伙伴们在她背后。作为幸存者,她顶住压力,和施暴者一样站在了明处。
何谦一位师妹的朋友圈。2018年何谦匿名发出自述后,她认出了何谦并取得联系。哭泣的场景何谦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师妹的见证帮助她收藏了那个瞬间。
“争一线生机”
2021年1月 6日,邹思聪在公众号上公布了一审结果《邓飞诉邹思聪何谦案,一审判决书在这里了》,并表示会继续上诉。法院判决书显示:何谦 “虽尽其所能以‘亲历者’ 的视角向法庭回溯文中封闭空间的事件”,但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地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因此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邹思聪提出,法院过度保护名誉权,而未充分考量这种情况下何谦作为当事人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何谦当年没有及时录音录像,没有报警,她今天就不能宣之于口吗? ”
这一结果对何谦而言是残酷的。在庭前会议和庭审当中,她要反复回忆事件发生的细节,同时应对原告律师和法庭的质询,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而邓飞一方并没有完成初步的举证义务,并且在庭前会议上作虚假陈述 ,声称“完全不认识何谦、没加过QQ好友,对何谦没有印象”,这些说辞已经被何谦一方提供的证据所驳斥,但在判决书中完全没有对于此事的回应。
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公益律师李莹在微博发文评论,认为“令人毫不迟疑地确信”这样的举证标准对于民事诉讼来说明显过高,更不符合性骚扰、性侵害、家庭暴力等案件的特殊性。 在她所代理的“社工明星刘猛涉性骚扰”一案中,“性骚扰或性侵当事人双方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主张受害一方陈述的可信度应大于另一方”,这一主张获得法庭认可,帮助当事人争取到了相应的权益。
邓飞称“完全不认识何谦”,而判决书显示,被告方提交了邓飞与何谦之间存在过工作关系的证明。(来源:微信公众号“思聪的南方纪事”)
对于之后的上诉,何谦的想法是“争一线生机”。对她来说,最坏的结果不是二审再次败诉,而是当性暴力幸存者被反诉名誉侵权成为一种惯例,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声援其他幸存者。“那一切会是‘功亏一篑’,痛苦会无限循环,这才是比败诉更糟糕的结果。”
她期待即使是败诉也可以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讨论,让大家看到司法系统留给性骚扰和性侵案件当事人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从而推动一些改变。“**某种意义上,在经历审判的人并不是作为被告的我们,其实应该是整个中国法律系统在经受检验,在被‘审判’。**”
2020年11月11日,庭审当天,何谦和邹思聪的支持者们聚集在法院门前。法院采纳邓飞的请求,以“保护被告隐私”的名义对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庭审结束后,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发布报道,但后被删除,在场的行动者留下了较为完整的记录:《何谦,知晓你姓名时刻,我们与你同在》
何谦说最让她感动的是,场外的支持者中,除了弦子,其他人都是她不认识也从未见过的,她们自发去到现场。支持者带来的花束是向日葵和代表勇敢的洋甘菊。后来弦子的案件开庭时,何谦给她定了相似的花,特别选了洋甘菊。
回想起庭前会议的过程,当时何谦以证人的身份出庭,讲了几分钟后,她突然发现被告席上哭成一片。一位律师几乎泣不成声,律师助理一边哭一边做庭审记录,眼泪一滴一滴砸在电脑键盘上。
何谦自己的情绪也非常激动,中途不得不数次暂停发言。她背负着多重压力,既担心回应得不够好,又担心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律师发挥。但她还是迫切地继续说下去。有两位不在场的证人和她站在一起,当年正是她们对邓飞的控诉,促使何谦公开了自己的经历,此时她们为了支持何谦提供了自己的证词 ——即使这意味着她们要向法庭递交真实的身份信息,同时让原告方获知了这些信息。
在痛苦和自我怀疑中逃离酒店的那一天,何谦并没想到事件在多年之后还会产生如此多的后续,也没有想到,这件原本想要彻底忘记的事情,会因为各种原因被不断提起,直到在脑海里刻印得越来越深。
这是一种复杂的感受:讲述即是在重复伤害发生的过程,但讲述本身也赋予她力量。
曾经她因为无法定义“未遂” 事件给自己造成的影响,甚至一度希望自己没有挣脱——如果性侵“真实地 ”发生过,或许会有更多人愿意相信她的叙述,她的感受也才能得到承认。
但在米兔运动中,她的声音和众多女性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真实而有力地揭穿那些用以掩盖性暴力的谎言:她们不是“侥幸 ”,不是“不小心” ,不是“愚蠢”,更不是 “肮脏”。她们遭受的伤害来源于施暴者试图否定她们的意志,剥夺她们对身体的掌控,也来自纵容性暴力的社会文化和缺乏性别视角的司法系统。对自身真实经历的讲述,是她们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基本的权利。
“‘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何谦在2018年自述中留下的问题,如今也在拷问着这个我们身处的社会:当幸存者难以从现有司法程序中获得保护,甚至为了推动司法的进步需要“ 以身试法”,谁又能够替她们承受其中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