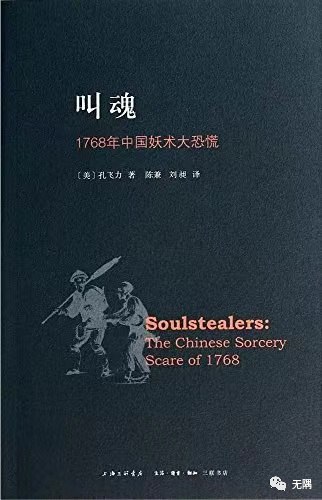2021年4月,一个“境外势力”的幽灵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上空盘桓。据称,一位擅长打昆特牌、扑克牌、游戏王和三国杀的78岁老人是这个幽灵的召唤者。尽管“境外势力”让所有网民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互联网社群都将境外势力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对境外势力的不同表达和理解,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境外势力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未知观念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或者说,当由于内卷化生活的剧压和由于启蒙教育的确实使得本就缺乏同理心的网民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与自身观念不同乃至相悖的观点时,这种恐慌与猎巫就开始了。
对于“境外势力”的恐慌与猎巫向中国互联网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事件从—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有些男性网民只是由于无法接受男性气质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特权被冲击,就去到与此次事件完全不相关的淘宝店铺进行侮辱和谩骂,他们所展现的除了丑恶的妒忌,还有彻骨的仇恨。而在著名的小众文化社交平台豆瓣关停了一系列和女性主义相关的群组后,部分被中国网民称为“粉红女权”的豆瓣网友,则称与她们对立,包括封停她们的豆瓣都是“境外势力”。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甚至还引用历代领袖的语录来证明对立者是“境外势力”。当然,她们先前的行为并没有任何错误,历代领袖的语录也都是真理,但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指控境外势力,这实在是让观察者们前所未见了。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境外势力”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网民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女权”(或者男权,请注意,括号内没有引号)“压迫”或资本盘剥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和正在遭受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内卷化程度加剧、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劳资矛盾加剧和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社会流动性的急剧下降和特权的合法化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能从把奔驰开进故宫的人们那里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境外势力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境外势力这样的存在是自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但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勾结境外势力而破坏自己的和平与安宁——虽然这种和平与安宁大概只是996ICU——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境外势力、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相互指控他人为境外势力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在网络上相互指控他人为境外势力所折射出来的,是人们现实中的无权无势状态。
任何人——无论所属社群——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境外势力。其实,把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当作替罪羊是决策者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决策者相信,境外势力的阴谋由女权主义者执行,而性少数群体则是他们雇佣来的跑腿。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决策者对他们大张挞伐,这些人也成为决策者的某种恐惧的最佳陪衬。至于普通民众,他们早已把境外势力的帽子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头上。他们也有自己的成见;女权主义者是危险的外来者,由于不认同父权性别秩序而背弃文化传统——虽然从理论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上天然不可靠,是潜在的第五纵队。当决策者对这些易受攻击的少数群体进行挞伐时,网民们是不会不对之表示欢迎的;否则的话,在抵御境外势力的问题上,他们就只有指望对新思潮持不可知态度的官僚们为他们提供微不足道的保护了。
笔者的前辈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将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描述为一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孔飞力认为,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是“受困扰社会”和“零和社会”的微妙结合。一方面,它在政治-文化上仍然保存着旧时代中国社会的很多印记,比如贤能政治和精英政治,以及近年来越发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传统以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奇迹增长使得民众产生了类似西方人对进步和经济成长的信念,但这种信念由于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相较西方式的“随着发展,一部分人会受益,而没有人会被损害”,中国民众则更强烈地相信,“随着发展,所有人都会受益,没有人会被损害,而一切问题都会被解决”。那么,显而易见地,在这一信念破灭之前,当有人被损害的时候,只要这个人不是自己,民众就倾向于将这个人非人化。
与帝制后期的中国相类似,今天对普通民众而言,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非常渺茫——实际上,声称自己是普通民众而拥有接近政治权力的可能性的人,基本都出自于中下层官僚、知识精英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企业主家庭。这种“普通人能够接近政治权力”的认知错位,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阶层流动的意识形态表现。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民众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因此,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后,我愿意引用我的前辈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语: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