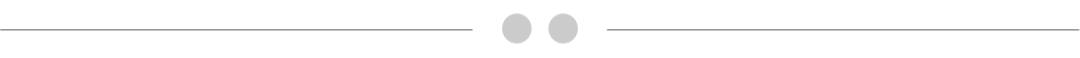作者:苏有若、苏小七 / 看理想(Weixin ID:ikanlixiang )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是最近经常出现的一句话。
疫情、战争、女性权益、人身伤害事件,个体遭遇的痛苦与不公被直接摆在我们眼前,难免让人感到愤怒、难过和焦虑。
想要对话,网络上却充斥着仇恨、偏执的声音;想有所行动,却难以撼动巨大的体系;就连去发声,言说的空间都被进一步收窄。
生活中充斥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无力感,“政治性抑郁”开始被越来越多人提及,甚至成为了一种隐性却极为普遍的症状。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当下蔓延的“政治性抑郁”。一篇文章无法提供对症下药的药物,但希望通过这次的梳理和讨论,能够让你获得一些共情、力量和希冀。
01. 时代与现实,让我们无法逃离
当下,互联网让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也就更加能实时地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们很容易看到超出生活范围的社会议题,发声、参与讨论,但往往在接近问题核心时,却发现背后是难以撼动的、错综复杂而巨大的系统,不是个体可以轻易解决的。
被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无力感捕获,被弥漫的焦虑所影响甚至吞噬,是许多人的真实感受。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无从逃离所处的时代。
当互联网在算法辅助下争夺流量时,带来了更加碎片化也更加极化的观念表述。被信息流裹挟的我们,注意力变得分散,很难静下心来,进行长期系统性的学习与思考。
从日常生活到国际视野,身份政治、信仰、族群与国别,都在经历这样的极化和崩裂。
一些人在持续重复性输出“噪音”,一些人选择了退回话语的同温层,一些人陷入了更深的沉默。而简单粗暴地否定、举报,乃至对“异见”的消音,则进一步逼仄了我们的交流空间。
当真正的对话难以开展,看似热闹的互联网,反而把我们放逐到了一个个观念孤岛上。
公共事务、新闻政治带来了巨大无力感和孤独感,让人大部分时间里持续感到情绪低落或烦躁,并有悲伤、空虚或绝望的想法和感受时,那很可能遭遇了“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的情绪。
5年前,心理学家吕松(Robert Lusson)专门写作了名为《政治性抑郁》的文章,论述这一现象,这些年,政治性抑郁已经逐渐从一种隐喻层面的症候,演变为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抑郁症标准的临床症状。
目前,病症层面的政治性抑郁,本身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经历,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也可能是政治环境,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总体来说,政治性抑郁有一条重要表现:个体开始失去能够掌控自我命运的想法和感觉。
同时,患有政治性抑郁的人,往往也是共情能力更为丰富的人。他们能够在这些社会事件里,天然共情到类似的恐惧与悲伤,担忧时代灰尘造就的大山,有可能无差别地降临在所有人头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有些人相对幸运地成长于比较“privilege”(特权/优待)的环境;有的人天生相对“钝感”,已经学会了更好地屏蔽负面信息的情绪刺激;更有一些人,带着某种“大局观”站在高处发言,选择性回避他人的具体痛苦。
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里总结过一个临床研究现象:抑郁症患者往往“不会表现出过分的利己主义”,他们更少控制欲,也更少对未来抱有“不现实的预期”。
类似角度的研究指出,被政治性抑郁困扰的人群,常常也拥有更敏锐的感受力、同理心。
同时,因为他们很难用自我膨胀的姿态面对世界,也减少了许多“兴高采烈”的感受。换言之,他们往往拥有谦虚的美德,经常自我反思与自我怀疑。
02. 该如何面对政治性抑郁的情绪?
正在爆发的俄乌战争,被称为是“短视频时代”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跟以往相比,死亡、灾难甚至核威慑等残酷的实时战况,如同瀑布一般推送到我们眼前,消息鱼龙混杂,种种对立、激烈的情绪也都被挑动起来。
2月28日,新闻传播学者方可成在“新闻实验室newsletter”中呼吁,从情绪健康的角度,我们不必“实时”关注进展,尤其是泡在社交网络上,通过不断反复刷新页面来获取新动态,因为:
“真真假假、夸大其词、挑动情绪的消息,会白白消耗你的能量。即便是完全真实的消息,在刚刚被报道出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背景补充和意义解读的,而绝大多数人自己并不具备解读其意义的能力。
……自主回答这些问题,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范围,但它们可以轻易让你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和焦虑的状态。这时更好的选择,是等一等,不必以小时、分钟来更新你对战况的了解,每天集中阅读一次汇总和解读足矣。”
“而合理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则是这个年代每个人都要学会的事情”,在这篇通讯文章最后,方可成写到。
在吕松的研究里,如果任由政治性抑郁的情绪一直持续下去,会引发疾病的状态,甚至让身体健康状况恶化。
因为,承载着我们情绪的神经系统,也是有负荷限度的。抑郁引发的情绪过载,很容易引发生理性的变化,也就是临床心理学上的“情绪的躯体化症状”,比如:胸闷、头疼、失眠、呼吸急促、身体发抖等。
有位朋友分享了自己对抗政治性抑郁的经历,过去新闻很容易让她陷入政治性抑郁的情绪里。最近有所好转,她尝试的改进方法是在关注事件时,内心里已经默默划好一条边界,保留思考、情感和愤怒的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关照自己的情绪。
有意识地识别自身情绪的饱和度,是干预政治性抑郁的第一步。
由于引发政治性抑郁的源头,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是相对明确的。在感觉不适时,你可以深呼一口气,暗示自己将开始改善情绪,并及时远离引发焦虑的信息源,转移注意力到那些有助于缓解或改善情绪的外部事物上:比如阳光(研究证明,充足的光照能改善情绪)、绿植、宠物、美食等。
当情绪持续不适,可以更有计划性地在多个维度上调整生活节奏,比如从运动、饮食、睡眠等多方面着手。(如有必要,建议及时就医。)
同抑郁症一样,政治性抑郁也常常不被理解和正视,被认为“想得太多”“总喜欢看负面”,招致“杞人忧天”的评价。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往往加重了受这种情绪困扰的人的自我怀疑。
实操证明,与不同人真诚地沟通交流,也能有效地改善情绪。比如在许多心理干预的小组中,一群人聚在一起,轮流讲述自己的遭遇与感受。这种不局限于同温层之间的对话,非单向度的讲述与情绪交流,还能够帮助彼此交换信息,获得新的视角和处理方法。
回想疫情初期,也是许多人遭遇政治性抑郁的时刻,那时,互联网上自发成立了许多互助小组和社区。在这些社群中,人们不只是得到情绪的安慰,更因为交换信息得到了现实中的实际帮助,从而有效缓解了身心压力。
03. “焦虑的反面是具体”
与情绪共处,只是治愈政治性抑郁的第一步。在现实中,仍会不断出现新的让人感到无力的事件。
政治性抑郁带来的情绪波动,不止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使得我们丧失生活的动力,好像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象力和坚持信仰是不重要的,而自己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
心理学教授王芳在看理想节目《问题出现就来告诉我》中,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了应对这种情绪的解决办法。
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是因为它很难解决,想解决却总解决不了,不免让人陷入挫败,状态变得更消极。这时候,如果我们还要花费所剩无几的心力,去处理内疚、自责、怀疑等连带情绪,可能就更难面对现状,甚至容易彻底失控。
最佳的选择,当然是尽量远离造成困扰的源头,但政治性抑郁的特点就在于,大环境让人避无可避。
这时候,不如把关注点暂时从问题上移开,专注于做一些在广泛意义上更有益的事情。你会发现,只要行动起来,即便它并不针对现存的某个问题,但也一定会像流动的水一样,汇集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深度探讨抑郁症的书籍《正午之魔》里,介绍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农帕莉通过行动,帮助许多女性从严重政治性抑郁与战争创伤中脱离。
上世纪70年代起,柬埔寨经历了多年的残酷内战,社会机制被完全抹杀,逾1/4的人口遭到屠戮。整个国家的公民,都生存在一种深深的恐惧与麻木情绪之中。
当时许多女性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问题,其他医生束手无策,只能任她们自生自灭。但农帕莉没有放弃她们,她先引导她们,忘记抑郁的存在——虽然抑郁症无法移除,但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尽力淡忘不好的回忆。
随后,农帕莉带着她们尝试工作,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擅长的技能,并找到为自己骄傲的部分。
最后,农帕莉带她们一起到蒸汽室洗澡,互相触摸、梳洗——这些行动,是灵长类最原始的社会化形式之一。身体孤立也是一种情绪折磨,会导致情感孤立、抑郁直至崩溃,而这种回归原始、以之作为人类间的社会化力量,让人惊叹却又显得十分自然。
农帕莉总结,“遗忘、工作与爱作为整体一起践行,让这些事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改变就会发生……她们慢慢理解了,然后就做好了重回世界的准备。”
农帕莉的努力非常成功,她本人其实也是内战的受害者,遭遇过痛苦的磨难。但通过不断的救助行动,她不仅治愈了自己,还与被救助的妇女们组成一个慷慨助人的社群,从业形成了一条不断传递影响的链条。
有一位叫@狐狸 的朋友也向我们分享了类似的感受,“我真正感到(政治性抑郁)有所好转,不是靠退缩来完成的,而是我发现我其实拥有一些力量,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虽然时常感觉这世界就是一艘将要沉没的破航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为同行的乘客,在花瓶里插一朵玫瑰。”
去做一件事,再让这件事驱使你去做另一件事,用一个良性循环来替代一个恶性循环。只一步一个脚印,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可以成功地迈向明天、迈向明年。
“大多数巨大的转变,都是靠我们用数百个微不足道、甚至难以察觉的一小步累积而来的”,心理学书籍《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么写。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虽然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安、无力感,但如果真的行动起来,好像感觉也就“没空去焦虑”了。
周轶君在《圆桌派》里说,“焦虑的反面是具体”,要对抗看似混沌的巨大疑惑,就是需要在行动中把它拆解为一个个可能的分支和要通关的关卡。这样不止能获得强烈的真实感和掌控感,甚至还能够推动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历史上很多巨大的改变,就发生在这样的“小事”之中,上世纪70年代,在捷克,几乎所有文化艺术与出版行为都只能在地下进行,但还是有人没有放弃,在不可能之处尽量做事,那些事情甚至本来就没有特定的意图。比如不自觉改写了历史的乐队“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最初只是一群爱模仿西方摇滚乐队的年轻人,他们的力量只在于对音乐的一腔热情。
如《无权者的权力》所总结,“任何普通个体(“无权者”)基于自身本能感受的一些行动,都具有特定的价值……所谓希望,并非确信事情总会有好结果,而是不论结局如何,也肯定有其价值。”
政治性抑郁让人感到无助,但这样实践下来,你会慢慢拥有一种笃定感:行动,就是存在主义上的生命价值所在。
就像要治疗身体疾病,除了用药之外,还需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我们的情绪缓解,也可以通过这样长期的行为实践,一次次给肌体注入新的感知,从而不断获得来自生命本身的力量。
当然,还有一点提醒:在对抗政治性抑郁的每一步的行动中,无论单一的行动本身多么有限,结果多么不可预期,我们都不必赋予它太多形而上的宏大理想,而导致对存在价值失去信念。
这是生活在与我们今天非常相似、时代同样撕裂的尼采,所反复诠释的“酒神精神”中的核心理念: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体命运的无常,去否定生命本身的价值。
一次行动结果的失败,并不会决定我们的一切。如此,才能更好地抵御时代压力的侵袭,因为具体行动的价值从来都是有限的。
接受有限,是避免政治性抑郁的关键。
04. 抑郁的时候,就看看历史吧
造成政治性抑郁的每个问题,几乎都牵连或背负着复杂的、结构化的系统性成因,这是任何个体都难以独自厘清和解决的。
吕松分析过年轻人遭遇政治性抑郁后的表现,他们会愤怒,感觉到被欺骗或背叛,并且难以重新审视自我的信仰体系。当我们发现,自己和已有的价值观步调不一致时,政治性抑郁,就可能会反过来引发更深层次的、关乎生命意义问题的危机。
二战后,世界经历了经济腾飞的高速发展期、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而在我们所处的时间节点,这一切都在整体性坍缩、分崩。
基于现代性生产模式生成的社会观念、文化、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旧有成熟词汇如“父权制”“资本主义”等,无法完全解释诸多现象,我们既有的思想资源,仍不够迎接时代的挑战。
这个时代的政治性抑郁,不仅仅是以个体有限的行动力,面对未来巨大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更是因为我们在诸多观念之中,时常面临无所适从的窘迫,甚至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思想锚点。
但话又说回来,有一个概念叫作“历史近视眼”,认知心理学家(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发现,人会本能地使用“易得性启发”(the availability heuristic)的“捷径”,来评估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即越是容易回想起来的事件,人们就认为它越可能发生。
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我们会更关注当下的痛苦,甚至觉得它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承受。
事实上,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困惑与痛苦。学者杨照在谈及历史的时候说,“许多过往的道路和选择,回头看也许路径很清晰,但在当下都是困境。”
许多在我们看来熠熠生辉的名字,其实也在遭受着来自信仰体系的崩塌与价值观的巨大冲击。比如清末民初自杀的梁巨川(梁漱溟之父)、王国维等,用今天的视角去看,或许都曾罹患政治性抑郁。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生活在19世纪末的清朝,在看起来黑暗无光的时代里,自身熟悉的一切,伦理次序、文明理念、世界想象……都遭遇着巨大的冲击,整体性的激愤与茫然弥漫四周。
那时的人们,很难想象就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潮流,不知不觉改变着所有的一切,塑造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当我们回望过去,他们所有人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性抑郁也非洪水猛兽,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许多优秀的结晶,经常是这些痛苦的副产物。
综观中国历史,自沉的屈原、疾呼的杜甫,近代的龚自珍与鲁迅……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原本自于内在感受的抑郁情绪,转化为对时代、对群体的爱与责任,而不是仅作为自我成就的抱负。
除了这些历史书上的名字,背后还有更加庞大的,跟我们一样,拥有着丰富感触的“普通人”,他们也默默推动文明史前进的基石。正是这种人类普遍的疼痛,促成了改造历史的合力。
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还会发现,无论如何人类磕磕绊绊都走到了今天,或许还会继续磕磕绊绊地走下去。
“读史早知今日事”,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接纳历史语境的变迁,或能帮助我们暂时跳出个体的遭遇,缓解时代造就的焦虑。
因为历史问题的爆发,总能在新的转角逐渐得到新的解决。在文艺复兴与现代性草创的前夜,黑死病正在欧洲肆虐;现代性的全面确立过程,伴随着欧洲近两百年的动荡,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诞生的。
政治学者刘瑜在一个讲座上表达过类似的感受:如果以理想为尺度衡量现实,当然会觉得很糟糕;但如果以历史为尺度来看待现实,你就会觉得,“还可以”。
今天,看似全球化遭遇困局,现代文明正遭遇挑战。确实暂时没有新的观念,一枝独秀地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信仰,鼓励我们走向未来。
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下,我们这代人仍会被时代的整体氛围压抑,我们的精神状态也容易进入一种“金属疲劳”的状态。最深处的政治性抑郁,当然可能终身难以完全治愈。
但越去了解历史,越会让人相信:也许我们同样身处于从未经历过的历史变局之中,更多崭新的观念,也正在孕育和突围。
这样想想,或许我们能对未来有一些好奇,对当下的行动也有更多价值感,能更坦然地面对当下的精神困境。
参考资料
1.《政治抑郁者:在大海上挣扎前行的夜航人》Political Depression,Dr. Robert Lusson|刺鸟栖息地
2.《正午之魔 : 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安德鲁·所罗门|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3.《陈婉容:(后)极权主义的阴霾下,人活著还有没有意义?》|the Initium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