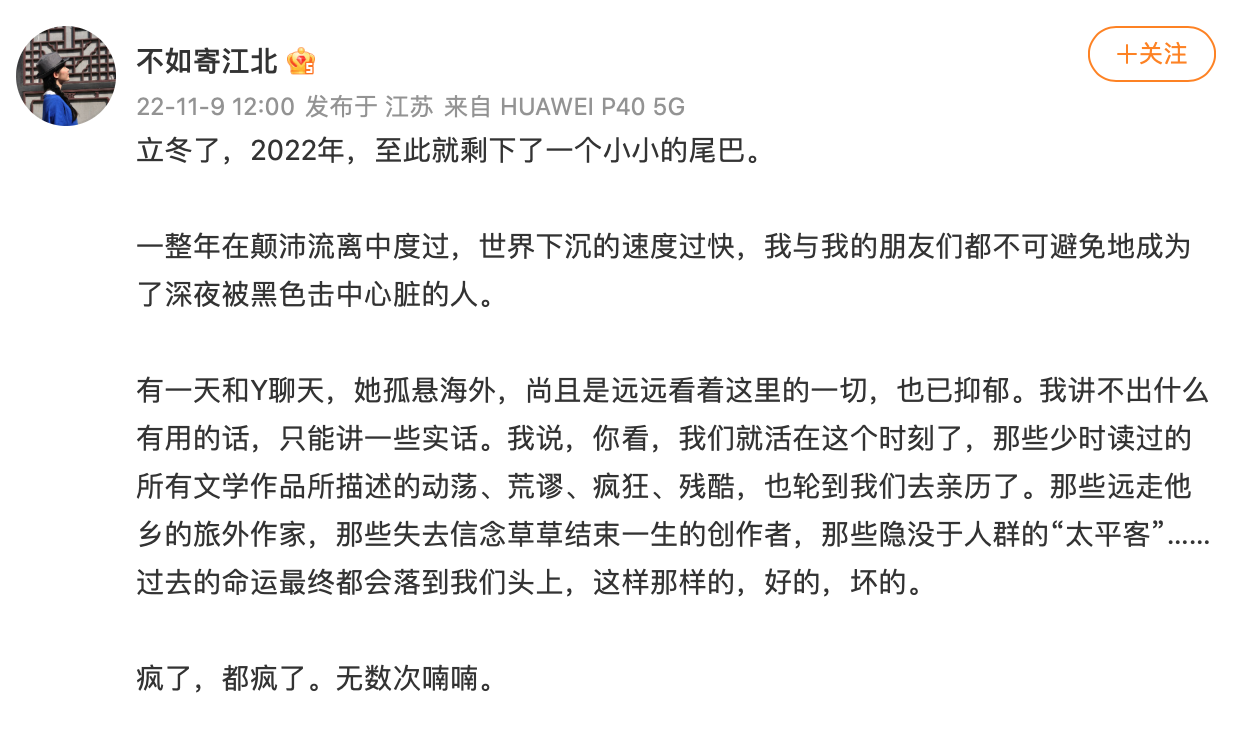@不如寄江北:
立冬了,2022年,至此就剩下了一个小小的尾巴。
一整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世界下沉的速度过快,我与我的朋友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深夜被黑色击中心脏的人。
有一天和Y聊天,她孤悬海外,尚且是远远看着这里的一切,也已抑郁。我讲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只能讲一些实话。我说,你看,我们就活在这个时刻了,那些少时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动荡、荒谬、疯狂、残酷,也轮到我们去亲历了。那些远走他乡的旅外作家,那些失去信念草草结束一生的创作者,那些隐没于人群的“太平客”……过去的命运最终都会落到我们头上,这样那样的,好的,坏的。
疯了,都疯了。无数次喃喃。
认真地讲,我仍有吃与穿,事业尚未停摆,朋友们还在近侧,至亲并未遭受灭顶的劫难。但肉眼可见地,受苦的人群在疯长,枷锁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满目的血雾越来越近了,迸溅到衣上时,已经很难装看不见。
常常会有无法抑制的愧疚。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秋天余晖落下的时刻,猫咪的头蹭上手背的时刻,安静地坐在桌前翻开一本书的时刻……一个声音会冷不丁响起:我是要下地狱的,时间有早晚而已。你敢说自己没有一秒钟站在妥协的一边吗?你敢说自己不曾膝盖一软闭眼退让吗?时至今日还不做点什么吗?可你到底能做什么呢?属于众人的大洪水已经来临,但谁知道该如何去造一条舟?
一个意外的带来宽慰的瞬间,是前几日去苏博。馆内正好在做木心的展,馆里游客寥落,就那样静静放着他的纪录片。寒冬的乌镇,呵气成霜,他窝在摇椅里语速很慢地回忆那个十年,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大意是:“我跟自己讲,我不能被他们毁掉。就算把我关起来,我要去要纸笔,我要创作。不给我纸笔的话,我脑子里也要在创作。只要我还在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没有被他们毁掉。”他说他从监狱的栏杆里伸头往外看,“月亮很好。”
只要还能感受到冬夜里月亮的美,就没有被毁掉。任凭他们绑住我四肢,但凡思想还在继续,他们就没有赢走我的一切。
如果像那十年一样,理性和科学被猎杀,一切都将变成恶的角逐。怀抱真诚善意的人,要逾越这个寒冬是艰难的。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然后拿胸口的热气一点点捂着它,捂着自己也是捂着别人。呵出的热气如同伸进天空的信号塔,我们都将靠彼此这一点点遥远的温度去越过寒冬。
前不久在某地演出,在剧场门口查验完证件、扫码完毕后,保安拦了不让进去,说“院长正在前面大厅里参观”。定睛一看,果然前面某一处站着院长等人,正对着一面墙赏玩。这一行人不过占了开阔大厅的小小一角,所有人就被封了路。不管是着急去演出的、剧院工作人员上班快迟到的、马上要开重要会议的,大家都被要求在远处等待,为公卿清道。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在这沉默的等待中愈发感到荒诞。开始问保安还要等多久。他说再等等。我又试图讲道理,我们持工作证,一切都可查验,并非什么来路不明的人,而且穿行大厅也就是两分钟的事,远远地经过并不打扰领导参观。他不耐烦地说,让你等你就等。我提高了声音,这里是剧场,是公共场所,难道现在是什么封建王朝吗?领导出行,普通人就没有走路的权利了吗?事先有通知吗?有文件吗?他不再言语,只是非常不友好地盯着我,示意周围几个保安慢慢围过来。
但原本静静等待的人群,终于在这一刻开始有了反应。一位看上去同龄的姑娘站了出来,跟我一同高声质问,保安自知理亏却仍不放行。姑娘冷眼看他,直接拎了包迈开腿走,我跟着一起。想象中的阻拦并没有发生,我俩就这样直挺挺走进了大厅。没想到的是,剩下的人目睹我们离开,也并未跟上,仍有许多人留在原地等待着没有尽头的“刑满释放”。
后来我跟那位姑娘互加了微信,得知她也是一位创作者。再后来我邀她来看春逝,她却说自己早已有票了,还在来剧场的时候给我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周边。那一天的心情都是好的,并非因为在闯关时提早获得了自由,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识别了同类。我们都没有背叛自己的灵魂。
友邻分享给我麦克尤恩的一段话,他说创作者有三个本份:良知、书写的技能和见证的意愿。在如今的环境中,这大概是所有人抵抗虚无的一种可能:我救不了他们,但我没有假装一切不存在。
我还在这里,我在记录和见证,如果有一天我的笔不被允许,就用我的身体作为载体。这具普通人的普通躯体,她的耳她的眼,将努力地记住现在发生的一切真实,在生命的每一天选择绝不遗忘。等到历史被试图改写、盖棺定论的那天,以及到达那天的漫长过程里,发我微弱之音,即便不能扭转任何,也要留下痕迹。正是依靠这样微弱的声音,我们会找到同类。如果有一天我这具躯体不在,我的同类会继续记录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被抹去了,至少我们没有不发一言地沉入水面。莫管浪潮卷向何处,这涟漪存在过。
将军,你的坦克很难摧毁,可坦克手也是个人。他有一天会想从栏杆里伸出头去,看看月亮。
祝我的友邻们平安。虽然常态化的奥斯维辛里,不会再有真正的平静,但愿大家能够有片刻原谅自己、心无旁骛地拥抱月色,再回过头来在夜深人静时继续书写和抵抗。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网友评论:
吕伏阳:知识分子在这片土地向来最脆弱。你相信吗?有些痛苦来自“不愿相信它已到来”。回京后我已彻底觉悟:未来一旬两旬甚至一生,事情只会这样下去,不会有心中一直虚妄期待的那个“回转”。所以,要快乐地活下去。为了种子留到看不见的未来;要么就惊天动地地死,也为溅出几粒种子,或吹动那人,看看月亮。
fo了蛙了瓜:“那些追问答案的人啊,不要羞惭。”
我坐金渐层那桌:知识分子总是多一分痛苦,因为他们总在思考“世界应该是什么样”……我想我会因为“世界是什么样”而停在保安围栏前,也会因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而一脚踏过去。(姐姐晚安
等花开_leaf:最近在读的一些书常常使我感到荒诞,仿佛八百一千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过多久,这些事件中展现出来的性格底色还要在我们的群体里存在多久。至少不应该鼓足勇气才能说真话,不应该要做好准备才能说真话。
冰莹落雪:读完想说什么,却在心里打草稿的时候就担忧地逐字逐句删除,甚至于读到原po的第一反应是慌张地保存下来,生怕哪天失去这份记忆。或许未来哪一天我所谓的“不妥协”也会被保护自己的沉默代替,在那天来临之前,我只能痛苦地记住一切。
欧神妮可:曾经觉得我们离那荒诞的年代很遥远,而实际上却早已开启了下一个十年。
海子街的瓊:来看月亮吧,即使隔着雾。
羊哥punk:活着的每一天感觉都是在对共情能力强的、有良知的人的一种审判。“我可能救不了他们,但我没有假装一切不存在”。含泪再读两遍。活下去,见证。
Reachable_:这样的时代里,保持清醒和愤怒容易,保持抗争或希望很难。但是难也要保持下去。我是这时代的一部分,那么无论能客观地留下什么,主观上,我都要留下属于我的感受。同行。
云妨psyche:永不妥协,永不做帮凶。
时钟下的兔子:我也是一个创作者,我写作,我绘画,我从发丝到指尖遵从生命的律动,我爱,我追求,我探寻,我不惧。想把鸟儿困于笼中的尽是妄想,因为没有牢笼,因为根本就困不住。
你是哪块小五花:大概是在深夜里嘶吼的声音实在太过于渺小,以至风轻而易举地将他吞噬。只是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月亮很好,遥祝你我平安。
西贝利亚山下雨了:想起王小波致李银河:你和我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足够了吧。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是温慕舒啊:在怪诞与荒谬中,原谅自我的怯弱,更对那些同行的灵魂,他们为突破绝望所做的坚守与抵抗动容,在常态化的奥斯维辛里,还有黑暗中大雪纷飞的木心们,告诉我们不要被毁掉。
Boat轻舟已过万重山:“常常会有无法抑制的愧疚”这句真的让人流泪。在我沉默,在我假装忽略,在我下意识选择性的只看歌舞升平的时候,在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和我同在一片土地的哭泣和伤痛依然充斥在我的身边、心上,于是我的沉默就变得可笑。
超大只王:反复看了几遍原文和评论里的回应,仿佛内心也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犹如这黑暗云雾中亮起的一个火把,得到了另一个火把的回答。而又有更多未发声的观察者,他们也不是在沉默,而是在等待一个点燃的机会。
安之若素如我:这个世界共情能力有多强就有多痛苦。
噢哦耶嘿喂:“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看到“无法抑制的愧疚”一时愣住,转眼看到“莫忘草木青”又放心了一点,加油诶,你并不孤独。
落拓章鱼:“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太阳照在脑门上:最近情绪很脆弱。虽然处于这个疯狂的漩涡里,也多年不曾用笔记录什么,但我依然有热爱的生活,有最爱的亲人,也不至于为了几斗米折腰,在这个生搬硬套、没有理性,令人窒息的运动中,自身的力量真的太小,我只能要求自己慢慢平静下来,祈祷自己和爱的人平安健康,保护自己不被裹挟进这场疯狂的运动中。
NLDRDDT-:坚守自己的观念,最大可能地为作恶增加成本。
一潭水水养乐多:只怕是书写下的记忆,也被有心引导篡改,变成方方类的‘不实传说’。如果生活在一个鼓起勇气才能有良心的时代,大乱也就不远了。
无耻海航欠债还钱:我贫瘠的语言无法描述我的心情。但我也是一位迷雾中试图突破思维禁锢的普通人。这个动乱的世界,如果谁说真话,当权者就会给ta带上“反”的帽子。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清醒一点。
MoonVelvet:想起木心在无法获得纸张的监禁岁月里,就在飞马牌香烟壳的背面手写曲谱。一切「愧」不成军的人,不要羞惭,也不要被击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