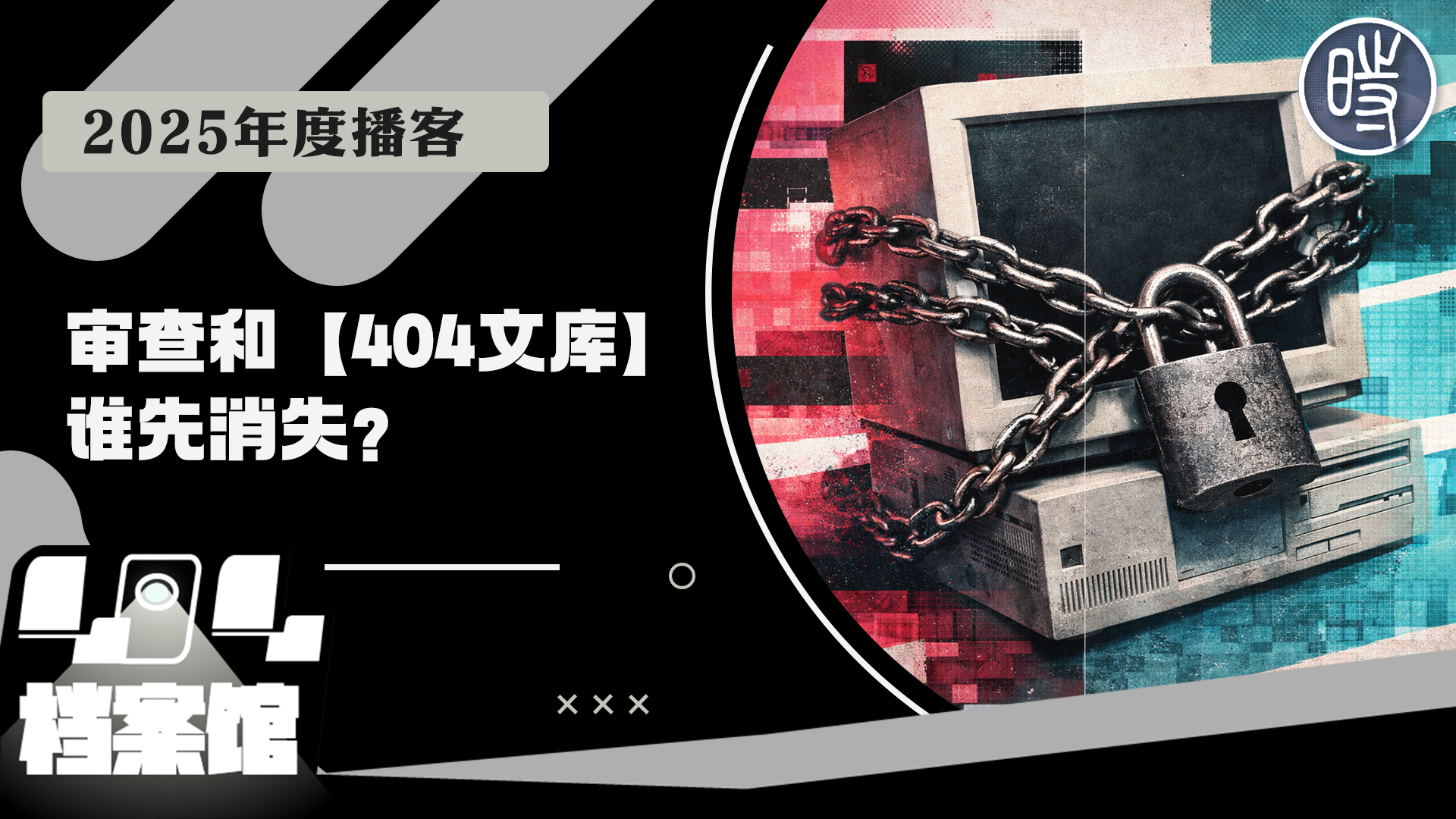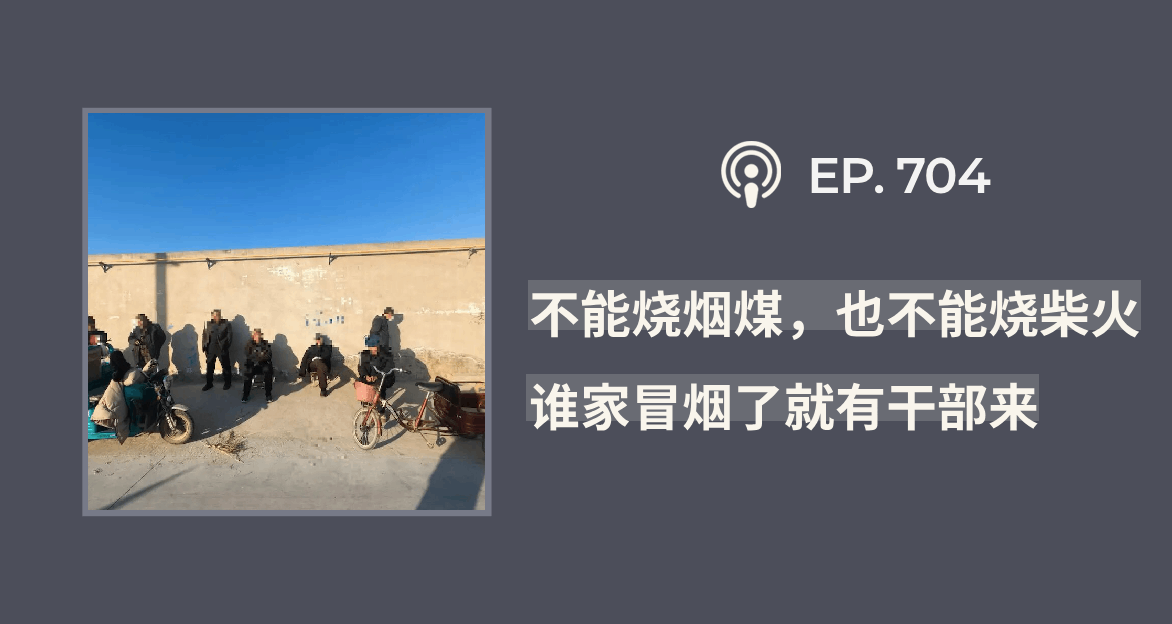“多年前,我从某知名媒体辞职。没有告诉任何人真实的辞职理由……”,黄雪琴说。
多年后,她参与了一场与女性赋权有关的话题分享,与她一同参与分享9位女记者当中有5位表示自己曾遭受了程度不一的性骚扰。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女记者群体里,不是只有她曾身陷囹圄,不是只有她选择了沉默。
图片来源:《华南早报》视频
#Me too风暴在盘踞西方主流媒体头版数月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今年年初,300名好莱坞女性发起的Time’s Up行动使得性骚扰问题再次升温。而在中国,2017年10月20日《我也被性骚扰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一文在传媒圈内掀起一波风浪;2018年3月7日,《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在调查报告发布之后继续跟进采访,一起来听听这份沉重报告背后的故事。
中国媒体版#Me too:聚焦女性媒体人
2017年,中国持证记者已超过22.8万,其中女性占48.23%,在媒体行业,女性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
然而,根据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全球约有一半的女记者遇到过与工作有关的性骚扰,近三分之二的女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威胁、恐吓、性别歧视及骚扰。而这个数字近几年有怎样的变动不得而知,原因是近几年的该主题的权威调查数量几乎为零。
8成受访者曾遭遇性骚扰,近6成保持沉默
此次调查共有1762人参与,收回有效问卷416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受访女记者曾遭受性骚扰,42.4%的受访者遭遇的性骚扰不止一次,18.2%的受访者遭遇 5 次以上。
“数据结果的出来的时候,这个数据展示的结果比想象中严重。”黄雪琴表示,这只是媒体行业范围内的一个调查,并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所以数据是偏高的。
这些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报警仅占 0.6%。“女记者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并且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数据结果验证了这一经验性结论。
89份被骚扰自述,5张#Me too照片
在网络上发布性骚扰调查的时候,黄雪琴曾呼吁曾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实名或匿名留言讲述自身的经历、拍照支持#Me too。截止调查结束,89 人以留言的形式分享了曾经的遭遇,37人以邮件、私信等方式详细讲述其遭遇。然而,只有5名女记者拍下#Me Too 图片。
黄雪琴表示,在这为数不多的5张照片当中,有人特意遮住了脸,有人只拍了自己的背影,几乎没有人愿意大胆站出来。
起初,在国内推#Me too的时候,黄雪琴就发现,许多曾遭遇性骚扰的人并不太愿意用正脸、图片或者相片的方式来直接告诉大家“我被性骚扰了”。互联网为匿名发声提供了便利,这也是她决定采用调查的形式推动大家为自己发声的原因。
女记者缘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很是讽刺,我们自认为以笔为嘴,为全民发声,为弱势群体维权,然而,却耻于为自己捍卫权利。”
—— 受访者自述
一边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一边自身遭到侵犯时却选择了沉默,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作为拥有良好的数据搜集能力、反应能力、敏感度及话语权的高知群体,常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女记者们理应比较大胆地维护自己权利。在和受访对象的沟通之中,黄雪琴找到了答案。
“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中国,记者是自我认同价值相对较高的职业,这使得大部分女记者的自尊心很强。”通过调查采访,黄雪琴发现,一些女记者会抱着“不想让家人失望,也不想让别人对她所代表职业失望”的心理。
由于性骚扰事件中的证据采集较为困难,加之女记者们见惯了社会上的冷暖与无奈。她们明白如果证据不足举证对方,对自己是很不利的——不仅担心隐私被泄露,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跟生活,还担心性骚扰实施者对自己的打击报复。
种种原因之下, 57.3%的女记者选择保持沉默。
“其实女记者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导致最后越勇敢为别人发声的人,到了自己身上就变得更加无力、更加尴尬。”,黄雪琴说道。
345份被骚扰问卷的背后
性骚扰——权力的游戏
“怎么处理?聪明泼辣的,挡过去;胆小怕事的,躲着走;委曲求全,那就是悲剧。”
——受访者自述
性骚扰实施者当中,超过九成(91%)为男性。其中,40.9%的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30%的为同事,37.1%为陌生人,17.3%的性骚扰实施者为工作中的采访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40.9%的性骚扰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础岗位,职业级别仍有较大的性别差距。
由于早期的行业发展缺乏专业培训,黄雪琴认为,目前记者行业内充斥着一些“江湖气”严重的中上层领导。“那些站在权利的高处的资源拥有者或者既得利益者,比较容易对相对职位低、相对能力或者权利跟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群体发起的挑衅。”
“不仅是女记者行业受到困扰,性骚扰背后的本质是权利跟资源的不对等。” 黄雪琴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权主义者:“不管是男跟女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所以这不是一个男跟女的战争,而是权力高位跟低位的一个战争。”
人才流失不容忽视的原因
“这样的环境又会导致女记者的纷纷转行,媒体人才流失,媒体环境更加恶劣。”
——受访者自述
职业的特殊性是女记者成为性骚扰高发群体的一大原因,调查当中,性骚扰实施者为女记者的采访对象的比例也高达17.3%。
在遭遇过性骚扰的媒体人当中,16.3%的人有持续的精神抑郁,12.4%严重影响了事业,5.6%的当事人有自杀和自残倾向。
黄雪琴说:“如果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了采访对象的性骚扰,可能会对受访者其实是存有一定的芥蒂之心的,就很难再建立起跟受访对象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她们工作的表现,也或多或少地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媒体行业不景气、收入不高、做新闻的空间变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媒体行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黄雪琴发现,除了以上原因,性骚扰遭遇也是促使女性媒体人转行的重要刺激因素。
“这背后有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倾向,性骚扰是传媒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黄雪琴表示,“调查虽然没有显示出职场性骚扰是媒体人离职的直接原因,但它确实是原因之一。”
阴暗里的曙光
“或许真的像你说的,只有重新揭开伤疤,让里面的淤血流出来才能真正治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自我治愈,也给更多女记者们一份力量。”
——受访者自述
自揭伤疤、打破沉默、调查呼吁……"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曾是黄雪琴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她的这份勇气与果敢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面临着多种质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给记者行业抹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加剧两性矛盾。
在黄雪琴看来,大家应该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不应该因过度美化而对女记者性骚扰问题避而不谈。目前的状况是——女记者职场性骚扰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性骚扰与调情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在黄雪琴看来,之前的披露和这次的调查都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事情。
比如,在这次采访调查中,有位男编辑想借这个调查道歉。这位男编辑说,他曾出于喜欢拥抱了一位女记者,在了解了许多性骚扰的案例之后,发现这位女记者当时可能因为他的高级编辑身份而压抑了不情愿,他认为自己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骚扰了这位女记者。
有时候,性骚扰和调情只有一步之遥。黄雪琴说:“当事人到底舒不舒服,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一点很重要。”
有人揭开自己淤血的伤疤,有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黄雪琴认为自己的举动至少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思及性骚扰意识的提升。“其实很多人对性骚扰是脱敏的,我希望大家敏感起来。”
沉默到发声:让脱敏的人们敏感起来
下一步,黄雪琴打算将这份性骚扰报告邮寄给记协和工会,引起他们对行业内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在黄雪琴看来,媒体行业是在一个比较开放、包容、接纳的行业,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带头来在媒体里面做一些培训,给女记者做一些培训,告诉她什么是性骚扰,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去做。”
调查显示,61%受访者在性骚扰发生后处于一种“懵”状态;48.6%不知道该如何反抗;近74.4%的受访者都希望工作单位有必要开展“防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或者出台相关的规定,但只有3%的受访者表示他曾受到过相关的培训或讲座。
中国缺少防治性骚扰的机制是性骚扰问题的症结所在,黄雪琴和罗茜茜很早就在资料搜集中认识到这个情况。防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包括事前的防性骚扰教育、事中的处理机制(调查协助、法律援助及心理咨询)及事后的惩罚机制三个方面。“‘反性骚扰机制’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我要把实化。”
《时代》杂志2017年度风云人物——“打破沉默者”,这个词不仅指#Me too运动中勇敢发声的女性,而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职业与身份,都选择不再沉默,将秘密公诸于世,汇集成一个声音的群体。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打破沉默者”的行列。
在这个注意力只有七秒的金鱼系时代,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发声本身,更是一种力量。黄雪琴说:“其实尖锐的批判声当局反而不接受,人们反而愿意倾听那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声音。我希望我发出的声音是柔和但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