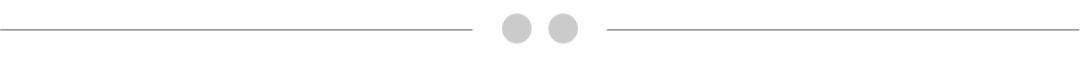最近,互联网上兴起了一场造“媛”运动。
先是“佛媛”说法的迅速爆红,然后各个媒体为蹭热度开始造谣“病媛”,接着网上迅速效仿衍生出“支教媛”“医媛”“饭媛”“离媛”等词,让“媛”的意义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媛”这个本指漂亮女性的褒义词被污名化为搔首弄姿、打造人设以赚取流量和财富的女性。
虽然现代中文里含“女”的字大多表贬损和侮辱的意思,但没想到在2021年,“娘”和“媛”也要加入娼、妓、婊、妒、妖等字的行列了。
也许三十年后的年轻人会惊讶于曾有那么多女性取“媛”字为名,不亚于现在的我们因不知“嫖”曾用来形容人勇健轻捷,而震惊于西汉汉文帝给女儿取名为刘嫖。
毫不夸张地说,这场造“媛”运动是一场厌女集体潜意识的大型爆发。每一个被造出的“媛”都从不同角度体现着对女性的污蔑、矮化、抹煞和憎恶。
其中最容易被看穿的厌女行为是数家媒体把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生病经历的女性造谣成带货假装生病的“病媛”,并且在当事人澄清后拒不道歉。
女性用漂亮的照片获得流量和钱财是大逆不道,但是媒体造谣污蔑女性而获得阅读量和关注却是正大光明,这样的“双标”实在过于讽刺。
公然的污蔑造谣容易被戳穿,而弥散在文化中的厌女逻辑却难以被捕捉。
有时厌女文化氛围过浓,让我们感到气愤、窒息甚至绝望。但是,被厌女文化伤害的痛觉,是觉醒的证明,也是改变的向导。每一次对厌女逻辑的捕捉、对厌女行为的抗议、对厌女情绪的反省,都至少是迈向进步的希望。
1.
男人对女人的欲望,来自**占有和支配**
梁文道在《八分》(319.成为“某媛”为什么会被骂?)中谈到,从古至今,利用佛教来满足和粉饰自己欲望的人比比皆是。为了个人的健康、学业、姻缘、财富而去寺庙烧香拜佛,本质上都是为了一己贪念,是违反佛教教义的。
而利用佛教文化赚钱盈利那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了,那些价格不菲的佛珠、刻着菩萨相的玉坠、讲究禅茶一味的茶道等等,哪一样不是生意,不是在利用佛教文化赚钱?
可是,舆论却从未把这些行为纳入需要被谴责的雷达上。
直到出现几个漂亮的“穿开衩袈裟吊带佛衣”的女性用学佛的人设赚钱(她们甚至可能都赚不到多少钱,且也有当事人澄清并非在寺庙拍照),一些人立马警铃大作,不仅对她们在网络上进行封杀,还在名声上进行羞辱。
不难发现,所有抨击“媛”们的文章都没有提到男性,但其实整个猎“媛”事件的逻辑都和男性密不可分——穿着暴露身体服饰的女性看上去就是不正经的“媛”,因为她们这样的穿着和姿态会挑起男性的欲望,而男性会被挑起欲望是因为他们对女性的身体有着天然、纯粹的欲望。
这个逻辑太深入我们文化的骨髓,以至于人们可以迅速地靠外貌和姿态来给女性贴上“媛”的标签。
但仔细想想,男人对女人的欲望真的这么“天然”,以至于他们看见女人的吊带抹胸、短裤短裙就会产生欲望?既然他们的欲望这么“天然”,那岂不是古往今来的男性都应该享有相似的欲望?
古代男人是不是看见现代女性的吊带抹胸、短裤短裙和高跟鞋就难抑情欲还有待考证,但是现代男人应该很少会对古代男人痴迷的一个女性部位和一种服饰有欲望——女人被缠得畸形的小脚和缠足女人穿的莲鞋。
准确地说,中国男人对女人小脚的痴迷并不只是古代的事情,毕竟放足运动也不过是上世纪初的事情。在《摇晃的灵魂:探访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一书中,作者杨杨记录了,在缠足崇拜的文化中,男人对小脚的痴迷不仅仅是欣赏,而是有着强烈的性欲。
他们不仅认为小脚好看、性感,还要把玩、吮吸这根本已经看不出形状的小脚。要知道,缠足的女人并不能常洗脚,被布紧紧包裹的小脚上充满了汗液,甚至还混合着血液,让脚散发出难以想象的臭味,但是这样的味道,却让过去的男人迷恋,是可以挑起他们欲望的一种气息,是男人们之间隐晦却刺激的谈论话题。
历史学家高彦颐在《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的书中还详细记录了,过去男人因为对小脚的痴迷而衍生出了不少描写和幻想关于缠足的露骨性事文章,同时还有很多男人钟情于收藏女人的莲鞋,甚至还用发臭的莲鞋喝酒作为男人间玩乐的恶趣味。
为什么过去的男人会对这样畸形的小脚产生性欲?因为在男权社会中,男人对女人的欲望从来不是性本身,而是关于占有和支配。
和现代女性的胸部一样,缠足是私密的,欣赏和把玩女性的小脚表示了男性对这个女性的占有,这种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占有和支配感让男性兴奋,于是小脚和莲鞋也就变成了承载男性性欲的符号——正如现代女性的胸部和内衣对现代男性一样。
现代男性可能觉得过去男性对小脚的痴迷很变态,殊不知自己的欲望能轻易地被女性的服饰和身体部位点燃,表明着自己与过去男性并无本质区别。
大多男人并没有意识到,男权社会在给了他们支配和占有女性的权力和资源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欲望驯化,让他们习惯把女性物化、器官化从而达到占有的目的,使自己的欲望最终寄托于器官、物品和符号。
而这欲望被驯化的过程,使得男性丧失与真实的女性交流、共情、相爱的能力,以至于他们看起来对女人有很强的欲望,但实际上迷恋的只是自己想象中的物而已。
2.
“还不都怪女人自己要迎合男人审美吗?”
一些人认定,只要女性打扮得让男人觉得很性感,就是在故意勾引和讨好男人——正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公然造谣“媛”就是性工作者;但会有另一些人认为,这样穿着打扮的女性也许并不是有意要讨好男人,但潜意识里一定是在迎合男性审美的。
不过,无论是有意的讨好还是无意的迎合,许多人仍认为穿着性感的女性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被骚扰还是在网上被“猎媛”都并不无辜。
但是,不管是否有意,女性迎合男性欲望的审美真的是错吗?在男性掌握社会资源和权力的社会,女性难道有机会逃脱男性欲望的审美塑造的牢笼吗?
当女性完全跳脱出男性欲望对象,会怎样?
2005年开启女性中性审美潮流的李宇春,虽然爆火但是多年来一直被很多男性骂为“春哥”,在网上对她极尽羞辱和讽刺。十五年后的现在, Sunnee、刘雨昕这些个别“幸存”的外表中性的女偶像仍在遭受着大量因外表而带来的诋毁。
普通女性在工作生活中更是难逃为男性欲望而服务的审美体系的评价和筛选。
最近,乌克兰SkyUp航空公司为女性空乘人员更换了制服,把过去的紧身裙改为宽松的长裤,并且不再强制空乘穿高跟鞋,而是可以换成她们觉得舒服的鞋子,比如运动鞋。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改变,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会去思考为什么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女性空乘都要在狭窄、干燥的客舱内画着妆,穿着高跟鞋和紧身裙进行紧张的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这样的要求又何止限于空乘,无数的行业、职位、场合都对女性都有着类似的着装要求。
掌握着社会资源和权力的男性,把这样符合自己欲望的审美通过广告、影视剧、工作选拔等方式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让女性潜移默化地认为这就是自己应该成为和追求的样子,明白自己需要打扮成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社会地位,以及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
所以,穿着开衩袈裟吊带佛衣来赚流量带货的女网红和航空公司广告中穿着高跟鞋紧身裙的空乘有区别吗?从是否迎合男性审美角度来说,没有区别。
但在另一个层面有重要区别——前者是女性自己在赚钱,而后者是父权社会之下,男性为主体的高层在利用女性赚钱。
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审美和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并不是到了成年才突然形成的。
早在女孩明白什么是男人的欲望之前,早在她们意识到自己可以、需要利用外表来获得社会地位之前,男性欲望下的审美早就已经通过动画片、电视剧、家长和学校将她们同化了。
女孩成长过程中听过无数次“你长得真漂亮” “太胖了别吃了” “这么穿显得腿细”“赶紧打伞小心晒黑了”等等话语,都在告诉她们自己的外表有多重要。
这些来自家长、朋友的日常夸奖或劝告的初衷都不是为了让她们去刻意讨好男人,但确实又都是在将她们塑造成男权社会中男人们会喜欢的样子。
而学校的反向操作——为了让女生专心学习而禁止她们打扮、为了防止早恋而要求她们遮盖自己发育的身体,看起来是保护女生,实际上仍然是在告诉她们,你不是你身体的主人,你的身体是为了符合外部的评价体系,是为了他人的眼光而存在(或隐藏)的。
所以,攻击迎合男性欲望的女性无异于讽刺那些为了保住工作而拼命加班的“打工人”——不去责怪制定规则的权力上位者,而去责怪学习并遵守规则的弱势群体,这样的谴责是错位的。
3.
警惕以解放女性为名,
对另一些女性进行压迫
想想一百年前的大多数汉族女性还要缠足,我们很难不庆幸自己活在21世纪,这也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把女性从男性权力和欲望所建造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
于是,很多人以解放女性之名,对那些看似不够“进步”和“现代”的女性进行严厉抨击。
我们也许可以理解这些情绪的初衷,但是过去中国一百年的女性解放事业也提醒着我们,对一些女性的解放很有可能同时成为对另外一些女性无情的压迫。
《摇晃的灵魂》书中写到了云南这个村子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
她从小就被长辈告知“大脚女人是一个妖怪”,到了五六岁,她迎来了漫长的缠足噩梦。她每天都哭,母亲也为她哭,但还是要经历这让人骨折筋挛,皮亏肉烂的漫长过程。
她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哪里知道缠足和男权社会的关系,她只知道缠足是母亲痛哭着也要让她完成的事情,是她可以让母亲在村子里抬起头来的事情,是未来可以让她找个好人家过日子的条件。所以,她熬过了漫长的缠足黑夜,用无数血泪换来了一双小脚。
可是,这时候她看到村里的女孩们已经开始放足了,那些高呼着天足万岁的女孩走过她家大门,“向她显示出放足的荣耀…显示出不依存于男性的那种近乎神圣的冲动”。
她也幻想自己能有双天足,带她去飞快奔走、感受自由,但同时“她深爱着那来之不易的纤纤玉足,像贡品一样,寄托着她太多太多的赤裸的愿望”。
现代人在拥抱和庆祝放足运动结果的同时,却极少了解到那时候对缠足女性的公开羞辱。而当时那份让女性放足的迫切,却并不真正源于对于女性需求和困境的理解。
《缠足》里高彦颐写道,那时男性知识分子眼里,女人缠足是中国不如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把女人的身体视为失去的疆土,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回主权进行现代化改造。
于是,男性改革者和男性主体之下的城市知识妇女,不断散播缠足女性苦难叙事,用最迫切和激进的方法强迫女性放足,却无视年长妇女在这样的声浪中受到的羞辱、贫苦乡野妇女沦为女贼的无奈等等女性面临的种种复杂的困境。
就像杨杨书里描述的缠足女人的感受:“缠足只是阵痛,只是皮肉筋骨止痛,而放足之后的疼痛,是心灵的绞痛,是相伴一生的刺痛”。
很多人,包括女性和男性,都希望如今的女性可以自立自强、不再依附于男性,从男性的权力和欲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是这份迫切让他们与当时的进步人士对待缠足女性一样,以解放之名行残忍之事。
这次是对迎合男性欲望的网红的羞辱,其它时候是对放弃工作的全职太太,让孩子随父姓的母亲,为了弟弟而放弃学业去打工的姐姐,为了达到白瘦幼标准而整容、催吐、割胃的女人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攻击。
可是,不站在真实、具体的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困境和欲望,而把自己理想化的,甚至是幻想的独立和选择强加在她们身上,又怎么谈得上“解放”?
成长生活在男性欲望为主导的社会中,批判和羞辱迎合男性欲望的女性有什么意义?如果认为女性迎合男性欲望是错,那么抵抗的可能在哪里?抵抗的空间又多少?抵抗的代价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抵抗的力量?
在能回答和解决上面的问题之前,谁都没有资格对着女性的外貌、生活是否迎合男性而指手画脚。
因为,这些指手画脚的逻辑与将女性困在男性欲望主导的权力结构中是同一种力量——都并不在乎女性真正面临的处境和欲望,只想利用女性为某一种幻想服务,无论这种幻想听起来是多么美好,也只会成为女性身上的另一把枷锁。
参考资料
1.《摇晃的灵魂:探访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杨杨
2.《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高彦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