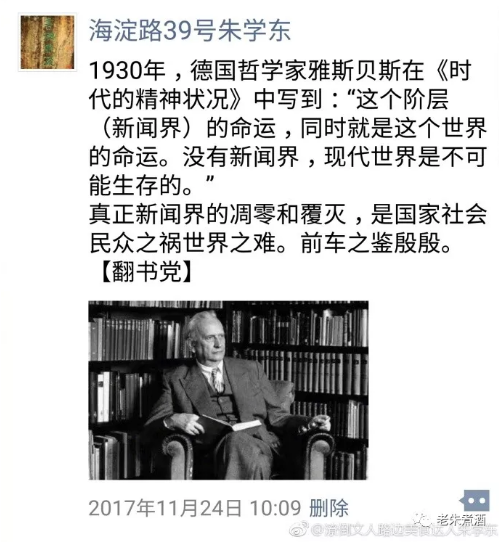【这篇文章,是2017年9月我熔断职业生涯后,一个朋友代一家媒体约的稿。这家媒体想做一个新闻专业主义的学术讨论,朋友希望我从曾经的从业者角度谈一下。我犹豫之后,最终还是动笔了。因为,站在业界角度思考的太少了,许多高校老师,所谓站在学术角度的思考,浮光掠影,完全是何不食肉糜。本文写于2017年10月中旬,至于杂志发没发,我不清楚,也不关心了,毕竟半年过去了。最近我有两个特别好的才华横溢的年轻朋友,又相继离开这个行业,我有些伤感,遂翻出来。在下述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被微博删除的今天,在前坂俊之反思日本新闻界从被军国主义裹胁到主动做恶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的读后感都会被删除的今天,这篇文章,我想对我个人,一个新闻业逃兵最后的哀鸣,算是给自己的媒体生涯棺材上钉上的最后一枚钉子吧,也权当向两位年轻友好致意,壮行。】
“再有片刻——
将猝然中止有关黏土委屈的朴素歌声,
而嘴唇也将被灌入铅块……”
——曼德尔施塔姆,《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新闻专业主义,无论是在曾经昙花一现的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还是在今天这个新闻业的凛冬,在那些曾经的国内市场化媒体以及今天依然对新闻尤其是关注知情权的新闻传播学界和媒体业界,它依然是一个令人尊敬且向往的追求,尽管实践中屡遭践踏。
在当下中国的媒体实践中,并不存在理想语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但并不是说,它就不存在,尽管有残缺,尽管无论新旧媒体极大多数奉行的是新闻不专业主义,而真正能够朝向专业主义方向努力的媒体屈指可数。
作为一个曾经在媒体行业服务了二十余年,并曾经在横跨政府管理机构、专业媒体、杂志和报纸,内容和经营,第三方研究机构服务,同时也是自媒体重度玩家的人,我对新闻专业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切肤之痛。
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使用新闻专业主义这个外来词汇,我个人更愿意使用职业追求和专业要求这两个土产词汇来表达自己在服务媒体时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我个人认为,在实践中,这两者的相合,大致与西式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相距不甚太远。
那么,什么是媒体的职业追求?
现代媒体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媒体是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出现的,我理解这个意义上的媒体,它的核心价值就在记录与传播,记录信息,传播信息(当然,不同的媒体对信息的理解自然也不同)。这是媒体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它关乎公众的知情权。
这两项要求,看似简单,其实很难,不惟现在,过去也不易。1931年,胡适称赞大公报,说它那几年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这两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其实是每个媒体,无论什么性质定位,都应有的职业追求。
而专业要求,则是确保这个“最低限度”的职业追求实现的能力和道德要求,即确保胡适提到的“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言论”。
所以,在中国的媒体实践中,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媒体的职业追求和专业要求,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如何办一份负责任的媒体的基本要求。
当代中国媒体是由党政机构的业务延伸而来,最初主要服务于党政机构的工作,这也是其宣传和喉舌功能的由来。但一个东西一旦离开母体,它终究会有按照自己的生命逻辑发展的意图,更何况,后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最初脱胎于党政机构及其延伸物的媒体,尤其是后来被普遍称为市场化的媒体,逐渐获得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这种成长,是社会发展过程社会分工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渐次开放的产物。
这些在社会上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媒体及其从业者,开始按照职业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而这一过程,其实也是职业化专业化的过程。它的核心评价标准,不再是原有母体的标准,而是社会标准,市场标准,专业标准。这个时候,这些媒体的影响力,不再是来自于原来母体的品秩地位,而是来自于它内容产品的社会公认的影响力和专业水准——当然这种专业水准也是随社会变迁而改变的,其方向自然是遵循媒体业内在的逻辑。所以,尽管现实的压力和作为媒体的内在逻辑之间有着冲突,有追求的媒体人,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有职业追求和专业要求之路。其思想资源既有来自传统的铁肩道义辣手文章,也有渐次开放后对外国同行的学习。这一过程中,学界引进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这一理念恰好同媒体业自身的追求合流了。
必须强调的是,这一过程,是媒体业基于社会分工逐渐而来的,是职业化的产物,绝非学界一些人所谓的产业化产物。
我没有系统学过新闻专业主义知识,所知不过一鳞半爪。但在我的媒体生涯中,无论是做专业媒体时代(《传媒》),还是在政经杂志时代(《南风窗》、《中国周刊》),亦或是大众媒体(新京报),我都努力坚持一点,就是在时代允许的框架下,回到媒体本身,回归媒体的基本属性,让它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媒体。这是我的职业追求,也是我执掌具体媒体时那些媒体的职业追求。而专业要求,就是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的框架下,尽可能逼近真相,追索真相,服务社会。媒体对真相的追索,是法律赋予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的保障。这也是媒体和媒体业者的尊严价值所在。
所谓时代允许的框架,无非就是政治和法律许可的空间。一个夹缝中成长出来的有影响力的媒体,因为日常坚守,它公开的隐秘的敌人很多,这些人都等着你犯错误,一旦出现事实性疏漏,你便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前车之鉴殷殷。所以,在中国,专业追求是能用来求生的,它能帮我们规避许多风险雷区,而且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
我所服务的过的媒体,无论是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新京报,在这方面都是坚持的受益者。尤其是新京报,2016年一年3万多条报道,3600多条评论,即时新闻近12000条,微信原创17000余条,直播320场,短视频3500余条,这么大数量规模的原创生产供应能力,能够有今天,就是报社管理层在职业追求和专业要求方面的坚定不移。没有这两方面的支持和规范,保证新京报不出重大的事实性疏漏,以舆论监督闻名的新京报早就横死了。无论是早年的正定血案嘉禾拆迁报道,还是后来的上访者的精神病院,更后来的沙漠之殇天津港爆炸报道,河北大水练溪托养中心报道等,成就这些报道的,不仅是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追求和勇气,更有扎实专业的调查与突破,当然,报社管理层对这一理念的坚定不移,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当时的记者采访不扎实,后方编辑逻辑梳理不严密,证据审核不严谨,报道中事实上有任何瑕疵,新京报就不会有今天。
在这些年新京报遭遇的诉讼案中,无论是世奢会诉新京报侵权案,还是中曼石油诉新京报案,最后保护新京报和记者的,就是素所追求的专业要求。而这些案例,都将成为新闻业的经典判例,其中世奢会诉新京报、派博在线和记者刘刚的案例,在二审判决后来写进了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
无论是在错漏被高度政治化的局面中,还是在名誉侵权诉讼日益增多的环境里,正是这种职业追求和专业要求,确保了新京报打铁还需自身硬,既获得了职业荣耀和尊严,也保护了自己。
这些年常在河边走,我总结职业追求和专业要求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也是新闻业前辈早已公认的,就是尊重新闻事实。在具体实践中,不仅要尊重新闻事实,逼近真相,更要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物化留存,而证据链条必须完整,同时,在采访和报道中,注意信息观点的平衡采集。同时,一定要求是职务行为,决不允许非职务行为作品出现在负责的媒体上。
但是,这样的追求,在过去也是很奢侈的,而如今越来越难。
新闻专业主义之无法实现,在我们身边,首先是政治。其次是从业者自身的追求和努力不够。在过去,即便有压力,有追求的从业者依然可以找到一定的空间腾挪,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为自己服务的媒体和个人,打下良好的职业声望。如今绝大多数人,或许也包括我个人,借口政治、资本和技术的冲击,而弃守原本应该有的责任。
我之熔断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这个行业的逃兵,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行业的职业追求和专业能力,已经越来越无法为自己,为自己服务的媒体机构带来尊严和社会价值,不是边际递减,而是在经历较长边际递减后的急速坠落。无论媒体还是从业者,越有追求越有能力,越发寒冷绝望。
海外一些传播学者也包括国内一些高校学者,把国内新闻专业主义萎顿不兴,常常主要归咎于资本和技术对媒体的影响和控制,让媒体失去独立性,从而扼杀新闻专业主义。
资本和技术控制媒体有没有?这个情况当然大量存在,但是,这个情况的存在,首先是附着于政治影响的卵翼下的。政治让资本和技术必须更着眼于即期利益,否则可能会颗粒无收。
同时,政治也让媒体行业的职业追求和专业要求失去了自我提升自我净化的功能,劣币驱逐良币的戏一直在上演。
在我们身边,媒体业如果要与政治、资本以及所谓大众趣味保持适当距离而有一定的独立性,不知有多艰难。能够坚守住的,不知要有多高的情商智商和多坚强的神经。但是,最最艰难的,并不是面对资本和大众趣味的压力。
在中国做媒体,我相信任一家都会有与资本妥协的时候,但妥协不是被左右。我职业生涯服务过的媒体机构,至少我了解和亲历的,对于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从来没有在资本压力下妥协过,这两年的新京报在舆论监督和经济报道方面所经历的诉讼,其实都反应了这种不妥协。这也是我服务过的媒体,以及我个人在职业生涯中赢得尊严的原因。
至于是否屈服于大众趣味,这是媒体定位的问题,就像我在中国周刊,或者分管新京报书评周刊时的坚持一样,如果要屈服于大众趣味,那既不是它的追求,也不是我愿意做能够做的,如果机构坚持要这样做,那就只能另请高明,恕不奉陪。
所以,把新闻专业主义无法成长归咎于资本等不谈政治,在我看来,与阿拉贡赞美苏联萨特赞美中国,异曲同工。根本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干脆故意视而不见当了鸵鸟。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在技术和资本催生下,自媒体似乎所向无敌,虽然也有一些自媒体努力为社会提供专业的严肃的信息,但是,整体性的状态并不容乐观。在美丽新世界,我们必将失去知情权。这是我们合力自掘的坟墓。
但我相信,在遥远的未来,哪怕传统媒体都死了,新闻专业主义也将如一盏明灯,照亮着热爱寻找真相的人,没有这盏灯,所有人将生活在黑暗中——一个垃圾信息笼罩的黑暗。但是,在可以看见的将来,我个人愈发悲观。